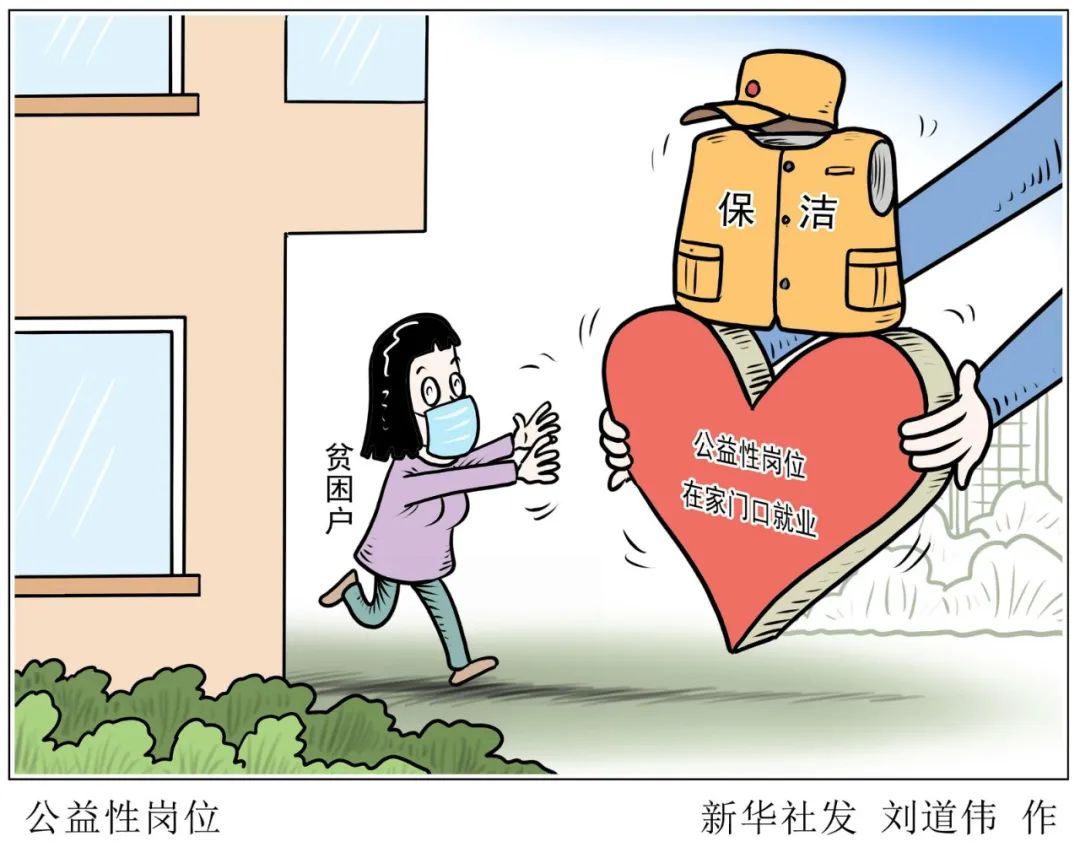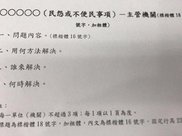еҢ…ж…§жҖЎпјҡиҘҝж–№ж–ҮеӯҰдёӯзҡ„вҖңзҺ«з‘°вҖқж„ҸиұЎпјҢжҳҜиҜ—дәә们й•ҝд№…зҡ„з§ҳеҜҶ(14)
иҖҢеҜ№еҗ„з§ҚзҺ„еӯҰзҗҶи®әз»Ҳз”ҹдҝқжҢҒе…ҙи¶ЈгҖҒиҮӘе·ұжҳҜвҖңйҮ‘иүІй»ҺжҳҺвҖқGolden DawnзӯүзҺ„еӯҰз»„з»Үй«ҳзӯүдјҡе‘ҳзҡ„еҸ¶иҠқжң¬дәә пјҢ жӣҙжҳҜеӨҡе№ҙз ”д№ и”·и–ҮеҚҒеӯ—дјҡж•ҷд№ү пјҢ е…¶дёӯе°ұеҢ…жӢ¬иҝҷдёҖжқЎпјҡеҸҜж„ҹзҹҘзҡ„зү©зҗҶдё–з•ҢжҳҜд»ҺзІҫзҘһдё–з•ҢејҘж•ЈemanationеҮәжқҘзҡ„дёҖзі»еҲ—дё–з•ҢдёӯжңҖдҪҺзә§зҡ„ пјҢ дҪҶе®ғдёҺзІҫзҘһе®һзӣёд№Ӣй—ҙд»Қжңүйҳ¶жўҜзӣёиҝһ гҖӮ еҸ¶иҠқз•ҷдёӢзҡ„笔记жҳҫзӨә
пјҲд»Ҡи—ҸзҲұе°”е…°еӣҪ家еӣҫд№ҰйҰҶең°дёӢе®Өпјү
пјҢ д»–еңЁжңҖжІүиҝ·и”·и–ҮеҚҒеӯ—дјҡж•ҷд№үзҡ„еҗҢж—¶еҸҲеңЁз ”究еҚ°еәҰе“ІеӯҰ пјҢ 并е°ҶеҗҺиҖ…зҗҶи§ЈдёәвҖңеӨ§дҪ“и®Өдёәе°ҳдё–жҲ–жӣ°иүІзӣёйғҪжҳҜиҷҡе№»зҡ„вҖқ гҖӮ еңЁгҖҠиҮҙж—¶й—ҙеҚҒеӯ—жһ¶д№ӢдёҠзҡ„зҺ«з‘°гҖӢдёӯ пјҢ жҲ‘们еҸҜд»ҘзңӢи§ҒеҸ¶иҠқеҜ№дёӨз§ҚзҗҶи§Јдё–з•Ңзҡ„дёҚеҗҢжЁЎејҸзҡ„ж¶ҲеҢ–е’Ңж•ҙйҘ¬пјҡвҖңи”·и–ҮеҚҒеӯ—дјҡжЁЎејҸвҖқе…·жңүејәзғҲзҡ„жіӣзҒөи®әеҖҫеҗ‘ пјҢ зӣёдҝЎзңҹзҗҶд»ҘиҮӘ然з•ҢдёҮзү©зҡ„йқўиІҢж— еӨ„дёҚеңЁең°е‘ҲзҺ°пјӣвҖңеҚ°еәҰж•ҷжЁЎејҸвҖқеҲҷи®ӨдёәиҮій«ҳзҡ„зңҹзҗҶжҳҜжІЎжңүеӣҫеғҸзҡ„вҖ”еүҚиҖ…дҪҝеҫ—иҜ—жӯҢдёӯзҡ„иұЎеҫҒдё»д№үжҲҗдёәеҸҜиғҪ пјҢ еҗҺиҖ…еҲҷжҸҗйҶ’иҜ»иҖ…йҖғзҰ»зҡ„еҝ…иҰҒжҖ§вҖ”дәҺзңӢдјјзҹӣзӣҫзҡ„жҖқз»ҙжЁЎејҸдёӯеҸ‘зҺ°е…ұз”ҹзҡ„еҸҜиғҪ пјҢ д№ҹжҳҜеҸ¶иҠқеңЁжң¬иҜ—д№ғиҮіж•ҙйғЁгҖҠзҺ«з‘°йӣҶгҖӢдёӯиҮҙеҠӣдәҺе®ҢжҲҗзҡ„дёҖ件дәӢ гҖӮ
гҖҠиҮҙж—¶й—ҙеҚҒеӯ—жһ¶д№ӢдёҠзҡ„зҺ«з‘°гҖӢжҳҜдёҖйҰ–еңЁжү№иҜ„еҸІдёҠжІЎжңүеҫ—еҲ°и¶іеӨҹйҮҚи§Ҷзҡ„жқ°дҪң пјҢ е…¶дёӯзҡ„зҺ«з‘°ж„ҸиұЎдёҚд»…дҪ“зҺ°д»–еҜ№и”·и–ҮеҚҒеӯ—дјҡзӯүзҺ„еӯҰжҖқжҪ®зҡ„жҺўзҙўе’ҢеҸҚзңҒ пјҢ д№ҹеңЁиҜҚиҜӯзҡ„иҠұз“ЈдёӯиҲ’еҚ·зқҖиҜ—дәәеҜ№з»Ҳз”ҹжҢҡзҲұиҺ«еҫ·В·еҶҲMaud Gonneзҡ„е‘је”ӨгҖҒеҜ№ж•…д№ЎеӨҚжқӮиҖҢж·ұйҮҚзҡ„ж„ҹжғ… пјҢ д»ҘеҸҠжёҙжңӣе®ҡд№үзҲұе°”е…°ж°‘ж—ҸзІҫзҘһзҡ„ж–ҮеӯҰйҮҺеҝғ гҖӮ вҖңзәўзҺ«з‘° пјҢ йӘ„еӮІзҡ„зҺ«з‘° пјҢ жҲ‘дёҖеҲҮж—¶ж—Ҙзҡ„жӮІдјӨзҺ«з‘°пјҒвҖқвҖ”жң¬иҜ—дёӯзҡ„зҺ«з‘°дёҚд»…е°ҶжүҖжңүзҡ„зҫҺз»јеҗҲдәҺдёҖдёӘж„ҸиұЎ пјҢ жҲҗдёәвҖңж°ёжҒ’дёҚжңҪзҡ„зҫҺвҖқзҡ„еҢ–иә« пјҢ жӣҙеҮ д№ҺжҲҗдёәдёҖеҲҮеҙҮй«ҳе’ҢеҖјеҫ—жёҙжңӣд№ӢдәӢзҡ„з¬ҰеҸ· пјҢ дёҖдёӘжүҖжңүзҡ„дёҠеҚҮд№ӢеҠӣжұҮиҒҡзҡ„иҪҙеҝғ пјҢ дёҖз§ҚвҖңиұЎеҫҒеӯҰзҡ„иұЎеҫҒвҖқ гҖӮ дёҖеҰӮеҸ¶иҠқеңЁ1925е№ҙзҡ„笔记дёӯжүҖиЁҖпјҡвҖңгҖҠзҺ«з‘°йӣҶгҖӢдёӯиў«иұЎеҫҒзҡ„е“ҒиҙЁдёҺйӣӘиҺұзҡ„жҷәжҖ§д№ӢзҫҺдёҚеҗҢвҖҰвҖҰжҲ‘жғіиұЎе®ғ
пјҲзҺ«з‘°пјү
дёҺдәәзұ»е…ұеҗҢеҸ—иӢҰ пјҢ иҖҢдёҚжҳҜжҹҗз§Қд»ҺиҝңеӨ„иў«иҝҪжұӮе’Ңзңәжңӣзҡ„дёңиҘҝ гҖӮ вҖқгҖҠиҮҙж—¶й—ҙеҚҒеӯ—жһ¶д№ӢдёҠзҡ„зҺ«з‘°гҖӢејҖзҜҮзҡ„гҖҠзҺ«з‘°йӣҶгҖӢдёӯ пјҢ зҺ«з‘°дёҺеҚҒеӯ—жһ¶еҪјжӯӨж¶ҲејӯдёәдёҖз§Қж— йҷҗзҡ„жҡ—зӨәжҖ§ пјҢ йҳҙйҳізӣёзі… пјҢ е…ғзҙ дәӨиһҚ пјҢ жҳ“жңҪзҡ„зҺ«з‘°з»Ҹз”ұвҖңеҚҒеӯ—жһ¶еҢ–вҖқиҖҢи¶…и¶Ҡж—¶й—ҙ гҖӮ еҹғжҹҜжүҖи°“вҖңжҳ”ж—ҘзҺ«з‘°д»Ҙе…¶еҗҚжөҒиҠі пјҢ д»ҠдәәжүҖжҢҒе”ҜзҺ«з‘°д№ӢеҗҚвҖқеңЁеҸ¶иҠқиҝҷйҮҢ并жңӘеҸ‘з”ҹ пјҢ еӣ дёәеҸ¶иҠқзҡ„зҺ«з‘°е·ІеҚҮеҚҺдёәдёҖз§ҚжҺўзҙўзңҹзҗҶзҡ„еҠЁжҖҒиғҪйҮҸ пјҢ жҳҜе°ҡжңӘиң•еҢ–жҲҗдёҖдёӘеҗҚиҜҚзҡ„гҖҒдёҖжңөдёҚж–ӯвҖңзҺ«з‘°зқҖвҖқзҡ„вҖңе…ғзҺ«з‘°вҖқ гҖӮ
дёҚеҰЁд»Ҙ20дё–зәӘзҫҺеӣҪеҘідҪңе®¶ж јзү№йІҒеҫ·В·ж–Ҝжі°еӣ Gertrude SteinгҖҠзҘһеңЈиүҫзұіиҺүгҖӢSacred EmilyдёҖиҜ—дёӯзҡ„вҖңзҺ«з‘°з»•еҸЈд»ӨвҖқжқҘз»“жқҹиҝҷеңәеҢҶеҝҷзҡ„зҺ«з‘°д№Ӣж—…пјҡRose is 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
пјҲвҖңзҺ«з‘°жҳҜдёҖжңөзҺ«з‘°жҳҜдёҖжңөзҺ«з‘°жҳҜдёҖжңөзҺ«з‘°вҖқпјү
гҖӮ ж–Ҝжі°еӣ иҜ—дёӯзҡ„第дёҖдёӘRoseжҳҜдёҖдҪҚеҘіжҖ§зҡ„еҗҚеӯ— пјҢ еӣ иҖҢиҜҘеҸҘеёёиў«йҳҗйҮҠдёәпјҡд»…д»…жҳҜе–ҠеҮәдәӢзү©зҡ„еҗҚеӯ— пјҢ е°ұиғҪе”Өиө·дёҺд№ӢзӣёиҒ”зҡ„жүҖжңүзҡ„ж„ҸиұЎе’Ңжғ…ж„ҹ гҖӮ е·Із»Ҹжө®е…үжҺ еҪұең°зҝ»иҝҮе…ӯзҷҫеӨҡе№ҙвҖңзҺ«з‘°иҜ—е°ҸеҸІвҖқзҡ„жҲ‘们еҪ“然дјҡи®°еҫ— пјҢ вҖңRoseвҖқжҳҜзҺ«з‘°д№ӢеҗҚд№ҹжҳҜзҺ«з‘°зҡ„еҪұеӯҗ пјҢ жҳҜжүҖжңүиҜӯиЁҖдёӯвҖңзҺ«з‘°жҖ§вҖқзҡ„еҪјжӯӨжҝҖиҚЎе’Ңжј«й•ҝеӣһе“Қ пјҢ жҳҜдёҖеҲҮеұһзҺ«з‘°д№Ӣзү©зҡ„з»Ҳе°Ҷе®һзҺ°зҡ„жҪңиғҪ пјҢ жҳҜдёҖжңөзҺ«з‘° пјҢ д№ҹжҳҜе…ЁйғЁзҡ„зҺ«з‘° гҖӮ
еҺҹдҪңиҖ…дёЁеҢ…ж…§жҖЎ
ж‘ҳзј–дёЁи‘Јзү§еӯң
еҢ…ж…§жҖЎпјҡиҘҝж–№ж–ҮеӯҰдёӯзҡ„вҖңзҺ«з‘°вҖқж„ҸиұЎпјҢжҳҜиҜ—дәә们й•ҝд№…зҡ„з§ҳеҜҶгҖӮ
жҺЁиҚҗйҳ…иҜ»
- еҒҡдҪ дёҖиҫҲеӯҗзҡ„иңЎз¬”|иҘҝж–№дёәд»Җд№ҲдёҚеҒҮжҖқзҙўзҡ„жұЎи”‘дёӯеӣҪпјҹеӣ дёәжҲ‘们зҡ„иҝҷдёӘй”ҷиҜҜпјҒ
- зҺҜзҗғж—¶жҠҘж–°еӘ’дҪ“|дёҖйў—е°ҸиЎҢжҳҹеҸҜиғҪе°Ҷж’һеҮ»ең°зҗғпјҢзҫҺеӣҪзҹҘеҗҚеӨ©ж–ҮеӯҰ家жҺЁзү№еҸ‘ж–ҮпјҡзҫҺеӨ§йҖүеүҚдёҖеӨ©
- е…«еҚҰзҲҶж–ҷ|еҺҹеҲӣжҳҺжҳҹеҲҶжүӢж–ҮжЎҲеӨ§жҜ”жӢјпјҢд»»иұӘзҺ©дјӨж„ҹж–ҮеӯҰпјҢжқҺжҷЁжҗһеүҚеҗҺе‘јеә”
- еҪұи§ҶеҸЈзў‘жҰң|жҳҺжҳҹеҲҶжүӢж–ҮжЎҲеӨ§жҜ”жӢјпјҢд»»иұӘзҺ©дјӨж„ҹж–ҮеӯҰпјҢжқҺжҷЁжҗһеүҚеҗҺе‘јеә”
- жө·еӨ–зҪ‘|зҫҺзҹҘеҗҚеӨ©ж–ҮеӯҰ家пјҡе°ҸиЎҢжҳҹеҸҜиғҪеңЁзҫҺеӨ§йҖүеүҚдёҖеӨ©ж’һеҮ»ең°зҗғ
- дҝ„иҜӯеӨ§дё–з•Ң|ж ёи®№иҜҲпјҹд№ҢеҶӣдёҠе°Ҷе–ҠиҜқиҘҝж–№еӣҪ家пјҡеҲ«йҖјжҲ‘们йҮҚеҗҜж ёжӯҰи®ЎеҲ’
- иүҜжҙҒеЁұд№җ|иҘҝж–№дёәдҪ•иҝҳжҳҜе®іжҖ•дёӯеӣҪеҙӣиө·дё“家жңү4дёӘеҺҹеӣ пјҢдёӯиҘҝеҗҲдҪңеӨҡж¬Ў
- йӮӘжҒ¶д№Ӣеҫ’|жөҷжұҹдёҖеҫӢеёҲиҫ©жҠӨж„Ҹи§Ғдёӯ称委жүҳдәәжҳҜвҖңйӮӘжҒ¶д№Ӣеҫ’вҖқ еҫӢжүҖпјҡжҳҜж–ҮеӯҰдҪңе“Ғ
- ж–°еҚҺзӨҫ|зҫҺеӘ’пјҡж— и§ҶдәҡеӨӘжҠ—з–«з»ҸйӘҢпјҢиҘҝж–№вҖңжёҗжёҗжәәдәЎвҖқ
- жІҷжј йҮҢзҡ„и“қзҺ«з‘°|еҲәз—ӣиҘҝж–№еӣҪ家зҡ„зҘһз»ҸпјҢзҫҺеӘ’еҲ—еҮәеӨұиҙҘеҺҹеӣ пјҢдёӯеӨ–еҜ№жҜ”йІңжҳ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