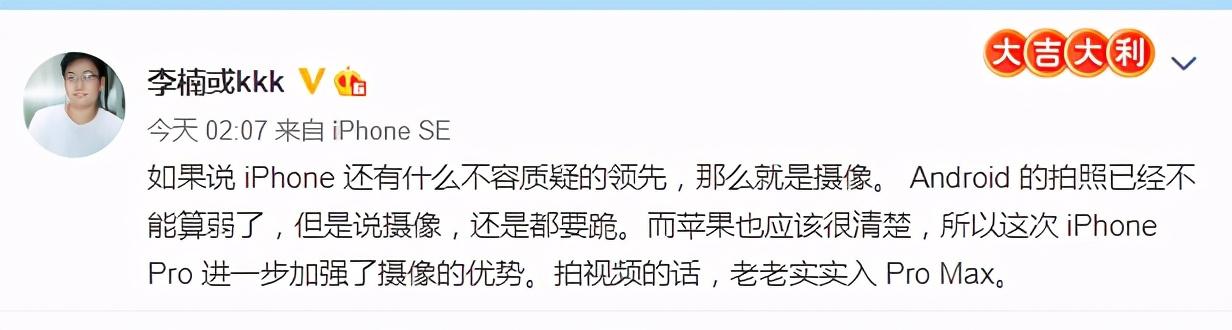光明网|家在“和平”住(图)
_本文原题:家在“和平”住(图)
本文插图
【光明网|家在“和平”住(图)】
我曾经有两个家 , 都在和平区 。 父母家在长沙路求志里;另一个家在慎益大街四箴里 。 求志里至今犹在 , 而四箴里早已拆除 , 建成了南市食品街 。 小时候 , 父母是双职工 , 我生下五十多天的样子 , 便被托付给四箴里胡同里一位老人看护 , 我始终管她称“奶奶” 。 直到二十多岁那年 , 奶奶病故 , 我才回到求志里的父母身边 。
可以说 , 我的人生是从四箴里胡同那个大杂院开始的 。 大杂院有三多:住户多 , 家庭妇女多 , 孩子多 。 这里民风淳朴 , 60户街坊邻居亲如家人 。 但是 , 大多数家庭都不怎么富裕 , 日子过的十分困窘 。 尤其孩子多的家仅靠父亲一人挣工资 , 生活更显艰难 。 我的同学孙君家里有自行车 , “双喜”牌 , 八成新 , 常骑出来显摆 。 我们几个同学抢他家的车在大马路练着骑 。 孙君笨 , 同学们都练会了 , 他的骑术却二五眼 。 一次同学们从海河游泳回来 , 骑车驶入人群汹涌的清和街 , 孙君慌里慌张地摇晃车把 , 大老远叫喊前面一位慢吞吞走着的老人:大爷 , 大爷──叫声未落 , “咣”一下撞趴下那位大爷 。 从此,我们嘲笑孙君“指哪儿打哪儿” 。 如今孙老兄“鸟枪换炮” , 60岁开外的人开一辆标致牌轿车满街乱蹿 , 还常常搭帮结伙地开车出去远游 , 幸福的笑容在老脸上花一样绽放 。
想当年汽车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 , 绝对是稀罕物 , 每天清晨只有一辆收垃圾的“解放牌”卡车停靠胡同口 , 收完各家各户的垃圾又开走 。 几乎见不着小轿车 , 偶尔见到驶过辆轿车 , 成群的孩子追后边跑 。 高高的天空飞过一架飞机 , 孩子们会边跑边喊 , 穿越狭窄的马路狂奔 , 飞机瞬间没了影子 , 孩子们眼中涌满怅然若失的神情 。
记忆中的南市道路相当狭窄 , 老旧平房居多 , 人们的居住条件也差 。 拿我居住的大杂院说吧 , 通常一家五六口人挤在十平米左右的小屋 , 晚上睡觉要临时搭床板 , 拼成床 。 或者在床上搭“阁楼” , 生生扩出点生存空间 。 洗澡去玉清池澡堂子 , 解手四处找公共茅房 。 夏天最难熬 , 小房间臭虫满墙爬 , 蚊子漫天飞 , 而且溽热难耐 , 人们就扛着木板凳子 , 拎着马扎到马路待一宿 。 后来我上班了 , 因工作关系经常出差 , 住两人的标间 。 客房带卫生间 , 装窗式空调 , 洗澡、解手、驱暑皆便利 。 当时我缺乏想象力 , 曾盼着:将来能住上带卫生间、装空调的房子该多好啊 。 改革开放之后变化实在大 , 人们纷纷搬进带卫生间的单元房 , 有的住进高层建筑 , 上下楼有电梯 。
南市一带今非昔比 , 高楼耸立 , 马路宽阔 , 已难识旧时模样 。 一次 , 我和邻居老友相约见面 , 他也是老同学 , 一块在大舞台小学上学 , 大舞台小学改成“五七中学” , 我俩同时在此上初中 。 中学毕业分配了不同工作 , 虽同居一座城市 , 却各居一方 。 后来有热心者组织老同学聚会才重新建立起联系 。 那天我竟然在高楼大厦的丛林中迷失了方向 , 找不到旧时的地点 。 两人从相隔不远的地方用手机联系 , 最后决定在百货大楼对面的新华书店见面 。 幸好 , 新华书店依然是过去的地方 。 仰望高台阶上的书店 , 不禁想起与书的一段情缘 。
令人难忘的是1978年五月里一天清晨 。 新华书店门前排着长长的队伍 , 买书的人们或在前夜或凌晨赶来在此守候 , 焦灼地等着书店大门洞开 , 随人潮涌进去 , 抢购新开禁的一批世界名著 。 我是其中一份子 。 “十年浩劫”使文化沦落成荒漠 , 中外名著遭禁 , 新华书店空空如也 。 改革开放初期 , 思想文化打破禁忌 , 一批文学名著付梓出版 , 让多少人翘首以望 。 人们在五月晨光照耀下等待 , 一种心灵释放出来的喜悦洋溢在脸庞 。
推荐阅读
- 和平精英|和平精英:国际服载具皮肤大赏,最后两款宝马皮肤不输特斯拉!
- 美军|塔利班指责美方违反和平协议轰炸非战斗区,驻阿富汗美军否认
- 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为了和平》第四集《英雄赞歌》
- 热点游戏|和平精英新赛季开启,虎牙虎牙包子手感火热,玛莎拉蒂1v4灭队
- 电竞小肥仔|和平精英:战队专属皮肤推荐合集,最后JDE队服堪比至尊金龙!
-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血性迸发!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为了和平》第三集、第四集来了!
- 游人馆|和平精英:4AM成功晋级PEL决赛,有几个数据还是蛮有意思的
- 青年|和平精英游戏隐藏有保底击杀告别零杀吃鸡的尴尬局面!
- 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为了和平》第三集《血性迸发》
- 光明网|年薪百万聘校长,能一劳永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