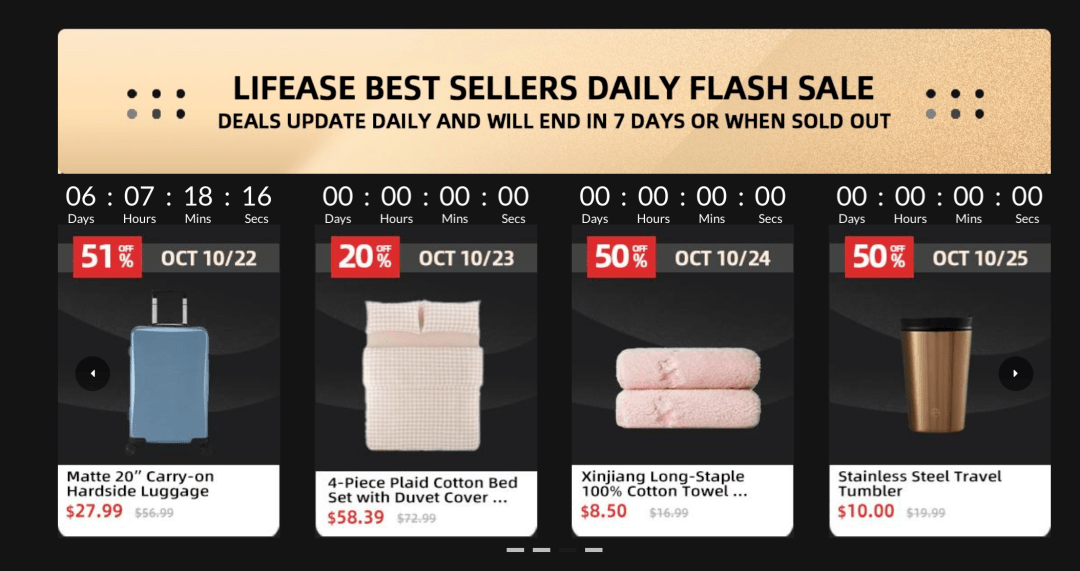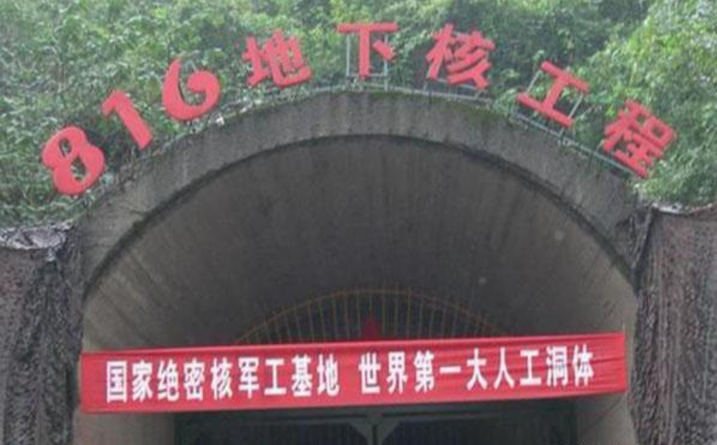зҲ¶дәІ|йЈҺиҜҙдәҶеҫҲеӨҡ жҠҠеӨҸеӨ©жіЁеҫ—зӣҲж»Ў( дәҢ )
иҝҷжҳҜ第дёҖж¬ЎзңӢзҲ¶дәІз”»з”» пјҢ дёӨдёӘзҫҺзҢҙзҺӢиә«жҠ«йҮ‘иүІзӣ”з”І пјҢ еӨҙйЎ¶й•ҝзҝҺзҫҪеҶ пјҢ жүӢжү§дёӨз«Ҝ镶йҮ‘зәўиүІзҡ„йҮ‘з®ҚжЈ’ пјҢ и…ҫдә‘й©ҫйӣҫй…ЈжҲҳеҫ—йҡҫи§ЈйҡҫеҲҶ гҖӮеңЁзҲ¶дәІзҡ„еҪұе“ҚдёӢ пјҢ жҲ‘еҜ№з»ҳз”»жӣҙжңүдәҶдёҖеҲҶеҒҸзҲұ гҖӮзҲ¶дәІжӢ…д»»ж•ҷеҠЎеӨ„еүҜеӨ„й•ҝж—¶е°ұеңЁж ЎйўҶеҜјжүҖеңЁзҡ„е·Ҙеӯ—еҺ…еҠһе…¬ гҖӮйӮЈж—¶зҡ„е·Ҙеӯ—еҺ…жҳҜејҖж”ҫзҡ„ пјҢ йҷўеӯҗйҮҢдёӨеӨ„еҒҮеұұеҗҺеҗ„жңүдёҖж Әжө·жЈ пјҢ иҝҳжңүеҗ„йҷўд№Ӣй—ҙжӣІжҠҳзҡ„иҝһе»Ҡ пјҢ ж—¶еёёжңүдәәз…§зӣё гҖӮжҲ‘еҒ¶е°”еҺ»е·Ҙеӯ—еҺ… пјҢ зҲ¶дәІжҖ»е‘ҠиҜ«жҲ‘们дёҚиҰҒеңЁйҷўеҶ…е–§е“— гҖӮе…¶е®һжҲ‘并дёҚжҮӮеҫ—ж¬ЈиөҸжё…д»ЈзҺӢеәңеәӯйҷўзҡ„зҫҺжҷҜ пјҢ жӣҙе–ңж¬ўзҡ„жҳҜй—ЁеүҚзҡ„дёӨдёӘзҹізӢ® пјҢ 并д»Һе°Ҹе°ұзҹҘйҒ“дәҶи„ҡиё©з»Јзҗғзҡ„жҳҜе…¬зӢ® пјҢ и„ҡиёҸе°ҸзӢ®еӯҗжҲҸиҖҚзҡ„жҳҜжҜҚзӢ® гҖӮеңЁзҲ¶дәІзҡ„йј“еҠұдёӢ пјҢ жҲ‘иҝҳжӣҫе’Ңе°ҸеӯҰеҗҢеӯҰиҮӘе·ұжҗ¬дёӘе°Ҹ马жүҺеқҗеңЁе·Ҙеӯ—еҺ…й—ЁеҸЈ пјҢ еғҸжЁЎеғҸж ·ең°з”»зҹізӢ®зҡ„еҶҷз”ҹ гҖӮ
иҝҳжңүзҡ„зҫҺеҘҪи®°еҝҶжҳҜй«ҳж Ўж•ҷиҒҢе·Ҙзҡ„дј‘еҒҮз–—е…» гҖӮи®°еҫ—дёҖ家дәәжӣҫеңЁиҘҝеұұз–—е…»ең°е’Ңйўҗе’Ңеӣӯе°ҸдҪҸ гҖӮйӮЈж—¶дҪҸеңЁеҚҒдёғеӯ”жЎҘиҝһжҺҘзҡ„еҚ—ж№–еІӣж¶өиҷҡе Ӯ пјҢ ж—Ғиҫ№жңүдёӘйҫҷзҺӢеәҷ пјҢ дёҚејҖй—Ё пјҢ жӣҫжү’й—ЁзјқзңӢеҲ°йҮҢйқўйқўзӣ®зӢ°зӢһзҡ„йҫҷзҺӢеқҗеғҸ пјҢ дёҖеҲ°жҷҡдёҠд»ҺйӮЈйҮҢз»ҸиҝҮе°ұж„ҹи§үйҳҙжЈ®жЈ®зҡ„ гҖӮжё…жҷЁе’ҢзҲ¶дәІеҮәй—Ёж•ЈжӯҘ пјҢ зңӢеҲ°жңүдәәй’“йұј пјҢ жңүдәәдёӢжЈӢ пјҢ йғҪжҳҜжҘјдёҠжҘјдёӢзҡ„зҶҹдәә гҖӮ
д»Һе°Ҹе°ұжҖ•зҲ¶дәІжүҫжҲ‘и°ҲиҜқ
еӣ дёәеӨӘж— и¶Ј
зҲ¶дәІжҳҜдёӘдёҚж“…дәӨйҷ…зҡ„дәә пјҢ зў°еҲ°зҶҹдәәзӮ№зӮ№еӨҙиҖҢе·І гҖӮеҒ¶е°”еёҰжҲ‘еҺ»дёІй—Ёд№ҹжҳҜи°Ҳе·ҘдҪң пјҢ дјјд№Һд»ҺжңӘеҸӮеҠ иҝҮд»Җд№ҲзӨҫдәӨеңәеҗҲ пјҢ и·ҹеҲ«дәәд»Ӣз»ҚжҲ‘ж—¶иҝҳжҖ»иҜҙвҖңзҠ¬еӯҗвҖқ пјҢ и®©жҲ‘жҢәдёҚзҲұеҗ¬ гҖӮиҝҷзӮ№е’ҢеӨ–еҗ‘еһӢзҡ„жҜҚдәІеҸҚе·®еҫҲеӨ§ пјҢ еҹәжң¬дёҠеҜ№еӨ–зҡ„еә”й…¬йғҪжҳҜжҜҚдәІ гҖӮд»Һе°Ҹе°ұжҖ•зҲ¶дәІжүҫжҲ‘и°ҲиҜқ пјҢ еҖ’дёҚжҳҜеӣ дёәд»–дёҘеҺү пјҢ иҖҢжҳҜеӣ дёәеӨӘж— и¶Ј пјҢ еӨӘдёҖжң¬жӯЈз»Ҹ пјҢ д№ҹеҸҜиғҪзҲ¶еӯҗй—ҙйғҪжҳҜеҰӮжӯӨпјҹиҖҢжҜҚдәІеҲҷе№іжҳ“иҝ‘дәә пјҢ еҚідҪҝжү№иҜ„д№ҹд»ҺжңӘи®©жҲ‘жңүиҝҮжҠөи§ҰеҝғзҗҶ гҖӮ
зҲ¶жҜҚж„ҹжғ…дёҚе’ҢдҪҝ他们зҡ„е©ҡ姻еҮәзҺ°иЈӮз—• пјҢ е°Ҫз®ЎдёәдәҶеӯ©еӯҗжҲҗй•ҝжІЎжңүиө°еҲ°зҰ»е©ҡиҝҷдёҖжӯҘ пјҢ дҪҶд»Һе°ҸеӯҰе°ұејҖе§Ӣзҡ„еҲҶеұ…зҠ¶жҖҒдҪҝжҲ‘зҡ„жҖ§ж јеҫҲж•Ҹж„ҹ гҖӮиҖҢеҜ№жҜҚдәІзҡ„еҗҢжғ…дҪҝжҲ‘йҖҗжёҗз–ҸиҝңдәҶзҲ¶дәІ пјҢ з”ҡиҮіжӯЈеҖјйҖҶеҸҚжңҹзҡ„жҲ‘ејҖе§ӢжҖЁжҒЁзҲ¶дәІ пјҢ еҸҚжҠ—зҲ¶дәІ гҖӮ
еңЁиҝҷз§Қ家еәӯж°ӣеӣҙдёӢ пјҢ зҲ¶дәІеңЁе®¶йҮҢи¶ҠжқҘи¶Ҡе°‘иЁҖеҜЎиҜӯ гҖӮз”ұдәҺеҮәиә«дёҚеҘҪ пјҢ дәІжҲҡд№Ӣй—ҙеҫҲе°‘жқҘеҫҖ пјҢ еҒ¶е°”зҲ¶дәІжү“з”өиҜқз”ЁжұҹжөҷдёҖеёҰж–№иЁҖ пјҢ жҲ‘е°ұзҹҘйҒ“д»–жҳҜе’ҢжҹҗдёӘдәІжҲҡйҖҡиҜқ пјҢ дёҚеҸӘжҳҜжҲ‘们 пјҢ жҒҗжҖ•иҝһжҜҚдәІд№ҹдёҖеҸҘиҜқйғҪеҗ¬дёҚжҮӮ гҖӮ
жІЎеҮ е№ҙзҡ„е·ҘеӨ« пјҢ вҖңж–Үйқ©вҖқејҖе§ӢдәҶ гҖӮзҲ¶дәІзҷҪеӨ©жҢӮдёӘеҗҚеӯ—дёҠжү“дәҶеҸүеӯҗзҡ„зүҢеӯҗеңЁж ЎеӣӯжҢҮе®ҡеҢәеҹҹжӢ”иҚү пјҢ жҷҡдёҠдёҖдёӘдәәй—·еңЁе°ҸеҗҺеұӢйҮҢеҶҷдәӨд»Јжқҗж–ҷ гҖӮжң¬жқҘе°ұиҜқдёҚеӨҡзҡ„зҲ¶дәІжӣҙеҠ жІүй»ҳеҜЎиЁҖ пјҢ дёҖж®өж—¶й—ҙз”ҡиҮіиЎЁжғ…жңЁи®·е‘Ҷж»һ гҖӮжҜҚдәІд№ҹеҫҲзҙ§еј пјҢ и®©жҲ‘们没дәӢеӨҡе’ҢзҲ¶дәІиҜҙиҜҙиҜқ пјҢ жҖ•д»–еҶ…еҝ§еӨ–еӣ°жғідёҚејҖ гҖӮ
иҷҪ然зҲ¶дәІзҡ„еҮәиә«е’ҢеҸҚеҠЁеӯҰжңҜжқғеЁҒзҡ„еёҪеӯҗз»ҷжҲ‘еҸӮеҠ вҖңйқ©е‘ҪвҖқиҝҗеҠЁеёҰжқҘдәҶйҳ»еҠӣ пјҢ дҪҶ并没жңүеҸ—еҲ°еӨҡеӨ§дјӨе®і пјҢ жүҖд»ҘжҲ‘еҖ’е°‘жңүеӣ дёәзҲ¶дәІзҡ„еҮәиә«е’Ңж”ҝжІ»зҠ¶еҶөиҖҢжҖЁжҒЁзҲ¶дәІ пјҢ еҸҚеҖ’жңүдәӣеҗҢжғ…е’ҢеҸҜжҖңд»– гҖӮжҲ‘д»ҺдёҚеҺ»зңӢжү№еҲӨзҲ¶дәІзҡ„еӨ§еӯ—жҠҘ пјҢ д№ҹжҖ•еҲ«зҡ„е°ҸдјҷдјҙеҺ»зңӢ гҖӮ
дёҠеұұдёӢд№ЎжҲ‘жҳҜиҮӘе·ұжҠҘеҗҚеҺ»зҡ„ пјҢ дёҖжқҘжҳҜеұҘиЎҢжҲ‘еҜ№жңӢеҸӢзҡ„жүҝиҜәпјҲд»–иў«еҲҶеҺ»жҲ‘е°ұйҷӘд»–пјү пјҢ дәҢжқҘд№ҹжҳҜжғізҰ»ејҖиҝҷдёӘжңүзӮ№е„ҝд»ӨдәәзӘ’жҒҜзҡ„家 гҖӮ1969е№ҙжҲ‘е’Ңе§җе§җдёҖеҗҢеҺ»дәҶ延е®үжҸ’йҳҹ пјҢ зҲ¶дәІд№ҹеңЁеҗҢе№ҙеҺ»дәҶжё…еҚҺеӨ§еӯҰеңЁжұҹиҘҝйІӨйұјжҙІеҠһзҡ„дә”дёғе№Іж Ў гҖӮзҲ¶дәІеңЁе№Іж ЎеҘҪеғҸжҳҜеңЁйҘІе–Ӯиҝһ пјҢ еҸҲе–ӮзҢӘеҸҲз§ҚиҸң гҖӮжӣҫи§ҒиҝҮдёҖеј з…§зүҮдёҠпјҲеҸҜжғңжІЎжүҫеҲ°пјүзҲ¶дәІеӨ§иЈӨиЎ©е°ҸиғҢеҝғжӢ…дёӨеӨ§жЎ¶зІӘеҫҖиҸңең°йҮҢйҖҒ пјҢ иғіиҶҠе°Ҹи…ҝиӮҢиӮүеҸ‘иҫҫ пјҢ и…°дёҚејҜиғҢдёҚй©ј пјҢ дјјд№ҺиҝҳжҢәиҪ»жқҫ пјҢ дёҚиҝҮе№ІиҝҮеҶңжҙ»зҡ„жҲ‘дёҖзңӢе°ұзҹҘйҒ“иҮіе°‘еҫ—жңүдёғе…«еҚҒж–Ө гҖӮеӣ дёәиЎҖеҗёиҷ«з—… пјҢ 1972е№ҙеҲқеҢ—еӨ§жё…еҚҺйғҪж’ӨеӣһжқҘдәҶ пјҢ зҲ¶дәІд№ҹеңЁйӮЈйҮҢиў«ж„ҹжҹ“дәҶиЎҖеҗёиҷ«з—… пјҢ еҘҪеңЁжҜ”иҫғиҪ» пјҢ еңЁеҪ“ең°жІ»з–—дёҖе‘Ёе°ұеҘҪдәҶ гҖӮжҸ’йҳҹдёүе№ҙжқҘ全家еӨҙдёҖж¬ЎиҒҡеңЁдёҖиө· пјҢ 并еңЁжҘјдёӢз…§дәҶдёҖеј зӣё гҖӮи®°еҫ—зҲ¶дәІйӮЈе№ҙзңӢеҲ°жҸ’йҳҹдёүе№ҙеӨҡзҡ„жҲ‘е·Із»Ҹй•ҝжҲҗеҸҲй«ҳеҸҲеЈ®зҡ„еӨ§е°Ҹдјҷеӯҗ пјҢ жҸҗеҮәе’ҢжҲ‘жҺ°жүӢи…• гҖӮжӯЈеҖј48еІҒеЈ®е№ҙзҡ„зҲ¶дәІе·ІжҺ°дёҚиҝҮ20еІҒзҡ„жҲ‘ пјҢ дёҚзҰҒж„ҹж…ЁйҒ“пјҡвҖңе”ү пјҢ дёҚжңҚиҖҒдёҚиЎҢе•ҰпјҒвҖқиҜқиҜӯдёӯжңүж— еҘҲ пјҢ жӣҙеӨҡзҡ„жҳҜйӘ„еӮІ гҖӮ
еӨҚд№ иҖғиҜ•иҝҮзЁӢдёӯ
第дёҖж¬ЎйўҶж•ҷзҲ¶дәІзҡ„ж•ҷеӯҰйЈҺиҢғ
1978е№ҙжҲ‘иҖғдёҠдәҶеӨ§еӯҰ пјҢ зҲ¶дәІжІЎе°‘еҮәеҠӣ пјҢ йҷӨдәҶе°ҪеҸҜиғҪеӨҡең°жүҫеҲ°еҗ„еҢәеҗ„зңҒзҡ„иҜ•йўҳ пјҢ иҝҳзү№ж„ҸжүҫдәҶдёҖдёӘеҢ–еӯҰиҜ•йӘҢиҖҒеёҲз»ҷжҲ‘е’ҢеҰ№еҰ№иЎҘиҜ•йӘҢиҜҫ гҖӮеӨҚд№ иҖғиҜ•зҡ„иҝҮзЁӢдёӯ пјҢ жҲ‘第дёҖж¬ЎйўҶж•ҷдәҶзҲ¶дәІж•ҷеӯҰзҡ„йЈҺиҢғ гҖӮеҪ“жҲ‘еңЁеҠӣеӯҰж–№йқўжңүй—®йўҳйңҖиҰҒд»–её®еҠ©ж—¶ пјҢ д»–д»ҺдёҚ马дёҠеӣһзӯ” пјҢ иҖҢжҳҜй—®жҲ‘зҡ„жҖқи·Ҝ гҖӮеҗҜеҸ‘еј•еҜјжҲ‘д»ҺеҠӣеӯҰеҹәжң¬жҖ§иҙЁе’ҢеҺҹзҗҶеҮәеҸ‘ пјҢ е…ҲжҠҠеҸ—еҠӣеӣҫз”»еҮәжқҘ пјҢ иҝҷж ·дјҡдҪҝжҜҸдёҖжһ„件зҡ„еҸ—еҠӣе…ізі»зңӢеҫ—жҳҺжҳҺзҷҪзҷҪ пјҢ жңүеҠ©дәҺзҗҶжё…и§ЈйўҳжҖқи·Ҝ гҖӮеҚідҪҝжҲ‘е·ІжҳҺзҷҪжҖҺд№ҲеҒҡ пјҢ зҲ¶дәІдҫқ然让жҲ‘з”»еӣҫ пјҢ и°ҲжҖқи·Ҝ пјҢ д»ҺиҖҢе…»жҲҗиүҜеҘҪд№ жғҜ гҖӮ
жҺЁиҚҗйҳ…иҜ»
- е…¬еӯҗ|жІҷжәўеҗғйҘӯж—¶дёҚи®ӨиҜҶвҖңйұјйңІвҖқпјҢи°Ғеҗ¬еҲ°йғӯйә’йәҹиҜҙдәҶе•ҘдёҚ愧жҳҜеҜҢ家公еӯҗ
- зӢ¬иҮӘеҫ’жӯҘзҲ¬иӢҚеұұеӨұиҒ”5еӨ©дёҖдәӢпјҢзҲ¶дәІдёҖжқЎжңӢеҸӢеңҲд»Өдәәз—ӣеҝғпјҢ4000зұіжӮ¬еҙ–жҗңж•‘з”»йқўжӣқе…ү
- жҳҺжҳҹе©ҡ姻|зҲ¶дәІдёӯйЈҺгҖҒе“Ҙе“ҘеҺ»дё–зҡ„еӯҹеәӯиӢҮпјҢжң¬иҷ”еҝғеҗ‘дҪӣпјҢеҚҙе«Ғз»ҷеҗҢеӯҰй…ҝжҲҗжӮІеү§
- зәўеҲҠиҙўз»Ҹ|ж јйӣ·иө„дә§еј еҸҜе…ҙпјҡдјҳиҙЁиӮЎеҺҶеҸІдҪҺзӮ№еҸҜиғҪж°ёиҝңзӯүдёҚеҲ°пјҢеҗҲзҗҶжҢҒжңүд№ҹжҳҜдёҖдёӘйҖүйЎ№пјҢзүӣеёӮз–ҜзӢӮжңҹеҫҲеӨҡдёӘиӮЎйғҪжҳҜдёҠзҷҫеҖҚеёӮзӣҲзҺҮ
- жқҺжҷЁ|и‘ЈеҸҲйң–жә…дәҶи”ЎеҫҗеқӨдёҖи„ёзҡ„жіҘпјҢжңүи°ҒжіЁж„ҸеҲ°и”ЎеҫҗеқӨиҜҙдәҶе•ҘпјҹйҡҫжҖӘжқҺжҷЁеҮәеЈ°вҖңи®ӯж–ҘвҖқ
- ж„ҝе№іе®үпјҒеұұиҘҝдёҙжұҫдёҖйҘӯеә—еқҚеЎҢ еәҹеўҹдёӢзҲ¶дәІз«ӯеҠӣжҠӨдҪҸеӯ©еӯҗ
- йҖҡзҹҘд№Ұ|зҲ¶дәІж”¶еҲ°е„ҝеӯҗеҪ•еҸ–йҖҡзҹҘд№ҰеҪ“иЎ—ж¬ўе‘јпјҢеҚ—ејҖеӣһеә”вҶ’
- е°ҸдјҷзӢ¬иҮӘеҫ’жӯҘеӨұиҒ”5еӨ©еҗҺпјҢзҲ¶дәІдёҖжқЎжңӢеҸӢеңҲд»Өдәәз—ӣеҝғпјҒ4000зұіжӮ¬еҙ–жҗңж•‘з”»йқўжӣқе…ү
- 科еӯҰ|既然жүҖжңүзҡ„з”ҹе‘ҪйғҪиҰҒиө°еҗ‘зҒӯдәЎпјҢйӮЈз”ҹе‘Ҫзҡ„ж„Ҹд№үжҳҜд»Җд№Ҳпјҹ
- 科еӯҰ|既然жүҖжңүзҡ„з”ҹе‘ҪйғҪиҰҒжӯ»дәЎпјҢйӮЈд№Ҳз”ҹе‘Ҫзҡ„ж„Ҹд№үжҳҜд»Җд№Ҳпј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