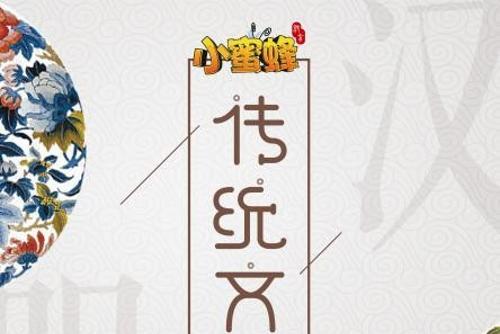李尔王|“李尔王”的命运交响曲
本文图片
冯新平/文
一
薛忆沩的很多作品通常都建立在铺张的研究和苦闷的冥想之上 , 接下来还要等待天赐的灵感以及经受自己苛刻的雕琢 。 长篇《遗弃》《白求恩的孩子们》《空巢》和《希拉里、密和、我》莫不如是 , 《小贩》《首战告捷》《上帝选中的摄影师》《广州暴乱》等诸多短制也同样如此 。 而“经过整整四十年的生活积累 , 经过整整十年的学术准备 , 经过整整十六个月一天都不停顿的孤独攀缘”(薛忆沩语) , 他终于在2020年3月8日中午抵达了自己文学生命里最新的高峰 。 与如此的殚精竭虑和苦心孤诣相对应的是 , 《作家》杂志社的眼光与气魄及其出版的速度与规模:自2020年3月号到5月号 , 《作家》三期连载刊发了薛忆沩的长篇新作《“李尔王”与1979》 。
当生活面临危机或者转机的时候 , 人的心理会有种种奇特的反应 。 善于“乘人之危”的薛忆沩能够很好地将个人内心的奇观与时代纷繁的景象匠心独具地结合起来 。 一位“自愿失业者”一年所写的日记 , 折射出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的精神状况(《遗弃》);一个激进而敏感的大学生被开除之后在南方城市所经历的理智与情感的冲突 , 触及了那个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一个影子的告别》);一个背负命运苛责的中国历史学者写给精神之父白求恩大夫的三十二封长信所建构的历史迷宫 , 涵盖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将近四十年的中国历史(《白求恩的孩子们》);一位遭受电信诈骗空巢老人一天的内心活动 , 所基于的是八十年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历史(《空巢》);一位妻离子散的中国男人与两个异域女子在蒙特利尔皇家山上的冰雪奇缘 , 所展示的是现代人在“全球化”时代的存在困境(《希拉里、密和、我》) 。
从小说名称即可看出 , 《“李尔王”与1979》是一个历经沧桑的悲剧人物适逢一个百废待兴的特殊年份 , 更准确的说法是 , 一个饱受苦难的家庭即将迎来焕然一新的生活 。 如 , 《告台湾同胞书》意味着小女婿的历史问题不再是其报考研究生的现实障碍;中美建交的头条新闻勾起父亲早已烟消云散的美国梦 , 而他视为珍宝的《李尔王》也终于可以重见天日;更为重要的是 , 《人民日报》上题为“中央决定给得到改造的四类分子摘帽”的报道 , 表明父亲终于不用再做“地主”了 , 而他也不用再当“农民”了(他的大女儿会把他接进城里生活) , 如此等等 。 不可思议的1979年在他们渐渐趋于平静的生活中接二连三地掀起了新的波澜 。 而父亲记忆的大门也频繁敞开 , 当年他发誓要统统忘记的经历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滚滚而来......
二
能够完全独立于作者的人物和能够完全独立于人物的作者都是不存在的 。 事实上 , 每一部作品都是作者与人物构成的隐喻 。 小说开篇 , 薛忆沩就开宗明义地写道:“献给我的外公唐振元先生 。 不可思议的1979年生活在湖南省宁乡县历经铺人民公社立新大队第四生产队的‘李尔王’ 。 ”一如他在《空巢》扉页上所写:“献给所有像我母亲那样遭受过电信诈骗的‘空巢’老人 , 那一天的羞辱摧毁了他们一生的虚荣 。 ”后者主人公正是前者“李尔王”的长女原型 。 而二者中的母亲又与薛忆沩的外婆非常相像 。 她有优越的出生、惊人的天赋以及女性特有的智慧 , 却是“封建”和“革命”的双重受害者 。 她在社会的最底层经历了中国现代历史上最根本的变化 。 但她没有被时代的变迁压垮 , 没有被外界的侮辱压垮 , 没有被“没有”压垮 。 这位经受过许多磨难和羞辱的女性却豁达幽默地活到了九十七岁 。 她的经历和性格让薛忆沩坚信精神是不可摧毁的 , 精神是最终的胜利者 。 据薛忆沩讲 , 这部小说里的许多细节都来自外婆惊人的记忆 。
与集智慧和幽默于一身 , 伶牙俐齿、活泼开朗的外婆相反 , 薛忆沩的外公不苟言笑也不善言辞 , 但却同样颇有才华:拥有经济学的本科文凭 , 曾任职于国民政府行政院 , 还擅长体育 , 痴迷京剧 , 通晓英语 。 如此才具与“李尔王”颇为相近 , 而其经历更是与后者如出一辙:外公曾经是沈阳一家大型国营工厂里的会计 。 “四清”之后携全家回到宁乡老家务农 。 他不可能预计到“浩劫”的到来 , 也不会想到他个人的成份有机会由“职员”升格(或者降格)为“地主” , 令“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 。 ”(薛忆沩《一个年代的副本》)作为“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 , 《“李尔王”与1979》中的许多人物和事件都“纯属虚构” , 而那些来自生活的人物和事件也都经过了作者刻意的加工和肢解 , 以符合作品自身的美学需要 。
三
2013年 , 当外婆在长途电话里为薛忆沩一字不漏地背诵出《长恨歌》等一批唐诗之后 , 他激动地写下了《外婆的〈长恨歌〉》 。 这篇随笔通过《读者》杂志让桂花的芬芳飘向了广大的读者 。 两年后 , 在外婆95岁生日的当天 , 《南方都市报》刊出了薛忆沩的短文《最平凡的“中国之最”》 , “桂姐”又一次变成了“公众人物” 。 2017年 , 薛忆沩再次饱含深情地写下了《生死之间的“桂姐”》 。 他想让热爱文字的外婆永远活在他的文字里:“我不知道‘现在’对我外婆意味着什么 。 她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 但是 , 她有过非凡的生命力 。 很多年之后 , 这生命力会让我将她虚构出来 。 她会沿着我的记忆和想象进入一个盘根错节的故事 , 一直回她的祖屋 , 她的出生地……她会通过我的虚构重新开始她的生命 。 我盼望着那个时刻 。 我盼望着在精致的语言里再现她精致的身影和她精致的声音 。 我盼望着她重新认出我来 , 用她的眼睛认出我来 。 ”从叙事的分量来说 , 《“李尔王”与1979》是薛忆沩献给外公的一本书 , 而就情感的浓烈而言 , 它更是一部献给外婆的作品 。
这位非凡的女性有两个非凡的外孙 。 其中一个被授予“法国艺术骑士勋章” , 另一个被人们用“中国文学最迷人的异类”来标识 。 他们曾经是心心相印的少年和相濡以沫的青年 。 后者不仅用随笔《与我相关的“骑士”》来纪念他们之间的友谊 , 而且还将他“画画的表哥”作为“李尔王”二女儿的第二个儿子写入《“李尔王”与1979》 , 而他自己则以“李尔王”大女儿儿子的身份现身其中 。
这位早慧少年与外公的精神交流既有宽广的话题 , 又具备深刻的思想 。 “李尔王”没有想到自己能够从孙辈那里得到那么多的惊喜和那么大的震撼 。 他没有想到这惊喜和震撼能够让他在医院里遭受的挫折感完全烟消云散 。 他甚至觉得这种与“知识”相关的享受自己一生之中只从另外的“两个半”人那里获得过:一个是他参与排练的《李尔王》戏剧中的“肯特”;一个是差点成为自己小女婿的年轻人;而性情古怪的英国诗人只能算“半个” , 因为他们之间毕竟存在着“母语”上的隔阂 , 尽管他是他选中的李尔王 。
四
父亲全神贯注阅读《李尔王》是母亲生活里的场景和常景 , 也成了她生命里挥之不去的疑惑 。 她不懂得让她的夫君入神或者走神的那本“鬼话连篇”的书 , 恰似母亲自己经常吟唱的《木兰辞》《长恨歌》《岳阳楼记》《桃花源记》以及《孟子》和《左传》中的一些章节 。 这些不同的经典在困厄的生活中有着相同的功效: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用“精神胜利法”来支撑自己的理智和脊椎 。
母亲终其一生难成父亲的精神知己 , 而捧着母亲骨灰罐面对村庄的父亲突然意识到 , 不管是他们作为“剥削阶级”生活的世界 , 还是他们成为“专政对象”生活的世界 , 母亲都充满了固执的爱 , “这不受贫富影响 , 不被荣辱干扰也不遭新旧歧视的爱当然就是因为母亲对生活之本和生活之美都有着牢不可破和自始至终的质朴信仰:她相信生活之本和生活之美都来自大地的深处 , 来自井水之纯和井水之甜 , 她相信有井水喝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家......这突然的意识令父亲的全身心立刻充满了暖意和醉意 , 就好像刚刚喝下了一口用最深的井水酿成的美酒 。 ”史诗意味已颇为浓厚的《“李尔王”与1979》因了父亲的顿悟 , 更准确的说法是 , 因了母亲的热爱 , 而臻于更高的境界 。 诚如禅师所言:生命的奥秘在于爱与欢笑 。
《李尔王》是一部人如何因为受难而变成非人的作品 , 但现实中的“李尔王”因了爱的呵护与爱的能力而保有人的品质 。 陪伴他生活将近40年的女人不仅让他没有陷入绝望的深渊(他作为阶级敌人 , 身捆麻绳 , 头戴高帽 , 跪在全体乡亲们的面前) , “因为那温热的水汽 , 因为那温热的抚摸 , 因为那平静却温热的语气” , 而且让他在生命最黑暗的时刻获得对生命最透彻的顿悟(他不再在意“公共空间” , 也开始将面子看得一钱不值) 。 而他与三个女儿彼此之间的“最恨”和“被恨”也并没有损害他们之间天然的爱 。 那是从来就不曾诉诸语言 , 也根本无须诉诸语言的爱 。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 , 渡尽劫波后的父亲不再将那次公审大会看做是自己一生的谷底 , 而只将它当成是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插曲 。 “黑暗不能驱散黑暗 , 只有光明能够 。 恨不能驱散恨 , 只有爱能够 。 ”(马丁·路德·金)《“李尔王”与1979》是一部爱与宽恕之书 。
五
严格来讲 , 每一个写作者的主题都是有限的 , 因此也都在不同程度地“重复自己” 。 这是写作这种事业本身的特点 。 而与其说薛忆沩在用不同的作品来探索同一个主题 , 不如说他始终在践行着文学是人学这一朴素的真理 。 很难用一句话来对薛忆沩的文学作出一览无余的概括 , 但“个人”是他所有作品的主题 。 个人的受难与挣扎 , 个人的屈从与抗争 , 沿着压制、孤独、死亡、爱情等方向投射到个人与历史的关系之中 。 与此同时 , 个人的情绪震颤与灵魂悸动 , 个人的内心世界与隐秘感受又都细致入微地呈现出来 。 而在对历史和心灵的双重开掘中 , 浸润着的是薛忆沩深厚的人道精神与宽广的悲悯情怀 。
虽然专注于“个人”是薛忆沩一直秉承的创作宗旨 , 但在形式上的不断创新也是他信仰的艺术准则 。 他创作的准备过程总是内容等待形式的过程 。 有时候一等就是五年 , 有时候一等就是十年......深圳人系列中的《小贩》更是等待了三十三年才等到它最完美的形式 。 1979年是个不可思议的年份 。 对整个国家来说 , 它可以称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 。 从新年的第一天起 , 它就充满了锐气 , 充满了诚意 , 充满了惊喜 。 而对“李尔王”一家来说 , 1979年更是“翻身之年” , 喜事络绎不绝、应接不暇 。 最大的喜事是“李尔王”作为一家之长的错案获得了完全的平反 。 这意味着长期扣在在这个家庭之上的那顶“帽子”不复存在 , 当然也就意味着这个家庭的成员将来不会再因为有这样一位父亲、岳父和外公而遭受社会的歧视 。 与如此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内容”相对应的是以丰厚现实为基点的“形式” 。
由33节构成的《“李尔王”与1979》以“李尔王”一家在1979年发生的事情为核心 , 各节叙事首尾相连 , 顺序推进 , 而在波澜迭起的现实表层之下是一个家族横跨50年动荡历史的往事洪流 , 与此同时又以莎士比亚名作《李尔王》关照主人公的命运及其心灵历程 。 扎实而厚重的架构下是巨大的情感张力与叙事空间 。 而在文本行进过程中又始终伴随着“李尔王”对自身命运的哲理性反思 。 这些彼此互文、斑驳并行的叙述将文学永恒的主题纳入到个人的经验之中 , 而作品在关注个体的同时不仅呈现出宏观的社会性视野 , 而且将命运的无可捉摸展现得淋漓尽致 。
六
小说写到这个份上已是出类拔萃 , 而让《“李尔王”与1979》抵达文学大乘境界的除了字里行间流露的“脆弱”或谦卑的气质之外 , 更有最后一节“李尔王”给他的真爱送终的仪式 。 表面上这只是他一个人的仪式 , 实际上却是他以“命运的名义”来完成的仪式 , “是的 , 他要将关于整个夜晚和全部仪式的想象变成生活 , 变成现实 , 变成大地上最深的刻痕 , 变成时间里最长的叹息.”母亲通往天堂的最后一段路程不仅庄严神圣 , 而且诗意盎然 , “父亲全部的身心都充满了暖意和醉意 。 他在这暖意和醉意之中品味着木浆入水的美妙和划水的神奇 , 完全不觉得自己正在用力 , 而觉得自己是在享乐 , 就像《桃花源记》里误入仙境又乐不思归的渔翁 。 划着划着 , 母亲轻柔的唱诵又由远渐近在他的耳边回荡起来 。 父亲羞涩地张望了一下四周 , 接着也情不自禁地随着与自己共同生活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女人一起唱诵起来. 父亲如此陶醉于这你我不分的恩爱、顽皮、细腻和激情 , 竟不知自己是怎样在水库中央停下 , 又怎样将妻子的骨灰一点一点地倒在手上又一把一把地撒向水面 。 ”
回望二人跌宕起伏、历经苦难的一生 , 如此情真意切而又空山灵雨般的画面 , 用雨过天晴式的亮丽 , 或暴风雨之后的彩虹来形容显然分量不够 , 而将之比作贝多芬《田园交响曲》最后一个乐章中向着上苍的感恩旋律也好像欠缺什么 。 就一派超然中所呈现的慈悲和怜悯而言 , 它与贝九的第四乐章更为相似 , 只是后者的《欢乐颂》好像阳光突破浓密的云层洒向大地 , 辉煌而震撼 , 而前者唱诵的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犹如大海上的星光 , 静谧而幽远 。 二者意境迥异 , 但都表达了人类追求自由的意志和获得友爱的希冀 , 也都是超越了各自国族的伟大作品 。 其中的宽容和悲悯与其说是历史批判的深刻 , 不如说是审美观照的天然成果 。
这部犹如“李尔王”命运交响曲的作品以“爱的名义”抵达了生命的高峰或叙事的高潮 , 而“李尔王”在仪式过后的酣畅睡梦中与小外孙的一番对话又似一段余韵悠长的旋律 , 使得《“李尔王”与1979》的叙述呈现出未完成或开放性的局面 。 父亲对想当大作家的小外孙说 , “一个大作家应该知道怎么去写‘不会结束的故事’ 。 ”接着他长叹了一口气 , 说:“可惜等你变成一个大作家的时候 , 我已经不在人世了 。 ”小外孙的脸上也出现了淡淡的伤感 。 “我写的故事会将你重新带回到世界上来 。 ”他说 。 这样的回应恰如文本之外的薛忆沩对外婆的承诺 , 而其兑现的结果就是《“李尔王”与1979》 。
小外孙“想去发现人性的全部奥秘” , 薛忆沩说他想创作一部“人性的百科全书” 。 虚实之间的回环一如埃舍尔绘画在交接点向出发点回归的同时 , 画面从二维过渡到三维 , 又如巴赫的卡农和赋格旋律在结尾的当口平滑地过渡到开头 , 在维度不同的和声中周而复始 , 充满了生生不息的动感和生命力 , 传达着一种无限循环延伸的艺术张力 。 这样的“形式”对应着父亲在结尾处的又一次顿悟:“他突然意识到母亲敲响的钟声其实就是他们回来的意义甚至就是他们生命的意义 , 因为那钟声能够告诉他们列祖列宗无家可归的亡魂他们的家还在繁衍 , 他们的生活还在继续 。 ”
七
薛忆沩之前的五部长篇都关涉家庭 , 但家人带给主人公的不是温馨与慰藉 , 而是隔膜与焦虑 。 两位羁傲不逊的青年最终都无可奈何地“消失” , 两位进退维谷的中年都有过刻骨铭心的幻灭 , 而孤苦伶仃的老人则直抵死亡的结局 。 《遗弃》中的“家”是一个极端压抑的地方 。 隔膜的家庭成员既无法通过血缘彼此牵挂 , 也不能运用理智相互理解 。 图林看到了这一点 , 却不能改变这一点 , 也不愿改变这一点 。 叙事终了时 , 所有的男性人物都“离开”了那个“家” 。 不能和解是《遗弃》的悲剧性特点 。 与此相反的是 , 在《“李尔王”与1979》的开始阶段 , 所有的女性人物(“李尔王”的三个女儿)就一个接一个地“回归”那个大“家” 。 这是这个家庭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团聚(1949年大年三十晚上与家人“划清界限”后的大女儿整整28年没有再踏足过故乡的土地) 。
【李尔王|“李尔王”的命运交响曲】写于1989年的《遗弃》是一个年轻的思想者和写作者对现实、历史以及生命的深层焦虑的宣泄 。 三十年后的《“李尔王”与1979》仍然初衷不改 , 但字里行间透露的不是焦虑 , 而是从容 , 那样的宣泄也已升华为悲悯 , 而这折射出的是文本之外的作者含辛茹苦的文学求索与勇猛精进的个人修为 。 如果说薛忆沩之前的作品是幽咽的泉水 , 是奔腾的河流 , 那么《“李尔王”与1979》就是平静的大海 , 就是浩瀚的湖泊 。 其行文从容裕如 , 架构宏大壮观 , 情感真切饱满 , 细节丰富生动 , 境界开阔深沉 。 这部更上层楼的集大成之作 , 注定会载入汉语文学史 , 而中国文学也终于有可以比肩西方现代派名著的作品了 。
推荐阅读
- 浪胃仙|泡泡龙的离世给所有吃播提了醒,浪胃仙顺势决定“转行”,新职业认真的吗?
- 结核|再见吧,“结核君”
- 感受松软海绵蛋糕“弹弹弹”
- 精河县精深加工,把每颗枸杞都“吃干榨尽”!
- 三星堆遗址|三星堆“迁都”猜想|自然灾害说:洪水、地震等致三星堆古城毁亡
- 农民|春分时节小麦田间管理,做好这些工作,高产又优质
- 猴面包树|这种树“能吃能喝还能住”,养活无数非洲人,引进中国后画风变了
- 早餐的新吃法,“透明饺子”简单好学,孩子看了都超级爱吃!
- 想吃点心不用买,教你在家做“驴打滚”,不用烤箱,软糯香甜!
- 它,有“蔬菜之王”的美称,炒一炒就出锅,清爽可口,好吃不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