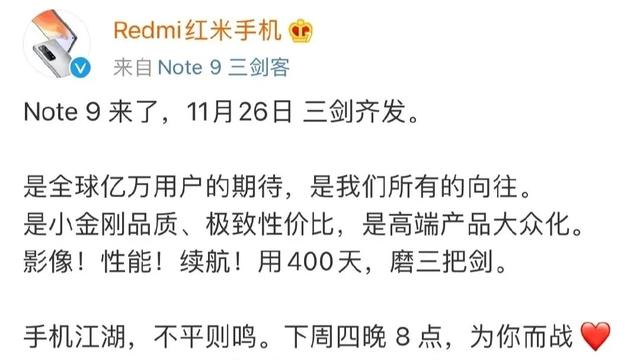“红消香断有谁怜”
“红消香断有谁怜”——回忆殷子突然传来殷子撒手人寰的消息 , 虽然早有预感 , 还是很吃惊!吃惊的是 , 殷子之死不是因为她患有癌症 , 而是死于非命——被人杀害了!殷子 , 不过四十出头的年龄 , 正是女人“三十如狼 , 四十如虎”的好年华 , 却就这样去了 , 悄悄地…… 与她平时大喊大叫 , 爽朗张扬的性格大相庭径 。(一)认识殷子 , 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 。那时 , 我刚刚调到一个单位 , 主管党群工作和第三产业 。 单位里负责人事工作的年轻人童麟 , 在性格 , 爱好 , 为人处事上与我投缘 , 于是便成了好朋友 。 虽然我比他大好多岁 , 论职务 , 还是他顶头上司的上司 。 忘年之交 , 就不顾这些啦!友谊的淳厚 , 是靠时间和真情酿造的 。记得那是一九九三年 , 一次颇具规模的油、地文娱联欢比赛 。 参加的单位不少 , 参赛节目很多 , 评委现场打分 , 评比 , 当场宣布成绩 。我到单位不久 , 眼看比赛日子来临 , 单位还没有节目 。 这时 , 童麟向我毛遂自荐 , 献上节目:诗朗诵“毛主席诗词《沁园春 . 雪》” 。 我一听大喜过望 , 并且决定亲自操琴上台 , 为他现场音乐伴奏 。只有半天时间 , 我俩来不及排练 。 演出之前 , 一起吃晚饭 , 到饭店要了一瓶白酒 , 边喝边约定:“待我音乐前奏结束 , 由你尽情发挥” 。 就这样 , 一句话 , 没有化妆 , 没有演出服 , 我俩便匆匆登上了舞台 。演出效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借着那一点酒性 , 我双手在键盘上挥洒自如 , 行云流水般弹奏出《沁园春 . 雪》的主旋律前奏 。童麟不要手稿 , 不需提示 , 随着我的音乐:“北国风光 , 千里冰封 , 万里雪飘…”冉冉飘进我的耳里 。那铿锵有力的朗诵声 , 时而高亢激昂 , 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瀑布;时而低徊婉转 , 似娟娟沁入心田里的溪流 。 仪态温文尔雅 , 台风庄重大方 , 节奏张弛有度 , 声音充满磁性 。 其把握的分寸 , 节奏 , 和朗诵的感染力 , 不逊专业人士 。 音乐声 , 朗诵声此起彼伏 , 虎啸龙吟 , 相得益彰 , 配合得天衣无缝 , 博得评委和观众阵阵喝彩 。 毋庸置疑 , 除了地方歌舞团几十人的大型歌舞法定特等奖外 , 我们两人的《配乐诗朗诵》 , 实至名归地夺得了第一 。这次演出 , 我们共同经受了考验 , 恰如风雨同舟 , 多了一份默契 , 多了一种磨合 , 友谊更深了 。也就在这个时期 , 我认识了童麟的朋友殷子 。(二)殷子大概二十岁左右 , 是工作在梨城库尔勒市的一个南疆姑娘 。那时 , 虽然塔里木石油会战比较紧张 , 但我们都是不带家的单身汉 , 工作以外 , 业余时间较多 。 于是 , 我们经常一起去聚餐 , 唱歌 , 跳舞 , 看电影 , 外出郊游 。 忙 , 且快乐着 。殷子是童麟的粉丝 , 敬佩童麟的才华和为人 , 总喜欢跟着他 , 参加大家的活动 。这个女孩子 , 虽然算不上漂亮 , 但是修长挺拔的身材 , 活泼大方的性格 , 对人礼貌得体 , 说话掌握分寸 , 唱歌跳舞都不错 , 喝起酒来也豪爽干脆 , 什么场合都能应付 , 大家都很喜欢 。光阴荏苒 , 岁月沧桑 。 随着塔里木油田会战的深入 , 管理从粗放型发展到集约型 , 指挥部从郊外“大二线”搬往库尔勒城市中心 , 机构重组改制 , 人事变动调整 , 我们都经历了几次大变动 。我和童麟 , 到了不同的单位 , 也有了自己温馨的家庭 。 而殷子 , 在我的视线中渐渐淡去 。(三)如果不是一个电话 , 就没有了这篇文章的下文 。大概是十年前 , 我从北疆挂职回南疆不久 。手机响了 , 一个陌生的号码 , 却是熟悉的声音:“老哥吗?我是殷子 , 听说你去当大官了!”说话还是那样大大咧咧 , 声音却有一些嘶哑 , 显得有气无力 。电话中 , 知道她因喝酒 , 摔了一跤 , 伤筋断骨住进医院 。 寂寞住院 , 无人照顾 , 连吃饭都成问题 。我当时刚回库尔勒不久 , 正在接手清理全油田公司第三产业的工作 , 很忙 。 除了一些安慰 , 给她打去一千元聊以慰藉 。殷子的生命力很顽强 , 没有几天 , 她居然出院了 。一出院 , 她就接连来电话 , 一定要请我吃饭 。记得那次印象深刻的“二人宴” 。 在一个小饭馆里 , 多少年没有见面 , 第一眼见她 , 我不禁悲从心来:头上缠着一圈圈纱布 , 腰上裹着厚厚的绷带 , 菜黄色的脸上 , 横着几块没有痊愈的疤痕 , 眼睛被浮肿的脸挤成一条缝 , 我怀疑她不是出院了 , 而是没有钱住院了 。殷子一边大口喝着酒 , 一边断断续续诉说着自己的遭遇:当年 , 她告别了我们这些朋友 , 独自在社会闯荡 。做过生意 , 开过公司 , 当过老板;替人打工 , 也做过包工头 。后来 , 结婚了 , 嫁人了 , 生孩子了 。 再后来 , 丈夫因车祸死了 , 孩子由南方的姐姐抚养 , 殷子又成了孤家寡人 。这一晃就是十多年啊!就这样 , 她一边毫无节制地一杯杯往嘴里倒着酒 , 一边骂骂咧咧地叙述着多灾多难的往事 。我没有说话 , 只是静静地听她倾诉 , 她蜡黄的脸因为酒精的作用和情绪的激动 , 开始有了一丝血色 , 但是 , 话语已经越来越不清楚 。 我强行夺过酒瓶 , 把她送回住所 。这是库尔勒市最整齐 , 最漂亮的“石化大道” 。 我没有想到 , 她给我指认的“家” , 却在这条宽阔双向八道马路旁的 , 一条窄小的巷道里 。 路面坑坑洼洼 , 曲曲弯弯 , 巷里又脏又暗 , 到处垃圾臭水 , 两边紧挤着破旧低矮的老屋 , 殷子就住在这样的环境 。房里的情况还寒碜:一架摇晃的木床 , 一把破旧的椅子 , 一个冰冷的铁炉 , 一床散乱的被子 , 这就是全部家当 。看到这里 , 我心里一阵酸楚 。 这就是当年意气风发 , 阳光灿烂的那个小姑娘么?十几年的苍桑岁月 , 怎么可能把一个才三十出头的女子 , 折腾到如若“乞丐”的地步?(四)从此以后 , 殷子与我的联系渐渐多了 。有时为了停机的话费 , 有时为了与朋友相聚 , 有时她就直接告诉我 , 心情不好 , 想喝酒了…大概是因为刚刚挂职扶贫回来的原故吧 , 我心想 , 能够一心一意去帮助素昧平生的 , 有牛有羊有家的农牧民扶贫 , 那么 , 为这个身无长物 , 没有自己的家 , 没有正当职业 , 穷困潦倒到如此地步的朋友 , 去力所能及地帮助一点什么 , 不是更应该么?一个天大的机会 , 似乎终于来了!二零一四年夏天 , 殷子兴冲冲找到我 , 说在紧挨若羌县的青海海西州 , 一个特大露天煤矿要剥离土石层 , 殷子已经托熟人联系到承包公司的老板 。 据称 , 只要有280万风险抵押金 , 能够组织各种设备车辆 , 就可以签订合同 , 年收入千万以上 。机会当然不能错过!我的职务限制了我 , 不能够直接参与地方经营活动 , 却没有限制我帮助别人脱贫致富 。 如果这个工程能够落实 , 将“一劳永逸”地解决殷子的困难 。为此 , 我特地与承包公司老板谈判 , 老板见我亲自出面 , 很干脆地把抵押金降了三分之一 。 我又委托我的小兄弟 , 与殷子专程到青海海西现场认真勘查 。 接着 , 亲自与克拉玛依的朋友联系 , 让他带上280万元巨款赶到库尔勒 。 紧接着 , 我一方面动员各种关系 , 召集几个有能力 , 可信任的朋友一起 , 商量筹备有殷子参与的公司 。 并且积极组织调配各种设备 , 车辆 , 做好前期的后勤生活保障工作 。 同时 , 挑选精明的小兄弟 , 与殷子一道 , 乘飞机前往乌鲁木齐与老板接洽 , 准备签订合同 。临行前 , 我多了一个心眼 , 嘱咐小兄弟到了乌鲁木齐后 , 必须先看有关文件和资料 , 随时与我联系 , 千万不能擅自行动 。当天晚上 , 聪明的小兄弟 , 悄悄把老板引以为豪的“红头文件” , 及时传送给了我 。 文件确实是海西州政府下发的 , 但是 , 凭我在特大型央企从事管理工作的多年经验 , 以及对能源开发政策的理解 , 要开发一个超大型能源基地 , 起码要经省一级考察论证 , 再申报国家 , 还需中央有关部门复核 , 审批 , 中央再下文 。 海西地区政府关于尽快开发能源基地的文件 , 只是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美好愿望 , 不具备开发的权威和操作的合法性 , 缺乏法律效力 。 当然 , 一个政府的“红头文件” , 往往很有诱惑力 , 也容易被人利用 。为了保险起见 , 我连夜咨询了在省区一级工作的同事和专家的意见 , 证实了我的论断 。我让小兄弟试探着向老板讨价还价 , 把风险抵押金再降八十万 , 当初气势汹汹的老板 , 居然一口答应 。 更增加了我的怀疑 。各种迹象表明 , 这里面藏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当晚 , 我立即召唤他们赶快回来 。 而殷子呢?还在为降低八十万抵押金沾沾自喜 , 喋喋不休地要求我同意签订合同 。回到库尔勒 , 我告诉了他们不能够签订合同的原因 。 殷子仍然心有不甘 , 甚至准备再去海西找熟人 , 搞一份有更大权威的文件呢!一直到现在 , 这个所谓土方工程与“藏水入疆”工程一样 , 如空中楼阁 , 只是一场骗人的把戏 。朋友的280万保住了 , 我却实实在在地惊出了一身冷汗 。(五)在我们庆幸没有受骗上当的时候 , 殷子却陷入了深深的失落中 。一段时间 , 她东跑西跑不知在忙些什么 , 生活很没有规律 , 无人约束喝酒无度 。 有时候 , 喝酒不尽兴 , 就跌跌怆怆跑到童麟家要酒喝 , 多亏童麟妻子贤惠豁达 , 以礼相待 。我就此劝戒她:“你这样做 , 女人的自尊心到哪里去了?”她悲切地说:“老哥 , 你看我还像一个有女人味的女人吗?其实 , 殷子是一个有很多优点的女孩子 。 她有能力 , 能吃苦 , 肯努力 , 善交际 , 具备这些条件 , 本应该事业有成 , 家庭幸福 。 可是 , 她性格直爽 , 好讲义气 , 三教九流 , 结交随意 , 动辄哥们兄弟推杯换盏 , 试图在酒桌上办成大事 。 恰恰是这个虚幻的“义” , 和那个实实在在的“酒” , 毁了她一生 。她事业无成 , 居无定所 , 中年丧夫 , 无力养儿 , 坠入社会最底层 , 与当年心高气傲的殷子反差实在太大 。这是她心里的一个痛 , 也是朋友们的一个痛 。殷子也努力过 , 挣扎过 , 有过重建家园 , 重新生活的期盼 。记得有一年 , 她兴冲冲找到我 , 请我代表娘家 , 去参加她的一个“订婚礼” 。 我心里十分高兴:名花有主 , 殷子终于有一个安乐窝了!男方是铁路上的机车工 , 四十左右 , 人很老实 。 宴席整整一大桌人 , 都是铁路员工 , 唯一的我 , 代表娘家临时发表了“祝贺辞” 。 为了替殷子撑面子 , 过了几天 , 我特意邀请男方与殷子两人吃饭 , 叮嘱他们要相亲相爱 , 白头偕老 。 酒桌上 , 殷子又多喝了几杯 , 开始口无遮拦骂骂咧咧 , 无端训斥小伙子 。 我暗暗嘀咕:这可不是好兆头呀!果不然 , 没有多久 , 二人就“孔雀东南飞”了!殷子长期学习 , 生活 , 工作在库尔勒 , 也有很多发小 , 朋友 。 他们经常关注着她 , 也给予她力所能及的帮助 。 可是 , 这些生活中的“拾遗补缺” , 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 替她摆脱不了风雨飘摇的生活 。殷子最后一次跟我联系 , 是二零一七年五月 。 她与我加了微信朋友 , 然后告诉我 , 在乌鲁木齐医院检查出了癌症 。 她语气很平静 , 没有一点惊恐与慌张 , 然后轻描淡写一句话:“没事 , 生死由命富贵在天” 。 我心里漂浮不祥的感觉 , 安慰她说:“我过段时间回库尔勒 , 到时候邀几个朋友聚一聚 。 ”她给我最后的讯息 , 是一个带勾的“OK” 。没隔多久 , 死讯传来 。 不过 , 她不是死于可怕的癌症 , 而是倒在与“哥们兄弟”换盏推杯的酒桌下 。一个并非仇人的凶手 , 一把并非凶器的小刀 , 鬼使神差般要了她的命 。 那个虚虚假假的“义” , 这杯实实在在的“酒” , 与她那曾经漂亮的身材和高傲的灵魂一起 , 烟消云散……“红消香断有谁怜”?殷子 , 你的音容笑貌和以死换来的警示 , 永远纠结在我们心中!201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