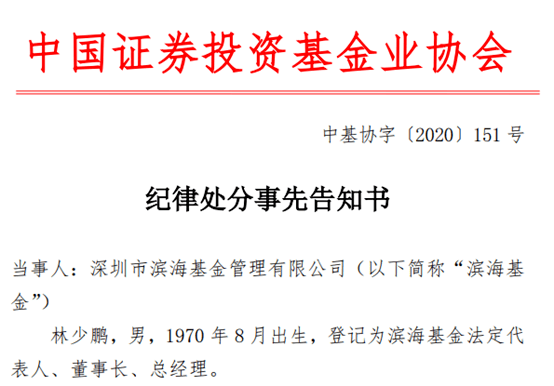物理学家都是唯物主义吗( 二 )
打印 纠错 分享 推荐
1919年,党的八大通过《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纲》,规定在人民教育中,不仅要将1917年十月革命所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而且要对其“展开最广泛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工作”(17)。1924年,党的十三大决议再次强调,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把对俄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提到应有的高度,其目的仍是立足于总结历史和宣传联共(布)经验。决议强调,党中央委员会应该采取一系列措施,把俄国共产党历史的适当教科书的出版提到应有的高度,并且使党史成为一切党校、一切高等学校、一切小组等的必修课。因此,要充分认识“目前对党史、十月革命史研究工作的广大需要和这项工作的莫大教育意义”,必须加强党史研究室的工作,“应特别注意采取一切措施来”保证这项工作的成功(18)。
从1931年到1937年,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其他领导人还多次指出,“要把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问题提到应有的高度,把我党历史研究工作放在科学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轨道上,叫大家集中注意力去反对那些托洛茨基主义的和其他一切伪造我党历史的人,有系统地揭破他们的假面具”(19)。在批判《世界历史》教科书纲要存在的问题时,斯大林等指出了“纲要”未曾反映而理应反映的历史问题。比如要区分俄罗斯的历史与苏联的历史,要区分反动和反革命、“一般的”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区分资产阶级陈腐的、完全非科学根据的定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有科学根据的定义,要区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和十月革命意义等一系列问题(20)。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论述联共(布)党史时,要给予诸如“在苏联党内以及在资本主义时期的工人阶级中有极多的派别和小组织”及其“残酷斗争的事实”等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使其“存在”不仅成为可以“理解的”,而且认识到它是“保卫列宁主义的原则性的斗争”(21)。
苏共倡导历史教育,一方面,是用“统一的”历史来推广普及历史经验,统一思想认识;再一方面,是用经过“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历史,实现联共(布)历史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用斯大林的话说,我们需要的不是各地革命运动概况的汇编,而是需要总结党在发展过程中各重大关键问题的经验的历史(22)。
因此,重新编撰联共(布)党史,可以使所有人认识和把握四个问题:1.联共(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2.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党的正确指南;3.为什么我们国家是列宁主义故乡?4.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规律。所以,编著一本经苏共中央审定的、统一的党史教材,不仅成为推广十月革命历史经验的重要文本依据,还“给党的积极分子对联共(布)党史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教会他们“应该怎样表达思想、说明观点、阐述党的方针”(23)。
四、理论诉求:规范党对“列宁主义”的统一解释
列宁逝世以后,苏联党内和理论界出现了暂时的领袖缺位现象。而行进中的新经济政策和国内外严峻形势,给苏共提出许多复杂的问题,核心问题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争论,该问题若不从理论上加以澄清,则必将带来实践上的“思维混乱”。
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始于对“列宁主义”的不同阐释。争论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由谁来阐释列宁的学说,二是怎样阐释列宁的学说。从1923年开始,托洛茨基首先以《新方针》总标题的文章和《十月的教训》、《论列宁》等文章,提出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进行历史分析和确定方向的方法”,“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应用”(24),是这种历史特点和历史方法的结合。1924年4月,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将列宁主义界定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25)。季诺维也夫认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26)布哈林虽然没有正面介入这场争论,但他认为“革命破坏和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综合,这就是列宁主义”(27)。苏联理论家和政治精英们争先恐后评议列宁主义的内涵,暂且不去分辨哪种界定更为周详和科学,透过争论事件本身不难发现,争论之中隐含着另一个更为深刻的理论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也是在列宁逝世之后苏共必须回答的理论难题。
1925年,苏联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作为当时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开始将视线从国外转向国内,从巩固革命转到发展经济生产,于是一个国家单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被提出来。十月革命之后,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而无法在一国内“建成”,尤其是在像俄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成似乎正在成为一种共识。为批判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斯大林首先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托洛茨基从“不断革命论”出发,衍生出了“世界分工”论,认为世界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是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我们虽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保持为一个国家,但是我们并没有达到甚至还没有走进建立社会主义的阶段”(28)。但斯大林却认为,在其他国家于相当长的时期内保存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在我们这个技术上和经济上落后的国家里,在资本主义包围而且是目前还稳定的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不仅可以用自身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而且可以保证免除武装干涉的危险和旧制度复辟的危险(29)。季诺维也夫认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国际援助条件和国内与农民达成妥协等条件的缺失,使得“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最终取得胜利,列宁一分钟都没有忘记”(30)。1926年,斯大林又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对此问题作了系统论述,分别对“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能否在一个国家里获得最终胜利”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认为前一个问题的解决需要用国家内部力量解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并获得其他国家无产者的同情和支持,而后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至少几个国家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保证武装干涉和旧制度复辟的免除,也就无所谓社会主义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完全的最终胜利问题(31)。布哈林分析“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视角比较独特,他强调“一国”是指“我国”,即苏联,而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所以,“如果我们从我国内部的各种力量的配合出发,那么,尽管我国落后,尽管存在由这种落后所决定的巨大困难,我们有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而且是足够的一切,我们能够建设而且能够建成社会主义”(32)。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存在较大的分歧,究其缘由,还是在于对社会主义含义的不同理解。
历史与冲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编著缘起探析2016年09月26日 19:22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作者:许冲 孟令蓉字号
打印 纠错 分享 推荐
如果说诠释“列宁主义”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那么还有一个更为现实和紧迫的问题,即在苏联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依靠自身的力量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就是根据什么样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仍等待着苏共领导人和理论家们回答。对于这个问题,从整体思路看,托洛茨基的回答比较直白——“等待”世界革命,促成世界革命。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也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托洛茨基派的观点。布哈林以其“落后型社会主义理论”批判了托洛茨基的观点,企图通过“乌龟速度”和一个长时期的有机的过程,“真正长入社会主义”。斯大林沿着“落后就要挨打”的思维强调,要么灭亡要么改变新经济政策的思路,加速工业化发展,所以“直接进攻”和“短促突击”就成为斯大林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方法。从具体策略上看,托洛茨基、布哈林、斯大林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农业与农民、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农业集体化与高速工业化等理论和现实问题都存有较大分歧。
苏共党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既是现实的,也是理论的。争论无法达成理论的澄清和统一时,一种经过官方审定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党史教程,就成为一种迫切的要求。重新编写联共(布)党的历史教程就成为一种现实之选。
五、实践期待:对社会主义矛盾冲突的澄清与消弭
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相比理论上的争论不休,如何应对日益紧张的国内局势,对实践中的冲突乃至错误进行解释,并从理论上赋予实践以合法性,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因为现实中的混乱比理论上的迷惑所带来的影响更加直观和深刻。
20年代后期,斯大林与布哈林对于工业化问题、农业集体化问题、粮食收购危机问题和如何对待富农问题一直争论不休。1927年至1928年初,粮食收购危机和“沙赫特事件”分别在农村和城市中被揭露出来。在清除“布哈林右倾投降主义集团”的同时,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暴力”消灭,农业全盘集体化的飓风也以革命运动的方式席卷了整个苏联。同时,新时期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国民经济所引起的新的“阶级变动”,在有些领导人看来必然会引起“垂死阶级对苏维埃政权的政策的反抗”(33)。所以,面对“阶级敌人破坏”,抑或“有组织的反革命破坏”,只有“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展开阶级斗争、消灭阶级、消灭资本主义阶级残余的手段”才能解决(34)。而由“基洛夫被害案”所直接点燃的“大清洗”导火索,更成为30年代苏联国内波及党政军群各领域的一次重大社会运动。此次运动,可以追溯到斯大林在推进超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的“大转折”胜利之后,面对苏联国内各界的紧张和不满,领导人习惯性地从政治上去追究“破坏者”和“人民的敌人”的责任。在此之前,苏联国内关于“拯救乌克兰联盟”案、“乌克兰青年联合会”案、“劳动农民党”案、“孟什维克中央联盟局”案、瑟尔佐夫—洛米纳泽“反党集团”案、“马克思主义联盟”案等案件层出不穷。1934年12月,“基洛夫被害案”很快就被纳入指控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行动中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逮捕。接着各种各样的审判接连不断,1935年5月,在斯大林倡议下,全党开始了为期大半年的检查党证运动,被开除党籍并被逮捕的有15218人,揭发了上百个“敌对组织和集团”,没收党证25万张(35)。1936年7月29日,随着《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恐怖活动》密信的下达,“大清洗”运动大幕拉开,并一直延续到1938年。在此期间,受到牵连的人有500多万,仅1937年和1938年两年间就有150万人遭到逮捕,681692人被判刑。1934年12月至1938年12月,估计有140多万人被处决(36)。
何以在苏联和平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甚至在苏共党内,会出现涉及范围如此之广、牵涉人数如此之众的“特务”、“暗害分子”、“间谍”等“人民的敌人”,而且需要通过逮捕、判刑、监禁、处决的极端方式加以处理,广大苏联人民群众无法理解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实践和现实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斯大林和苏共必须从理论上对此作出“合理”解释,因为这场运动已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大批干部被牵连并受到迫害,影响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干部群众的建设积极性和创造性,甚至在共产国际内部也产生了不信任。重新编写联共(布)党史,对实践进行重新解释也是另一种现实的需要。
六、主体需要:民族心理与斯大林领袖权威的树立
历史学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改写或重写历史对于政党、政权、政治人物巩固自身、树立权威意义重大。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崇尚权威的民族,因而重写联共(布)党史,对于斯大林领导下的联共(布)党具有更为直接的意义。
历史与冲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编著缘起探析2016年09月26日 19:22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作者:许冲 孟令蓉字号
打印 纠错 分享 推荐
从历史上看,俄国是一个具有东方专制主义传统的大国,没有经历欧洲文艺复兴,民族文化特性中“缺少理性精神,注重情感,驯服于权威,缺少自主性”(37)。究其缘由,一方面,俄罗斯拥有浓厚的东正教传统,教权与皇权联盟,前者帮助统治者麻痹人民,后者帮助前者维护宗教正统地位。东正教严格的宗教教条,“在教育水平极低的条件下,导致人们对历史上相对的和暂时的礼仪形式奉若神明”(38),产生教条主义。另一方面,对俄国沙皇的崇拜和神化,使其权威充满神性,个人则被奉为神明,一切人都希望得到被上帝派往人间的“好皇帝”和“父亲”的帮助。再一方面,俄国国内80%的居民是农民,文化素质普遍较低,1920年俄国文盲率为68.1%,1923年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受过中等教育的只占6.3%,受过高等教育的只占0.6%,文化的落后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民主体意识的淡漠,权威崇拜心理严重(39)。悠久的封建历史和民族传统,使得俄罗斯人民文化心理上有一种对权威的神圣期待。此外,俄罗斯历史传统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崇尚暴力和集权。从16世纪作为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崛起,俄罗斯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经过300年的扩张,掠夺了174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暴力和集权,或者说用暴力铲除一切反对派、用高压野蛮手段反对“野蛮势力”,就成为维系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传统,也构成了俄罗斯政治传统和领导体制的重要内容。
推荐阅读
- 仗着自己有病把自己爱的东西抢走的人是啥心理
- 你后悔过成现在的样子嘛
- 在北京,你们日常都是咋买水果的呢
- 5g先普及全国还是垃圾分类先普及全国
- 老北京人真的都是有钱人吗
- 不想在家啃老,想当代驾,前辈们有啥建议吗
- 受邀参加国宴的都是些啥人
- 所有人上班都是苦逼压抑的吗
- 家用空调,怎样选购相关的参数都是啥意思
- 北京哪还有露天大排档?










![人民网|[网连中国]乡音唱新风、定约除陋习,文明实践最后"一公里"通了](https://mz.eastday.com/1840376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