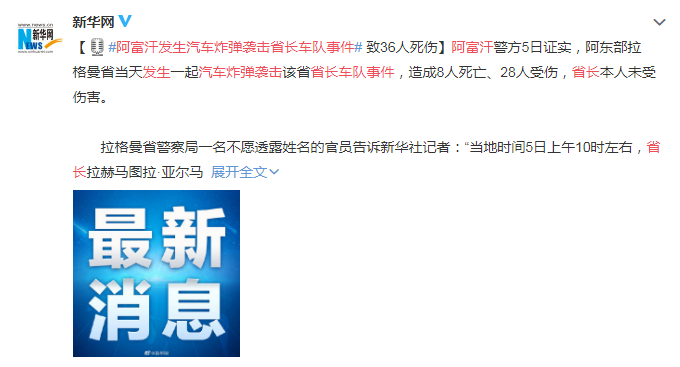еҢ—й”Јйј“е··в– гҖҠиғЎеҗҢйҮҢзҡ„жұҹж№–гҖӢпјҡеҢ—й”Јйј“е··йҮҢзҡ„д»Үе…Ҳз”ҹпјҢйЈҺе§ҝеҖңеӮҘпјҒ
еңЁйј“жҘјдёңзҡ„дәӨйҒ“еҸЈеӨ§иЎ—дёҠ пјҢ еҢ—жңүеҢ—й”Јйј“е·· пјҢ еҚ—жңүеҚ—й”Јйј“е·· гҖӮ
вҖңжң¬еёӮдәӨйҒ“еҸЈеҢ—й”Јйј“е··е…ӯеҚҒдёүеҸ·д»Үз„•йҰҷе…Ҳз”ҹеҗҜвҖқ пјҢ еӣ дёәеҶҷдҝЎ пјҢ иҝҷең°еқҖи®°еҫ—еҫҲжё… гҖӮ жҲ‘д№ҹзҷ»иҝҮй—Ё пјҢ иҝӣй”Јйј“е··еҚ—еҸЈдёҚиҝң пјҢ и·ҜдёңдёҖе°Ҹй—Ё пјҢ й—ЁеүҚжңүеҮ зә§еҸ°йҳ¶ гҖӮ иҝӣй—ЁжҳҜдёҖзӢӯй•ҝе°Ҹйҷў пјҢ д»Үе…Ҳз”ҹе°ұеңЁдёҖжҺ’еҢ—жҲҝйҮҢи§ҒжҲ‘ пјҢ жҳҜдёҚжҳҜиҝҳжңүеҗҺйҷўжҲ‘жІЎжіЁж„Ҹ гҖӮ 
ж–Үз« еӣҫзүҮ
зңӢй—ЁзүҢе·ІдёҚжҳҜвҖңеҢ—й”Јйј“е··е…ӯеҚҒдёүеҸ·вҖқ пјҢ иҖҢжҳҜдёғеҚҒдәҢеҸ·пјӣзңӢеҸ°йҳ¶жҲ‘и®ӨеҮәиҝҷжҳҜд»Үе…Ҳз”ҹ家зҡ„ж—§ж—¶й—Ёеўҷ гҖӮ д»Үе…Ҳз”ҹ家еңЁйЎәд№ү пјҢ жңүжҲҝеӯҗжңүең° гҖӮ жүҖд»Ҙд»–иғҪдёҠеҢ—дә¬еӨ§еӯҰ пјҢ зӣҙеҲ°жҜ•дёҡ пјҢ еҲ°жұҮж–ҮдёӯеӯҰж•ҷд№Ұ гҖӮ дёҖд№қеӣӣдә”е№ҙз§ӢжҲ‘иҝӣжұҮж–ҮеҝөеҲқдёҖ пјҢ ж•ҷе®ӨеңЁиҘҝжҘјеҢ—еӨҙзҡ„еҚҠең°дёӢе®ӨйҮҢ пјҢ еҗ¬д»–жҢҘжҙ’иҮӘеҰӮең°и®ІеӣҪж–ҮиҜҫ гҖӮ д»–дёҚжҳҜз…§жң¬е®Јз§‘дёҖжқҝдёҖзңјең°и®Ід»Җд№ҲвҖңж®өиҗҪеӨ§ж„ҸвҖқ пјҢ иҖҢжҳҜд»ҺиҜҫж–Үж”ҫе°„ејҖеҺ» пјҢ и®ІзӨҫдјҡ пјҢ и®ІеҺҶеҸІ пјҢ и®ІдҪңиҖ… пјҢ дҪҝжҲ‘们иұҒ然ејҖжң— пјҢ еӨ§ејҖзңјз•Ң пјҢ д№ҹжҮӮеҫ—дәҶйўҶз•Ҙж–ҮеӯҰжҸҸеҶҷзҡ„з»Ҷеҫ®еҰҷеӨ„ гҖӮ иҮӘ然жңүдёҚе°‘еңЁеҪ“ж—¶жҲ–д»ҠеӨ©ж•ҷеӯҰдёӯйғҪдјҡи®ӨдёәеҮәж јд№ӢеӨ„ пјҢ жҜ”ж–№и®ІйІҒиҝ…зҡ„гҖҠйӣӘгҖӢдёӯиҜҙеҚ—ж–№зҡ„йӣӘвҖңеҰӮеӨ„еӯҗзҡ„зҡ®иӮӨвҖқ пјҢ д»–е°ұд»ҘвҖңиұҶи…җи„‘вҖқе’ҢвҖңиҖҒиұҶи…җвҖқеҲҶеҲ«жҜ”жӢҹеҚ—ж–№е’ҢеҢ—ж–№зҡ„еҘіжҖ§пјӣеҸҲд»ҺдёӯеӣҪеҸӨе…ёе®ЎзҫҺжҺЁеҙҮвҖңжЁұжЎғе°ҸеҸЈвҖқиҜҙеҲ°еҘҪиҺұеқһж¬ЈиөҸеӨ§еҳҙзҡ„еҘіжҳҺжҳҹвҖҰвҖҰд»Үе…Ҳз”ҹжҠҠжҲ‘们еҪ“дҪңд»–зҡ„еҗҢиҫҲдјјзҡ„ гҖӮ жңүж—¶иҝҳиҜҙиө·дёҖдәӣи·ҹиҜҫж–Үж— е…ізҡ„иҜқйўҳ пјҢ ж— и®әе…ідәҺж—¶дәӢ пјҢ е…ідәҺдёӘдәә пјҢ йғҪи®©жҲ‘д»¬ж јеӨ–ж„ҹеҲ°д»–еҜ№еӯҰз”ҹе№ізӯүзӣёеҫ… пјҢ дёҚж‘ҶеҮәдёҖжң¬жӯЈз»Ҹзҡ„жһ¶еӯҗ гҖӮ еҫӘ规и№Ҳзҹ©зҡ„иҜҫе Ӯ秩еәҸдёӯжқҘзҡ„еӯ©еӯҗ пјҢ ж¬Је–ңдәҺд»–зҡ„дәІеҲҮ пјҢ еҸҜд»ҘдәІиҝ‘ пјҢ дёҚеғҸдёҖејҖе§Ӣи§Ғд»–жҲҙзқҖеўЁй•ң пјҢ зңӢдёҚеҲ°зңјзҘһ пјҢ зҘһз§ҳиҺ«жөӢ пјҢ еҝғеӯҳеҮ еҲҶз•Ҹжғ§пјӣд»–зңӢеҮәеӨ§е®¶зҡ„з–‘иҷ‘ пјҢ дё»еҠЁиҜҙжҳҺжңүеҸӘзңјзқӣжҖ•е…ү пјҢ жүҖд»ҘжҲҙзңјй•ң пјҢ е°ұдҪҝеҫ—еёҲз”ҹи·қзҰ»жӢүиҝ‘дәҶ гҖӮ
дҪҶ第дёҖж¬ЎдҪңж–ҮеҚ·еӯҗеҸ‘дёӢжқҘ пјҢ еҚҙз»ҷжҲ‘дёҖдёӘдёӢ马еЁҒ гҖӮ д»Үе…Ҳз”ҹеңЁеҗҺйқўд»ҘжһҒдҝҠйҖёзҡ„д№Ұжі•жү№йҒ“пјҡвҖңвҖҰвҖҰйқһзҺҮе°”ж“Қи§ҡиҖ…еҸҜжҜ” пјҢ жҳҜд»ҺдҪ•еӨ„жҠ„жқҘпјҹвҖқ
дёӢиҜҫж—¶жҲ‘иө°дёҠи®ІеҸ° пјҢ еҜ№д»–и§ЈйҮҠ пјҢ жҲ‘е°ұжҳҜиҮӘе·ұеҶҷзҡ„ пјҢ жІЎжңүжҠ„иўӯ гҖӮ д»–жІЎиҜҙд»Җд№Ҳ пјҢ еҝғйҮҢжҖ»жҳҜдёҚдҝЎеҗ§ гҖӮ 第дәҢж¬ЎдҪңж–Ү пјҢ д»–еӨ§жҰӮз•ҷж„ҸжҲ‘еҪ“е ӮдҪңдёҡ пјҢ зӣёдҝЎжҲ‘иҮӘеҮәжңәжқј гҖӮ з”ұжӯӨжҲ‘们жҲҗдәҶеҝҳе№ҙд№ӢдәӨ гҖӮ
дёҖд№қеӣӣдә”е№ҙ пјҢ жҲ‘еҚҒдәҢдёүеІҒ пјҢ д»–дәҢеҚҒдёғе…«еІҒ пјҢ еҠ иө·жқҘдёҖе…ұеӣӣеҚҒеІҒ пјҢ д№қеҚҒе№ҙд»ЈжҲ‘еҲ°иҘҝйғҠеҸҢжҰҶж ‘еҚ—йҮҢи®ҝд»– пјҢ жҲ‘们дёӨдәәзҡ„е№ҙйҫ„зӣёеҠ е°ұжҳҜдёҖзҷҫеӣӣеҚҒеІҒдәҶ гҖӮ
дёҖд№қеӣӣе…ӯе№ҙеҲқеҜ’еҒҮеүҚ пјҢ д»Үе…Ҳз”ҹжӢҝз»ҷжҲ‘дёҖжң¬жІ№еҚ°зҡ„жҜӣжіҪдёңгҖҠи®әиҒ”еҗҲж”ҝеәңгҖӢ гҖӮ иҖҢеҜ’еҒҮеҗҺд»–зҰ»ејҖдәҶжұҮж–ҮдёӯеӯҰ гҖӮ иҝҷж · пјҢ дёәдәҶиҝҳд№Ұ пјҢ жҲ‘еҲ°д»–家еҺ» пјҢ еёҲжҜҚзҺӢд№ҰзҸҚеңЁеёӮз«ӢдәҢдёӯж•ҷеӣҪж–Ү пјҢ д№ҹжҳҜд»Үе…Ҳз”ҹзҡ„еҢ—еӨ§еҗҢеӯҰ гҖӮ жҲ‘дҪҸдёңеҚ—еҹҺ пјҢ д»–дҪҸеҢ—еҹҺ пјҢ зӣёи·қиҫғиҝң пјҢ дёҖдёӨе№ҙй—ҙд№ҹеёёеҶҷдҝЎз»ҷд»– пјҢ д»–и§ҒдҝЎеҝ…еӨҚ гҖӮ жҲ‘дёҖеәҰеӯҰд»–зҡ„еӯ—дҪ“ пјҢ дҪҶжҖ»д№ҹеӯҰдёҚеғҸ гҖӮ
дёҖд№қеӣӣд№қе№ҙеҲқ пјҢ еҢ—е№іе®ҲеҶӣеӮ…дҪңд№үйғЁжҺҘеҸ—е’Ңе№іж”№зј– пјҢ еҹҺеӨҙжҳ“еёң гҖӮ жңүдёҖеӨ©д»Үе…Ҳз”ҹеҝҪ然иҝңи·ҜиҝўиҝўйӘ‘иҪҰеҲ°жҲ‘家 пјҢ д»–иҜҙзҢңжҲ‘еҮҶеӨҮвҖңеҸӮеҠ йқ©е‘ҪвҖқдәҶ пјҢ жҲ‘иҜҙжӯЈжҳҜ пјҢ ж—©е°ұдёҚжғіеҶҚз•ҷеңЁеӯҰж ЎиҜ»д№Ұ пјҢ жңүдәӣеҗҢеӯҰе·Із»ҸеҲ°еҹәеұӮе·ҘдҪң пјҢ еҲҶеҲ°еҢә委е’ҢжҙҫеҮәжүҖпјӣз»„з»ҮдёҠеҸ·еҸ¬жҲ‘们жҠ•иҖғеҚҺеӨ§гҖҒйқ©еӨ§ пјҢ еҮҶеӨҮйҡҸеҶӣеҚ—дёӢи§Јж”ҫе…ЁдёӯеӣҪ гҖӮ д»Үе…Ҳз”ҹдёҖеҸҚе№іж—¶еҜ№жҲ‘йғҪжҳҜйј“еҠұзҡ„еҸЈж°” пјҢ иҜҙ пјҢ жҲ‘зңӢдҪ иҝҳжҳҜ继з»ӯдёҠеӯҰзҡ„еҘҪ гҖӮ дҪ дёҚжҳҜз«Ӣеҝ—еӯҰж–ҮеӯҰеҗ— пјҢ йӮЈиҝҳжҳҜиҰҒеӨҡиҜ»д№Ұ пјҢ жү“еҘҪеҹәзЎҖ гҖӮ еҸҲиҜҙ пјҢ йҷӨдәҶжҜӣжіҪдёңгҖҒе‘ЁжҒ©жқҘ пјҢ е…ҡеҶ…иҝҳжңүдёҖдёӘзҗҶи®ә家еҲҳе°‘еҘҮ пјҢ жңҖиҝ‘еҶҷдәҶгҖҠеӣҪйҷ…дё»д№үдёҺж°‘ж—Ҹдё»д№үгҖӢжү№еҲӨй“Ғжүҳ гҖӮ еҸӮеҠ еҲ°йҮҢйқўеҺ» пјҢ ж–ҮеӯҰзҡ„дәӢдёҡе°ұеҒҡдёҚжҲҗдәҶ гҖӮ жҲ‘зӯ”еә”еҶҚжғідёҖжғі пјҢ д»–еӨ§жҰӮзңӢеҮәд»–зҡ„ж„Ҹи§ҒжҲ‘жІЎеҗ¬иҝӣеҺ» пјҢ еҸҲеҢҶеҢҶйӘ‘иҪҰиө°дәҶ гҖӮ
жҲ‘еңЁе…ій”®ж—¶еҲ» пјҢ дәәз”ҹзҡ„дёҖдёӘиҪ¬жҠҳзӮ№дёҠ пјҢ жІЎжңүеҗ¬д»–зҡ„иҜқ гҖӮ дҪҶи®ёеӨҡе№ҙеҗҺеӣһйЎҫ пјҢ еҚідҪҝдёҖж—¶еҗ¬дәҶд»–зҡ„иҜқ пјҢ жҲ‘д№ҹдёҚеӨ§еҸҜиғҪеғҸд»–и®ҫжғізҡ„йӮЈж ·иёҸе®һиҜ»д№Ұ пјҢ еҒҡжҲҗвҖңж–ҮеӯҰзҡ„дәӢдёҡвҖқ гҖӮ еҪўеҠҝжҜ”дәәејә пјҢ дҪ•еҶөжҲ‘зҡ„жҖ§ж јз»қдёҚжҳҜзү№з«ӢзӢ¬иЎҢ пјҢ иғҪеӨҹеҚ“然иҖҢз«Ӣзҡ„ гҖӮ
д»Үе…Ҳз”ҹеҺ»дё–еҗҺ пјҢ жҲ‘еҺ»зңӢжңӣеёҲжҜҚ гҖӮ еҘ№жӢҝеҮәдёҖдёӘеҸҢе®үе•ҶеңәжүӢжҸҗиўӢ пјҢ йҮҢйқўиЈ…зқҖдёӨ瓶酒 пјҢ иҜҙпјҡвҖңд»–дёҙеҺ»еҢ»йҷўд»ҘеүҚ пјҢ иҝҳеҳұе’җиҜҙ пјҢ иҝҷдёӨ瓶酒з»ҷдҪ з•ҷзқҖ гҖӮ д»–дёҚиғҪе–қдәҶ пјҢ зҹҘйҒ“дҪ иҝҳиғҪе–қдёҖзӮ№ гҖӮ вҖқжҲ‘йҒ“и°ўжҺҘиҝҮжқҘ гҖ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