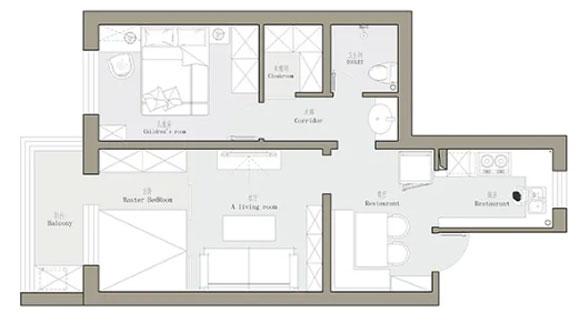戴手表



作为记录时间的工具 , 手表自诞生之日起便为世人所着迷 。 每一款手表都住着一个灵魂 , 无论是简朴凝重 , 还是高贵奢华 , 它们都以独特的方式演绎着自己的人生 , 诠释着你和光阴的故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 手表属于奢侈品 , 谁家如果能有一块国产的机械表 , 几乎就和今天“德国制造”的徕卡相机镜头一样牛逼 。 如果是进口表 , 就像今天的德系汽车 , 在和别人介绍时更会着重地强调一下产地 , 特别有面子 。那个年代 , 男人娶亲时将手表、自行车作为首选的聘礼 。 家境好的还要再加上一台缝纫机 , 那就锦上添花了 。 现在看来 , 手表的价钱是毛毛雨了 , 但在那时却是天文数字 , 要辛辛苦苦地积攒许多年 。那时 , 戴手表不被人知 , 犹如锦衣夜行 。 记得我读初中时 , 一天早上 , 班主任张老师在上操时举起双手向同学们呼喊:同学们注意了!只见他的手腕上有一块明晃晃的手表 。 同学们都在惊喜地相互转告:快看 , 张老师买表了!不言而喻 , 张老师那天充满了喜悦与自信 , 他的目的巧妙地达到了 。儿时 , 从谍情小人书、收音机的故事会中 , 获悉手表是识别特务的标记 。 梅花表是我读初小时知道的第一种也是唯一的洋表 , 因为大叛徒大特务都是戴梅花表的 。那时最好的游戏就是在手腕上画表 。 记得我还专门用圆珠笔画上去 , 这样不容易洗掉 , “戴”的时间可以久一点 。 有时为了把手表画的圆些 , 就用墨水瓶盖盖个印印 , 现在想想真的挺有趣 。 虽然手腕上的表针不能动 , 却带走了我最宝贵的时光 。父亲有块瑞士表 , 是五十年代初节衣缩食买的 。 对于那块进口名表 , 我一直非常崇拜 , 总喜欢把它从父亲的手上取下来把玩 。 拧一拧发条 , 或者盯着转动的秒针发呆 。 因为年幼 , 那时我看不懂几点几分 。小升初考试时 , 父亲曾借给我戴过一天 。 那时 , 穿白网鞋的小女生都会被同学说成是资产阶级 , 更不用说戴进口表了 。 现在想想父亲胆子也真大 , 居然敢把手表给我戴 , 也不怕弄丢 。六十年代初 , 表姐夫刚入伍就买了一块国产表 。 连长知道后多次批评 , 说他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享乐主义思想 , 吓得他再也不敢戴了 。那年表姐夫从部队上回来探亲 , 表弟寸步不离 。 大人们在一起说话 , 他总是站在旁边 , 两眼紧紧地盯着姐夫手腕上明晃晃的手表 。 一天 , 他壮着胆子说:“姐夫 , 让我戴戴你的表行不?”表姐夫笑了笑 , 把手表戴在了他的手腕上 。 那一会儿 , 表弟美得简直兴奋的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 表姐夫可能怕他把手表弄坏 , 只戴了大约一分钟就要了回去 。麻绳绳总是从细处断 , 人倒霉和凉水也塞牙 , 放屁能砸了脚后跟 。 就在表姐夫回来探亲的第二天 , 他不留神将手表滑落到毛司里 , 当时他急得团团转 , 死的心都有 。 幸好大队广播站有磁铁 , 他用根绳子绑着磁铁想把手表吸上来 。 可是不管咋弄手表就是不上钩 。 他没放弃 , 最后决定一桶一桶地将粪水清空 。 从中午1点舀到了下午5点 ,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 当粪汤还剩不多的时候 , 他当着全部人的面作出了一个很崩溃的举动:跳进臭气熏天的粪池里 , 用脚摸索着 , 最后终于将那块“蝴蝶”表找到 , 在场的人都看呆住了 。 那天他跳进御河里整整洗了一个晚上 , 尽管衣裳左搓又揉 , 半个月身上还有臭味 。 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得胜堡 , 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 直到现在还有人不时提起 。直到文革 , 全得胜堡也没有一块表 , 掌握时间全靠鸡叫 。 鸡叫三遍 , 冬天约摸五点 , 夏天更早 。 所以 , 农民甚时候起炕 , 全凭鸡婆提醒 。 到了上工的时分 , 穿戴好 , 拿上红宝书 , 就等队长吹哨(这时已经不是敲铁了) , 集中到队部进行“早请示” 。 全队主要劳力都到齐 , 需要一个小时 。 然后列队分成两排 , 站在主席像前唱《东方红》 , 接着在队长的带领下手拿红宝书喊“万寿无疆” , 一天的营生就算开始了 。 白天的时辰全靠阳婆的高低来估摸 。 天阴的日子 , 依据生物钟 , 也能估摸个不搭离 。那年 , 表弟和堡子里几个要好的小伙伴商量着国庆节去丰镇看热闹 。 没钱买车票 , 他们只好约定步行去 。 为了在丰镇城里多玩一会儿 , 因此就把出发的时间定在凌晨三点 。 那时 , 得胜堡就饲养院有一只闹钟 。 为了准确掌握时间 , 所以那晚他们就让三猴睡在饲养院的大炕上看时间 。 悲摧的是 , 三猴没看对长短针 , 凌晨一点就把大伙喊起来上路 。 二十多里路 , 走到丰镇天还不亮 。 他们没地方去 , 只好坐在铁路旁看南来北往的火车 。 大约看了两个多小时的火车 , 天才慢慢亮起来 。 表弟说 , 如果有一只手表 , 哪怕是一只破手表 , 他们也不至于白白地浪费几个小时的睡觉时间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或更远一段时间 , 手表绝对是身份、气派的象征 。 在农村 , 手表似乎成了“吃商品粮”“拿工资”的标志 。 买车票、买电影票 , 手伸进售票窗口 , 再挤再乱再多的手在一起挥舞 , 服务员也总是优先戴手表的那只 。 那年头 , 两人若是在路上碰到了 , 问一声:“同志 , 几点了?”那是最好的恭维话 。那时 , 得胜堡有一位戴手表的民办老师 , 一年到头 , 那怕是数九寒天 , 衣袖依然卷到恰到好处的位置 。 问一声:“同志 , 几点了?”他总是极为职业化地把手往天空一伸 , 晃动数次 , 然后快速收回 , 认真察看 , 准确地告诉你是北京时间几点几分几秒 。那个老师喜欢在公共场合露脸 , 为乡亲们义务报道准确的分毫不差的“北京时间” 。 可是 , 得胜堡卖肉的那个老汉却看不顺眼 , 有一次还气呼呼地跟人们说:“我最讨厌那个圪泡啦 , 狗爪上戴一块破表 , 老在额的肉摊上刨来刨去 , 问猪肉多少钱一斤 , 又不买!”改开后 , 表哥二锁在堡子湾公社小学教书 , 那时他已属大龄未婚青年 。 虽然家里底子薄 , 经济不宽裕 , 但基于他当时民办老师的身份 , 前来说媒的人还是有的 。 但一旦彼此相亲见过面后 , 不知为何 , 总是无疾而终 。 事后终于有人传了话过来 , 说是既然当老师 , 手上咋就连一块手表也不戴 。纵然二锁一表人才 , 也与当时小干部的流行打扮相契合 , 中山装上衣口袋里突兀的两支钢笔笔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 却到底因为伸出手来 , 手腕上看不见手表 , 而让闺女们心里起疑 。排除万难 , 也要去争取胜利 。 弄清楚事情的原委后 , 二锁最后一次相亲便采取了“草船借箭”的策略 。 临行前 , 硬是跑到公社教育组 , 找教育干事借了一块手表 。 自然这次的功夫没白费 , 他彼时的新娘 , 就是今天我已年近古稀的表嫂 。记得我曾经打趣地问过表嫂:“嫂嫂 , 你和二锁是咋认识的呀”?表嫂说:“咋能认识呀 , 那时候都是媒人介绍的 , 见一面就结婚了 。 ”我又问:“你凭啥见一面就看上他啦?”表嫂说:“还不是因为那块表 , 但是见了一面后就再也没有见他戴过了 。 ”二锁成家时 , 雁北娶媳妇已开始流行 “三转一响” 。 按说庄户人看阳婆过生活 , 要手表也没有 。 但人家女方索要 , 表哥没有办法 , 只好七挪八凑地给女方买了一块“钟山”牌手表 , 也叫支农表 , 三十元一块 。 过门后 , 新媳妇天天挽起袖子戴着表在村里晃悠 。 有人知道她不识字 , 故意问她:“你戴着表呢 , 给咱们看看几点啦?”表嫂抬手腕眊眊 , 再抬头瞭瞭日头 , 说:“十一点啦 。 ”表嫂也一天书也没念过 , 一次问我几点了 , 我说:“五点五十啦 。 ”她说:“哦 , 才五点多?”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 母亲就吩咐我 , 花钱要仔细 , 节约下钱买上一块好表 。 从此我把母亲的话铭记在心 , 数年如一日地节衣缩食 , 为拥有一块手表而艰苦奋斗着 。我的第一块表是1970年母亲给买的 , 上海牌全钢男式手表 , 一百二十元 。 听母亲说 , 这块手表买的很艰难 , 因为按百货公司的规定 , 买表不仅要票证 , 还需要单位革委会审批 。 单位革委会必须在票证的背面签署意见、加盖公章 , 商店才予以受理 。 记得联营商店发的那张购货票 , 背面印着这样一段话:最高指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革命委员会(军管小组)负责同志: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 , 而且越来越好 , 市场活跃稳定 。 近年来手表的生产和供应虽不断上升 , 但还不能满足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 。 为了坚决贯彻和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 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 打击投机倒把 , 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捣乱 , 本店对手表供应采取“定额分配 , 凭票供应”的办法 , 以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凡属叛徒、特务、党内走资派 , 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 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和反革命知识分子概不供应 , 请你单位在发放票证时严格按此原则处理 。 此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敬礼!呼和浩特联营商店19××年×月×日(公章)用今天的眼光来看 , 内容的确非常搞笑 , 但在当时 , 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 幸亏市立医院分管后勤的科长和母亲是老乡 , 母亲才得到了那张购货票 , 并在背面加盖了医院的公章 。手腕上第一次戴表的日子是我人生中的重大节日 , 欣喜之情难以言表 , 也招来许多同事的艳羡 。 那时 , 我只要没事时 , 就会把手表置于耳边 , 聆听那“嚓嚓嚓嚓”的欢快节奏 , 还有全钢的那种轻微而清晰的金属回音 , 那真是一种无比美好的享受 。我十分爱惜那块表 , 干活时用手帕垫在腕上 , 防震防水 。 只要表蒙子有一点污渍或划痕 , 就用手绢蘸着牙膏慢慢地抛光 , 否则就会心神不宁 。那块上海表 , 无法以货币价值来衡量 。 虽然花费了母亲数月的工资 , 母亲也没有丝毫感情投资的理念 。 它在我心中的价值无与伦比 , 那是我人生中的一个的亮点 , 凝聚着真爱、永远闪烁 。如今很多人都不愿戴手表了 , 要戴就戴名牌表 , 手表成了身份的标志 。 名牌表好几万元一块 , 戴手表成了成功男人的象征 。由于我胸无大志、自甘平庸、得过且过 , 自从流行石英表后 , 手腕上就再也没有戴过表了 , 有了手机之后更觉得戴手表没有必要 。 虽然后来 , 我也逐渐地意识到男人还是应该有一块好表 , 因为它不只是看时间的工具 , 更能体现佩戴者的品位 。 但因囊中羞涩 , 始终未能如愿 。前不久煤老板张总从美国回来 , 我们几个朋友聚在一起为他接风 。 他打开了一瓶路易十三请大家品尝 , 举手投足间有样东西甚是晃眼 。 见大家的目光追踪着他的手腕 , 他于是将腕表摘了下来放在酒桌上 , 让大家轮流观赏他的劳力士金表 。 轮到我时 , 用手掂了掂感觉有半斤重 。“在拉斯维加斯赌输了钱 , 一气之下去买了这块表 。 ”张总说:“前面连号的那只让国内一位著名的影星给买走了 。 ”那位仁兄事业发达但平时总爱生气 。 他冲冠一怒买下价值八万美元的这块手表只是为了出出晦气 。“老韩啊 , 到了这把年纪也该戴一块体面一点的表了 。 ”他一边对我劝说 , 一边把纯金劳力士戴回自己腕上 。我暗自寻思他那块表戴在我手上会如何:一来别人会怀疑其真假、二来人身安全恐无保障 。 于是我笑着对张总说:“等我把房子卖了再说吧 。 ”“哪里哪里 , 喝酒喝酒!”他连忙打住了这个话题 , 脖子一仰又喝了一杯路易十三 。
推荐阅读
- 扬子晚报网@醉酒后苹果手机和欧米伽手表都丢了,记不清丢哪儿了,三天后还能找回来吗?
- 手表@益阳一男子多次伙同他人行窃,落网时还带着失主的手表
- 『苏州公安』蟊贼施展“缩骨功”盗窃手表?抓你没商量!
- [何某]偷了老板手表潜逃,两年后落网感叹:昆明警察真厉害!
- 【手表】男子试戴手表没付钱拔腿就跑还亮刀威胁 涉嫌抢劫被刑拘
- 【临泉】阜阳一男子试戴手表拔腿就跑!你绝对猜不到原因…
- 「手表」商人把价值9万的劳力士手表扔上房顶 这操作把持刀劫匪惊呆了
- 山东青岛等一把手表态:今年GDP增长目标是10%
- 新天地会长跪地谢罪 刻朴槿惠名字的手表亮了(图)
- 「医护人员」按摩、画手表、做挎包……江苏医护人员悉心照顾“老小孩”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