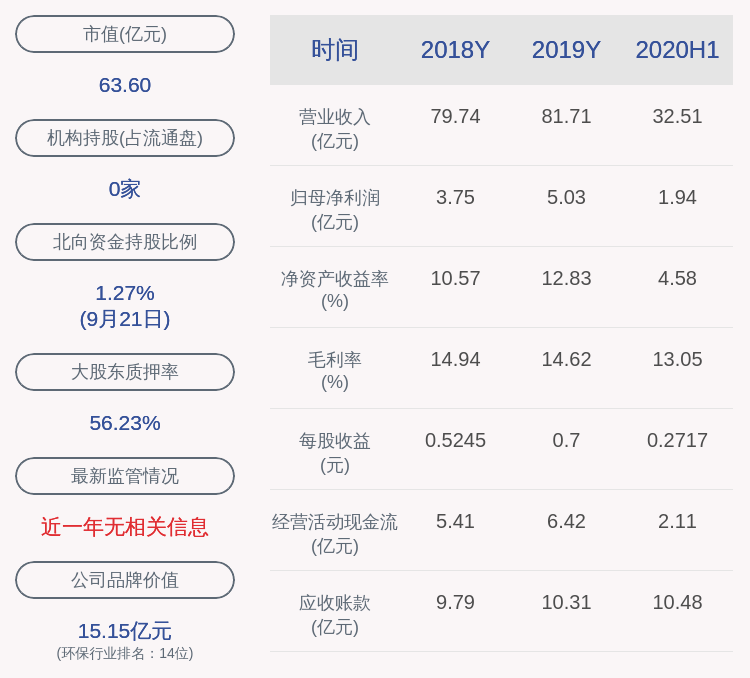看片
看片 1、日子有时感觉很快 , 有时又觉得很慢 , 觉得很快时 , 就起了些忧心 , 隐隐不安 , 而觉得慢时 , 日子就会有点磨人 , 须得有些手段对付才好 。 网上看片有几年了 。 也碰到很多烂片 , 有的看了一节就只得放弃 , 有的硬撑着看完 , 有些上当受骗的感觉 , 一下午或者一晚上什么也没留下 , 心里只留下些莫名的懊恼 , 仿佛上好茶叶被温水泡了 。 是的 , 也没有谁赖你看 , 是你自己无聊、手欠点的 , 怨谁呢! 但是仁爱博大的互联网 , 还是免费提供了很多好片 , 让无聊赖的日子不那么磨人 。 若要襟怀坦荡说点实话 , 前互联网时代 , 是有过一段不堪的日子的 。 那时的“看片”特有所指 , 后来又叫“看毛片” 。 朋友中有人好不容易弄了两盘录像带 , 却苦于找不到放像机 。 动用所有关系 , 最终查到县里搞团委工作的同学可以借的 , 就约定市里几个同学晚上去他那里 。 书记把他老婆提前支回市里娘家 , 一人在家利利落落等市里的我们几个老同学 , 让我们的带子和他的机子遇合 , 上演一出好戏 。 好事多磨! 夜里8点多了 , 天早已是完全黑下来 , 没有月亮 , 寒风强劲 , 标准的月黑风高之夜 , 我们骑着自行车向县里疾驰 , 迎面的寒风 , 刀一样割脸 , 还粗鲁地往嘴里灌 , 艰于呼吸 , 一刀刀割脸 , 却又被冷风压得抱怨声把的气力都没有了 , 也只好顾不得脸面 , 麻痹地顶撞着寒风 , 心里想着“好事多磨” , 古人这四个字下得!这位古人恐怕也有过我们一般的经历 , 才有此想的 。 一行人中 , 有一个其实不是我们同学 , 是个搞美术的 。 不知被谁带到我们这支队伍里 , 这有违我们事前定下的纪律了 , 这次特别行动 , 我们曾反复强调严格控制在我们市里要好的几个同乡同学之中的 。 但是违反也就违反了 , 临场也没谁较真的 。 ——只是这个梁姓的搞美术的外乡人 , 祚薄寿短 , 因为心脑疾病 , 几年前他停在了48岁上 。 后来他记忆里如我还装着这件事吗?谁也不知道了 。 世间事就这样吧 , 很多都是无关紧要的 , 记得也行 , 遗忘亦可 , 做完了数不胜数的两可之事 , 也就用光了一生的时 。 记得那天晚上 , 他在跨上车之前 , 套上了一个大口罩 。 他车龙头偶尔和我并行 , 我想他心好细啊!我用余光扫扫他 , 大白口罩让他显得肃穆、庄严 , 也让我们这支穿过冬夜寒风的队伍 , 有些像敌后武工队 。 平时喜欢高谈阔论的高姓同学 , 也一句话没有 , 勤勉地踩着车踏 , 寒风中 , 他的国字脸颇刚毅的样子 。 他在想什么呢?不知道 , 一如他不了解我 , 我也不掌握他 。 还有一层 , 高同学大我岁把 , 是有了家室且妻子貌美的 , 他算是队伍里唯一例外吧 。 然而那时并无违和感 。 寒风也从领口灌进去 , 虽然领口是扣严了的 , 但那里依然像砸破了玻璃的后窗 , 整个人像掉进冰河里刚捞起的样子 , 两个腋窝都是冷的 。 可心却是热的 , 并非暖热 , 而是燥热 。 恐怕通体也只剩下这一处是热的了 。 嘴唇有些抖 , 上下牙控制不了像两块玉佩或者瓷茶杯的盖和杯 , 轻微地不住碰撞 。 我想这一半是因为寒风 , 另一半 , 恐怕是心的燥热造成的吧 。 我们抄最近道从市到县 , 也不过10余里 。 书记家在县城一所学校西侧的高处 , 削平了的山头有几栋红砖墙教室改成的教师简易平房 。 县里学校条件有限 , 书记同学多年一直想调到市里却没能越过政策门槛而不能成功 , 只好在那里成了家 , 单身的房添了个女子就成了婚房 , 另外 , 窗玻璃某处有一个喜字大约当年粘得太牢靠 , 儿子落地多年 , 也没有除去 。 那一栋平房还另有几个单身汉教师 , 有时我白天去玩 , 他们没课就会聚拢来 , 但是晚上一般都不大在 , 我想应该到市里找对象去了 , 是书记当年一样的路数 。 所以晚上那里很空寂 , 我有时偶尔路过那里 , 连书记同学也已不在了 。 我们一行推车上去 , 那里果然还是空寂 , 清瘦的书记同学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笑吟吟出来相迎 。 我们7辆自行车 , 叮当哐啷门前排成一排 , 气气派派的 , 多少教那里的空寂有些改变 。 好大一会 , 才见书记从屋后过来 。 我怀疑他是上后面那简陋公厕去了 , 他却笑吟吟地解释说:“我去后面总务主任家了 , 问问电什么时候来 。 ” 哦 , 原来停电了! 我们才注意到 , 的确漆黑一片 , 远处几家的亮光也都蔫蔫的 , 似乎含了些忧愁 。 我们才明白 , 我们只注意到带子和机子两大要素 , 上演好戏其实是三大要素的 。 是啊 , 那电 , 怎么就忘了呢! 那就等吧! 电什么时候来 , 书记说总务主任也没给说法 。 于是把家里长短不一的所有蜡烛 , 包括塞在暗角的好几个蜡烛头 , 统统寻了来 , 大家齐动手都点上了 , 四处滴蜡立住 , 可烛光总还是显得不那么光明正大 , 有些苟且的样子 。 大家东拉西扯地说闲话 , 心里却都惦记着天花顶上的电泡 , 希望它在头顶突然爆炸一般亮了 。 但是大家的希望随着冬夜渐渐延长而不断耗散 , 仿佛寒凉中的一碗没加盖、就那么敞着的热汤 。 也许书记觉得让大家失望有些对不住吧 , 他掩藏了自己的失望 , 始终保持着笑吟吟的健康快乐情绪 。 他望着门外的一溜自行车 , 搞笑地说:“这要是当年放电影时的发电机就好了 , 大家轮流踩电 。 ” 大家呵呵一乐 , 可失望情绪还是渐渐坐大 。 忽然 , 书记拿起黑色的录像带 , 假装抽出一段胶带 , 闭起一只眼 , 独眼斜对着蜡烛瞄:“干脆这样看吧!” 书记一下子把一屋子情绪都有点失败的年轻人都哄的逗笑了 。 之后书记提议煮点饭吃 , 在煤气灶上煮了一大锅饭 , 蒸了几块咸肉 。 很香很香 , 多少年后大家还觉得那个冬夜的饭香咸肉香有些异样 , 似乎所吃过的饭和咸肉从未如此喷香过 。 可是大家吃罢抹完嘴巴 , 电还是没来 。 饭香和肉香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 或者说 , 它们解决问题的能力终究有限 。 那阴着的妖雾显然重又拢了上来 。 这也是没法子的事 。 好几个蜡烛头早已是瘫倒熄火不干了 , 而几支高大轩昂的也都已变成了蜡烛头 。 高同学认命地叹了一口气说 , 回府吧!他把录像带在桌沿轻轻敲敲 , 带子稀里哗啦的 , 声响是硬塑料特有的那种轻薄又夸张 , 仿佛提醒大家:我肚里有货的呢!可不来电 , 就什么也不是 , 不过一黑塑料盒 。 书记好不容易借来的放像机 , 虽然高科技 , 浑身布满各种金属按键 , 很高端地娴静伏卧桌上 , 仿佛一穿戴考究的黑衣渊默女子 , 可是没了电 , 也不过就是比带子大一些的四方塑料盒而已 。 2、肖有次来我家坐 , 电视里忽然是向 , 他在对稿讲话 , 大约是市里的一个什么会议吧 。 听了几句 , 肖扭头问:“记得不?” “记得什么?” 肖笑了:“妈的 , 我俩的第一次 , 就给他了 。 ” 哦 , 这个啊 , 记得记得 。 我也笑了 。 向多年前是我们老同事 , 他能说会写 , 按百姓说法 , 有点本事 , 他现在已然市里领导了 。 记得当年向经过我们单身汉大院门口上公厕 , 回来时和我招呼 , 说去他家 , 我问干什么 。 “看片!” 我想大约是《魂断蓝桥》之类的文艺片吧 。 其实那时 , 文艺片我已经不象在大学时代那么上心了 。 但是人嘛 , 上心的东西总是有的 。 当然我也答应了 , 就问可不可以带上肖 。 “可以 。 ” 他似乎没立即回答 , 离开走了一截 , 才朝背后扔了两个字 。 我和肖在预备了的小矮凳上坐下来 , 向便让放像机吞了带 。 电视机的画面虽粗劣不堪 , 却直接就是了 。 可怜!人生那个节点 , 我和肖都正在满世界翻找自己命定的女子 , 都还不曾和女性发生过真正的交往 , 但是那一刻 , 那粗劣的画面那么粗野地一把就扯掉了遮蔽另一世界的厚重布幔 。 没有任何过渡 , 仿佛两根棒冰 , 直接就被向扔进了青烟袅袅、滚腾着的油锅 。 3、一个晚上 , 几个好友在我校玩乒乓 。 临了分开 , 时从双肩包里掏一黑塑料袋给我 , 我问是什么 , 时不说 , 挤挤眼 , 附耳要我回去看 。 时算是我玩了多年的密友了 。 他玩什么像什么 , 比如乒乓、绘画、乐器 , 一玩就玩到一定的高度 。 且不说什么扯不清的天赋 , 时勤奋甚至勤苦 , 可以入定 , 这显然为我等所不能及 。 有时我们背后或者当面玩笑说 , 时和恒河边那个把左胳膊树枝一样举一辈子不放下的人 , 也许可以归为一类 。 时的为人 , 内敛、清高 , 自律、可靠 , 也为我内心所认可 。 他让我回家看 , 那就回家看吧 。 其实我是到第二天上午 , 妻已经上班 , 我上午没课 , 我喝着早茶 , 一个人在网上闲逛 , 才想起那个黑塑料袋 , 里面那柱状硬物 , 也还不知是什么 。 打开一看 , 原来是碟片 , 摞在一起 , 就成死硬的长圆柱了 。 都没有封套 , 直接就是碟 , 背面一律印有恶俗画面提示着碟片的性质 。 我不禁叹道 , 这家伙 , 弄这个都是异乎寻常 , 他的专勤也能用到这啊!如若绘画、音乐属于厅堂的话 , 那这饮食男女当归于庖厨之事了吧 。 我掂掂黑袋 , 呦嗬 , 都一两斤了呢! 我曾在南京呆了一年 , 晚上逛电子一条街 , 迎面总有人鬼祟兜售这个 , 可是我哪里敢要 , 怕遭不良之徒陷害 。 如今好了 , 一下暴富 。 只是 , 我的联想台式电脑 , 还是刚刚购买的 , 主机是湖蓝色的 , 文雅又高端 , 有些像涓生、子君那样的五四新青年 。 它能干这个? 不知怎么忽然就记起了我高中时代那个工农兵大学毕业的政治老师常挂口边的话——“事事有矛盾 , 时时有矛盾” 。 是的是的!有谁知道那个平静的上午 , 那个空寂客厅里的我 , 正落入一个空前的矛盾之中 , 仿佛撞上丝网、被卡了鳞片的“青混” 。 我横了心将第一张碟片插入湖蓝 , 是和平生第一次行偷 , 战胜忧惧 , 手第一次伸进别人的口袋 , 并无二致 。 矛盾的丝网是摆脱了 , 但仿佛被生生揪扯掉了好些鳞片 。 接下来的几个日子 , 有些昏胀 , 有些浑浊 。 那条本是湖泊里的“清混” , 一下子误入了小水凼 , 稍一摆尾 , 就能给小水凼掀起巨澜 , 仿佛更孔武有力似的 。 可是原先的相忘于江湖的悠闲自在没有了 , 平静悠远没有了 。 满眼都是吃的 , 也只剩下吃的了 。 局促 , 躁动 , 不安 , 浑浊 。 一种前所未有的厌恶和警觉忽然就盘踞上来 , 越加勉强的换碟变得再也不能坚持 。 终于 , 我把嘟囔的黑袋压瘪 , 用两提耳迅速打了个死结 。 我拨通了时的电话 , 说马上打车将碟片送还他 。 他笑了:“那么多 , 你就看完了?小心弄爆了眼球哦 。 ” 我说:“哪啊!还不过几片 , 就被大肥肉放倒了 , 醉肉了!” “哈哈 , 你担忧吃饭没了胃口了吧?” “呵呵 , 也多少有点吧 。 反正 , 厌得很 , 很厌很厌!这种厌还不同别的厌 , 很厌很厌的 。 呵呵 , 这日子还长呢 , 怎么过啊 。 我是实在坚持不下来 。 你自己全看掉了?” “嗯 , 是啊 。 呵 , 瞧你那身板 , 胃口!呃 , 自然还是要和现实切割的 , 断开的 。 这种东西 , 我只当粗劣的文艺片看 , 也就是专看身材和脸蛋的 。 反而我把一流的文艺片 , 比如《教父》、《亚特兰蒂斯之心》、《与你同行》、《怦然心动》之类 , 当纪录片看 , 很当真 。 ” 时说得我有些不明所以 。 他说看过就看过了 , 又不是文艺片 , 一次性筷子而已 , 洗洗再用也没什么必要 , 让我自己处理 。 我一时也没想清怎么处理 。 就仔细观察卧室 。 自搬进楼房 , 真还是第一次这么认真打量自己的卧室 , 似乎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熟悉 。 最终确认了一个暗黑、安全的地方 , 让黑塑料袋暂寄身 , 并覆以杂物 。 扔掉似乎不必 , 等哪天再找个下家吧 。 这么一放 , 一两年就过去了 , 我都把它忘了 。 一个星期六的上午 , 我买菜刚进门 , 只见套着围裙搞卫生的妻 , 朝我兜头喝到:“堕落 , 你堕落!” 头一回受此重话 , 我有点发懵 , 她满面通红 , 有些可怕 。 “怎么了 , 发什么疯 。 ” 我努力保持镇定 , 淡然说 。 她并不应 , 我放下菜袋 , 四下看看 , 一下瞥见电脑转椅上的那个黑塑料袋 , 那个提耳死结已被剪开 , 仄着的碟片已裸着一段黑脊 , 我体内的血一下冲上了头 , 一把火腾的就在脸上烧起来 。 “什么人给你的?你都在和什么人一起玩?” 她声音有些嘶哑 , 哀伤 , 音量不大 , 是对内心直接的传达吧 。 我一瞬间的发懵稍稍好了一些:“哦 , 那个啊!我在路上捡的 。 也看了两张 , 翻了胃 , 就塞那了 。 都摆那两年了 , 我都忘了 。 ” 自己这应急的话 , 虽夹杂了谎言 , 但也大半真实 , 即便谎言 , 也是只为了维护朋友以及我自己的清誉而已 。 一瞬间我也自我欣慰起来 , 也就渐渐稳住了情绪 , 脸上的火也快熄灭了 。 接着 , 思路也有了 。 我拿一份旧报纸 , 摊开像一床单 , 一把盖了转椅上那个难堪 , 胡乱打滚卷了 , 说:“我去扔掉 。 ” 楼下不远处就有几个垃圾桶 , 那里暂时也没有人 。 这是校园啊! 教师家属楼垃圾桶忽然仿佛有些高大、矜持了 , 有些凛然不可犯的样子 。 我捧着的不成形的报纸团似有些德不配位了 。 我估摸着 , 扔进去大约也就稀里糊涂被垃圾车拉走的 , 即便暴露了 , 也不可能怀疑到我 。 但是 , 还是别在这吧 。 我心事重重出了校门 。 门外就是川流不息宽阔马路 , 人们各自奔忙 , 都自然坦荡 , 意气风发 , 也许只我有些奇怪吧 。 丢马路上 , 虽也并无风险 , 但稍有良知 , 也就不会做的 。 我忽然发现 , 迄今为止 , 我人生之篇里 , 真还就没在这亮堂的马路上乱丢过一团卫生纸的 , 更何况眼下我手里头很不自然、不舒适捧着的有些奇形怪状、不衫不履的这秽物 。 那就走吧 。 我丢了魂一样地走 , 走了好一段 , 我发现自己是朝北边去的 。 马路边有几家大的单位 , 门前都是有垃圾桶的 , 有的垃圾桶边正有人 , 地税 , 区教育局 , 我经常去打球 , 熟人多 , 我稍一犹豫 , 又滑了过去 。 来到移动公司 , 上了向西的一条小路 。 马路上就能看到移动公司青年男女的白领模样 , 这是一个注重形象的现代企业 , 垃圾桶都漂亮些 , 也有些白领的气质 , 我只看看就算了 。 接下来是一溜小饭店 , 有一些垃圾桶 , 储满了脏东西 , 可是有好几位肥婆子在小矮凳上择菜 , 都探望着我造型奇特的报纸卷 。 一溜下来 , 是南北向的后塘一路 , 我向北去 , 北端出口不远处 , 是友好菜市场 , 菜市场的垃圾桶应是更多 , 更大 。 忽然发现 , 有人对我招手 , 浓妆艳抹的 , 我才想起 , 后塘一路美容美发、洗脚房、养生池一家挨一家 , 一到傍晚很多玫瑰灯屋即如洗澡花一般开了 , 本市市民心里 , 这儿其实就是红灯区的 。 我平时走路尽量不走这条道 , 除非骑车快速穿过 。 又走一段 , 屋里有两人朝我招手 , 一年轻的 , 一中年妇 。 中年妇还压着嗓撩我:“帅哥 , 玩玩呗!” 已经持续了好一段时间的懊丧又忐忑的我忽然来了灵感 。 我厚颜也用笑抵住她们的笑 。 她们有些期待地望着我 。 我完全没有在意她们的望 , 投进去的时候 , 有些磊落、坦荡 。 2019101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