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评论区里 , 有如今互联网上少见的包容和默契 。 他发一些没头没尾的情绪 , 比如 , “我今晚特别感性 , 一直在被感动一直在流泪” , 粉丝也不追问怎么回事 , 只是说:“一定是个你喜欢的故事吧 , 真替你开心 。 ”
白居易和“妖猫”
可能也因为这股向内生长的情绪 , 面对每一个角色 , 他都有融入骨血的塑造能力 。
盲人、诗人、文艺兵、乡村青年、翻译官……他说他们都不是他 , 又好像每一个都是他 。
黄轩曾对《南方周末》 , 回忆了他演《妖猫传》的细节 。 白天拍戏 , 晚上喝酒、不停地读诗 。
每晚临睡前 , 他都会打坐 , 自我催眠 , 心里不停默念“我是白居易” 。
《推拿》快要拍完的时候 , 他觉得像是“抛弃了一部分自己的感觉” 。 《只有芸知道》杀青 , 他说“又一次人生” 。 《山海情》播完 , 他说“像是在告别一段人生” 。
2014年《推拿》 , 2021年《乌海》 ,
眼里的故事不太一样了
“这两年我越来越熟练地 , 把戏和生活区分来 , 但是自己的感受是抹不掉的 。 ”
某种意义上 , 他的反思 , 他的孤独 , 都让他得以在纷乱的现实里 , 保护自己最真实的情感 , 在演戏这件事上 , 他不动荡、不急躁也不迷失 。
以下是黄轩的自述 , 从《乌海》谈到这两年的状态:
一冲动 , 我就演了
一开始我是拒绝出演的 。
2019年 , 我刚在新西兰拍完《只有芸知道》 , 想休息一段时间 。 这时周子陽导演给我发来《乌海》的剧本 , 看完我觉得好重 。 我刚从一个悲情的角色里出来 , 不想这么快再接一个沉重的作品 。
工作人员告诉子陽导演后 , 他给我写了一封信 。 信里讲他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 , 为什么想找我来演 。
我并不认识他 , 但我想他是一个非常有诚意 , 处于很纯粹的创作状态的人 。 我就说 , 那我请导演吃个饭 , 还是当面跟他说一下 , 为什么不能去出演 。
周子陽给黄轩讲戏
子陽导演有内蒙人的豪爽 , 见了面 , 说咱俩喝点 。 喝着酒 , 就跟我聊起他的过往 , 关于婚姻中的问题 , 拍电影遇到的困难 , 对社会现象的思考 。 他说话的时候很赤诚 , 让我一下想起了自己的过往 , 现实里遭遇的无奈 , 自己原生家庭带来的感受 。
我们越聊越近 , 就在饭桌上 , 我说:“咱俩就拍这部电影吧 。 ”
当时我的工作人员就在旁边 , 他说:“咱们说好的 , 过来是跟导演好好说一下 , 怎么你就决定要去了?”
就那一刻 , 接这个作品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 有时候我有一种冲动 , 没有那么理性 , 那么严丝合缝 。
在乌海“放羊”
我问子陽导演 , 为什么叫《乌海》?他说你不知道 , 乌海是个城市 。 我说这城市 , 名字还挺酷 。 他说这城市 , 非常特别 。 我说咱俩去一趟?他说你有时间吗?我说我在休息 。
第二天我们俩就跑去乌海 , 拿着剧本 , 从第一场到最后一场戏 , 所有的地方我们俩走了一遍 。 这个人物在这里生活 , 他每天会去哪里吃饭?他开的什么车?他小时候是在哪里长大的?上哪个小学?他的爸爸妈妈是一个什么状态?剧本里没有写的 , 我们把它联想出来 。
几乎没有演员在开拍之前 , 会跟着导演去堪景 。 但这次 , 连合同都没签 , 什么都没有 , 我就整个已经投入到故事里了 。
黄轩和周子陽在看监视器
后来我去学了乌海话 , 直到现在 , 我们都喜欢给对方发微信语音 , 只说内蒙话 , 问候起来特亲切:干甚呢?我搁北京拍戏呢 。
以前跟年长的导演拍戏 , 他们算是我的长辈 , 有时候 , 我要想一想这话该怎么说 。 但子陽导演是我合作过年纪最轻的 。 我们都是80后 , 成长在同一个年代 , 有好多可聊的东西 。
年纪相仿的人之间 , 不会有那么多拘谨 , 亲密的时候像哥们 , 不爽了我俩就开骂:你这不行 , 这什么玩意儿 , 你会不会弄啊 。 肆无忌惮地沟通 , 让我感觉到一种创作上的自在自由 。
挨了打、撞了妻子、烧了帐篷后 , 不同的情绪表达
两场戏
2019年底 , 我一进组 , 就想在戏内戏外都还原角色的真实情绪 。
他一直在路上 , 不断被突发事件牵着走 , 焦灼、压抑 。 戏里的那身衣服 , 我穿了一个多月 , 直到杀青都没换过 , 也不怎么洗头 , 头发油得一绺绺结在一起 。
有一场是 , 我和杨子姗在家里吵架 。 这段争吵非常重要 , 它彻底点燃夫妻之间的导火索 , 然后发展出后面的剧情 , 杨华变得无家可归 。
推荐阅读
- 罗伯特·帕丁森|反复被绿的罗伯特帕丁森成《新蝙蝠侠》主演,情场失意,商场得意
- 赵文卓|8天176万!赵文卓又拍了一部烂片,唯一的亮点是两个女配角
- 韩剧|过年必看的6部高分韩剧,每部都是精品,尤其是最后一部
- 明星|JK校服:我走起来,点在春日的碎片上
- 春晚|虎年春晚:12位新面孔,谁是你的菜?
- 罗云熙|罗云熙出道11年,颜值在线的他为什么迟迟不火?
- 李连杰|明明网上很火的电视剧,你却一集也没有看过,你中了几部?
- 穿搭|打底裤已经“失宠”!今年冬天流行这三种裤子,时髦的女人都在穿
- 林生斌|林生斌的事件何时有结果?冬天都到了,离春天还远吗
- 陶昕然|陶昕然挺有成熟女人味的,穿拼接泡泡袖裙贵气大方,身材也挺不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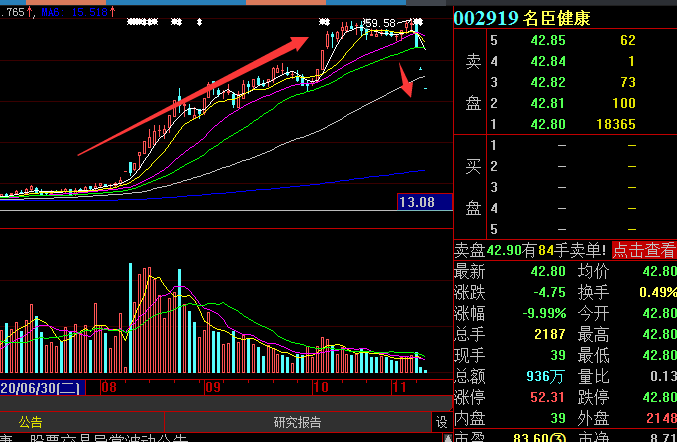



![[辽宁]辽宁省新增无症状感染者4例,均为境外输入,韩国、澳大利亚、泰国、英国各1例!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60例](http://ttbs.guangsuss.com/image/1460c9fc4209ef1a38b4718bc3e6ce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