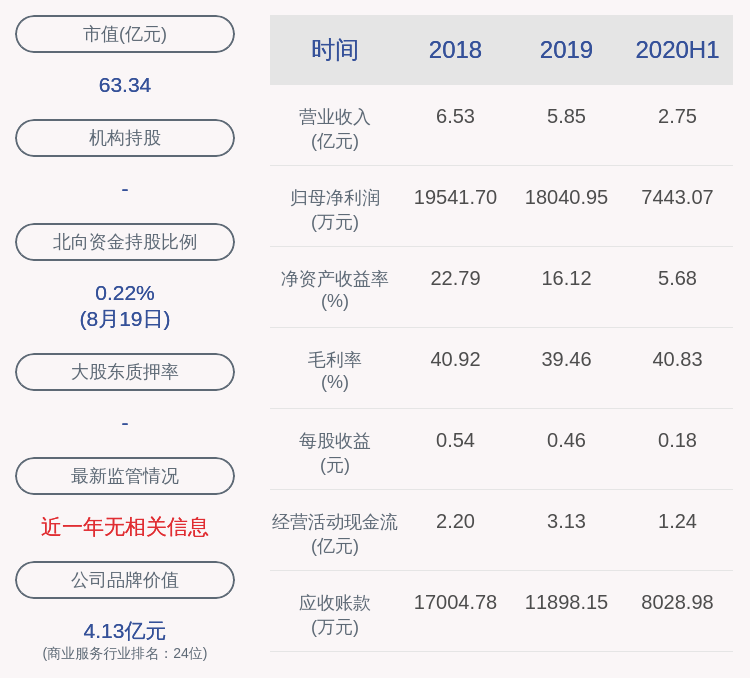像张玮玮说的,音乐剧《流浪之歌·河乐队》完全不是百老汇那一套。它像一群中年人老夫聊发少年狂,排了一出儿童剧。又像形式奇特的音乐会,陶醉着唱歌弹琴的人忽然开口说话,说着说着,再次滑进梦一般的音乐里。安娜伊思?马田、小河、张玮玮、郭龙、万晓利二十年前相识于河酒吧。二十年后,除了感情,没有一处地方、一个共同的梦想可以再次接纳他们飘流在没有尽头的时间里。一起排这么一出音乐剧,是他们给自己重新创造的契机。排练多快乐,安娜跳来跑去,大家一起唱歌,你唱我的歌,我唱你的歌,和声蒸腾起时间的雾气。
文章插图

文章插图
这个故事在儿童绘本里常见。从文本创作的角度,说它简陋也不过分。但故事不是最终落诸纸上。搬到舞台上,就有意思多了。导演应该想都没想过让演员们去“演”角色。每个人都不是专业演员,个人特质更难以掩藏,不如放大。万晓利白衣飘飘,人又削瘦,扮相如同八十年代的文艺青年。张玮玮和郭龙俩兄弟穿工装背带裤,一个像拉手风琴的土豆,一个像老了仍调皮的流氓。小河还是老样子,毡帽阔腿七分裤,发疯的时候像只猴子,有破坏性,狡黠,含着一股愤懑和引颈呼喊的渴望。
文章插图

文章插图
剧中的角色个个如同童话剧中会说话会唱歌的小动物。这些歌不怎么朗朗上口,是清浅情节中点缀的一只只深潭,神秘莫测,余韵悠长。观众都是怀着期许前来,多多少少听过他们的现场和唱片,追随或至少关注过中国现代民谣的脚步,在过去二十年的变迁中亲身荡涤过。民谣自发生长像竹笋必须顶破土地的力量感,与念着台词,努力表演,精心安排每一处细节的舞台形式产生了反差。他们因此变可爱了,朦胧恍惚中似乎返回青少年时代。可也要付出代价——被时间磨砺出的肃然与厚重被削弱了,和音乐共生的人的魔力,被框进了角色的小小范围中。河酒吧时代,安娜是刚到中国的留学生,和他们一起度过青春。她的相机留住当年群像,是为凭据,记录抑郁、重复和喷薄的生命时期。美丽的安娜也老了,她张开双臂唱歌时,蝴蝶袖微微颤动。剧中安娜饰演的安凭直觉应该是少女,担任通过寻找连接岛屿(人)的角色。非专业演员出身的安娜,没能赋予“安”这个角色更深的厚度。但当她硬手硬脚在台上奋力奔跑,大声唱歌,很像劲流划过快要死亡的岛屿,利刃裁破枯槁的纸张,犀利,赤诚,不可阻挡。
文章插图

文章插图
两个最有代表性的时刻。一是两兄弟吵嘴赌气,郭龙绕着长椅转圈,表示自己正在离家出走。幽默的情节和演员本身融为一体。略知他们经历的观众会马上想到白银,泛起原地打转的人生蹉跎之感。一边笑,一边想哭。另一个时刻是疯子小河,嘴里叽里呱啦唱一首很好听但歌词不明的歌。唱完,他疯疯癫癫地俯身反复把落叶抛向天空。小河是台上所有人中演得最不露痕迹的。但他演的也是自己,从前自己的一部分。偏颇的天才,缺乏理性审视自己处境的能力,没有幽默和欣赏的余裕;孤僻的疯子,没有人唱歌给他听。小河自己的经历和体悟,为这段表演注入真实的底色和流动细腻的层次。
文章插图
散场,有人被一群人一起玩音乐的简单快乐感染,下单了一只非洲手鼓。一起玩音乐,把音乐作为理想,然后懂得,音乐不是全部,但仍是非常重要的连接渠道。台上的人都已经过这个过程。现在他们以另一种迥异于以往的方式,把火种递给了别的人。(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推荐阅读
- 原创音乐剧《在远方》登沪 以艺术手段诠释现实题材
- 最新开票丨星期广播音乐会“南腔北调
- 音乐剧《在远方》致敬美好生活创造者
- 营造美好机关氛围青岛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德位书房举办午间音乐茶会
- “中国梦·劳动美”2021新年音乐会在北京卫视播出
- 向阳生长--陀乐乐团的非遗世界音乐之路
- 音乐声中辞旧岁迎新年
- 音乐会不按套路出牌:小毕哥现场吃起了大米饭,谢大脚跟着大爷学犁地!
- 阿云嘎变身“快递小哥”,音乐剧《在远方》讲述小人物的奋斗史
- 豆瓣9.6,苦等五年的神剧终于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