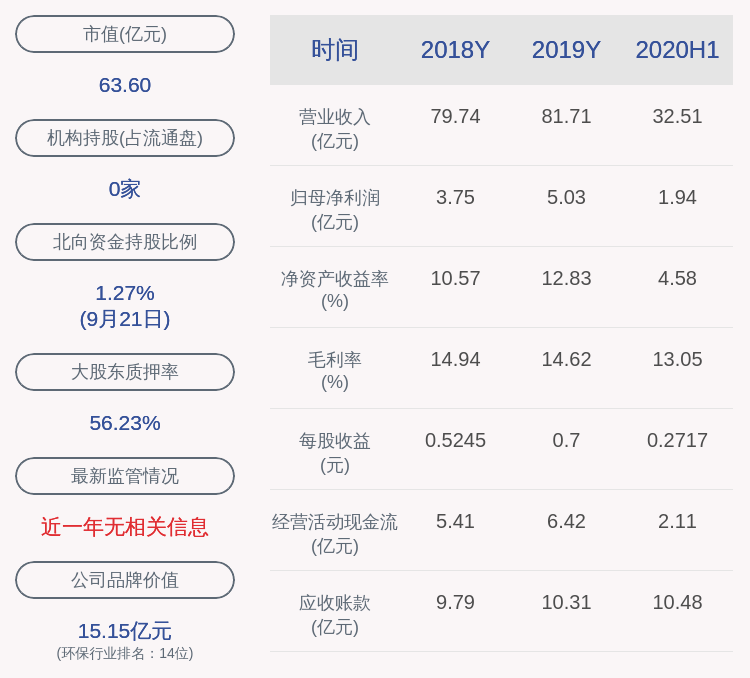大国小民|在城市的废墟中等了五年的类风湿病人( 二 )

姑姑当即报了案 , 警察到了现场 , 了解情况后很直白地告诉姑姑 , “这事情不可能立案” 。 媒体采访人员也来过 , 但是强拆还是在不断发生 。 姑姑说:“我们背后那一家院子 , 当时里面一个老人还吸着氧 , 被他们抬到其他屋子里 , 房子还是给拆了 。 ”被强拆的屋子里早已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件 , 但有几本姑姑珍藏的相册 , 有我刚出生时的照片 , 爷爷奶奶在世时候拍下的全家福 , 我父母结婚时的合影等等 。 拆迁办的人说屋子里的东西都收拾了起来 , 放在一间为姑姑提供的临时住房里 , 但她一直没有去过那间屋子 。 之后 , 她搬到了铁路边的小区里 , 是我父亲留下的老房子 , 在小区的顶层四楼 。 我小时曾在那里住过一阵 。从拆迁开始 , 到姑姑选择离开福村 , 已经过去了5年 。拆迁办的态度强硬 , 要求所有户主都要在场才能谈判 , 而大伯又总逃避——他觉得手里没有钱 , 谈了也没有用 。 因此 , 关于拆迁赔偿以及安置房的谈判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 至于我父亲的那份 , 一直是母亲在打理 。 在拆迁补偿的问题上 , 母亲与姑姑都独立处理 , 几乎互不联系 。姑姑四处托人 , 但处在社会底层的她 , 即便努力去寻觅 , 也只能像迎着大风张开双臂一样 , 很难找到能解决实质问题的人 。 她闹过、哭过 , 还找过残联 , 但都没效果 。 在2014年 , 姑姑曾联系上过一个“关系” , 把积攒的几万元递了过去 , 但事后一直没有音信 。 2016年下半年 , 她忽然给我打电话 , 带着哭腔说那个人不接她的电话 , 问我该怎么办 。 电话这头的我头晕目眩 , 没有丝毫头绪 , 但还是把那个“关系”的电话要了过来 。那人叫陈伟 , 跟拆迁办当时分管福村区域的领导走得很近 , 拨通电话前 , 我思来想去该如何开口 , 仿佛要打一场辩论赛 , 甚至做好了谈不成便用举报来威胁他的准备 。 电话拨通 , 我装出一幅深谙世事的语气跟陈伟嘘寒问暖 , 询问事情的进展 。 没想到他的态度很是坚决:“事儿我也烦着呢 , 我也不赚你几万块钱 , 不行就给退回去 。 ”我没有让他退钱 , 希望他能多上上心 , 他也满口答应 。 可当我两个星期后再次打电话询问时 , 他只告诉我要和家人出去旅游了 , 现在管不了这些事情 。 我顿时怒气上涌 , 可没等我发作 , 他便挂掉了电话 , 然后再也不接 。这件事兜兜转转 , 最后中间人调停 , 钱还是退给了姑姑 , 而事情显然没有进展 。2017年暑假 , 我去看望姑姑 。 我本以为搬到了楼房 , 姑姑的住宿环境会比以前好一些 。 可当我到了这个多年不见的小区时 , 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记忆中热闹街市早已消失不见 , 只剩下零星的几间铺子 , 给这里的居民维持基本的生活供应 。小区里没有物业管理 , 楼道墙壁满是污渍 , 杂乱不堪 。 当我推开门时 , 我看到了那张从福村搬来的床、几把椅子和一个“小太阳” 。 灯光一如既往的昏暗 , “小太阳”缓缓摇着头 , 散发出橘红色的光芒 , 是这个北方楼房里唯一的取暖设备 。 冷清的环境没有让姑姑不满 , 但是小区楼梯的设计的确让她有些头疼:“上下楼太不方便了 , 尤其是一楼的楼梯 , 又高又窄 , 实在太费劲儿了 。 ”不过 , 楼房相对干燥的环境少许缓解了姑姑关节的疼痛 , 相比起福村时刻担惊受怕的情形 , 这里还是安定一些 。我本以为姑姑能在这里度过一段相对平稳的时光 , 然后再去和拆迁办谈回迁房的事 。 可这房子还没住上半年 , 新的消息又通过父亲的同事传来——为了打通断头路 , 小区即将被拆除 。于是姑姑又得准备离开了 。 仿佛冥冥中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 , 不断驱赶着姑姑 , 让她总不能安定下来 。7当然 , 拆迁不是一蹴而就的 。 2018年春节铁路小区还没拆迁前 , 我去看姑姑时 , 她已经渐渐习惯了这处小房子 。 从福村到这个小区 , 我记忆中来看望姑姑的场景里 , 大伯几乎都在 。 我想起已经多年没去过大伯家 , 和婶婶也没什么联系 , 当即和大伯商量过年聚聚 。到了约定那天 , 姑姑和我一起买了200元的礼物 , 挤上公车 , 来到了北二环附近的大伯家里 , 见到了我可能已经十几年没见过的婶婶 。 进门后 , 姑姑热情地跟婶婶还有堂姐打招呼 , 并递上礼物 。 大家聊了一阵子后 , 便坐上饭桌 。我注意到大伯的状态很奇怪 , 他没有坐在沙发上 , 而是坐在桌子一角的矮凳上 , 眼神也从不主动和其他人接触 , 只是眯着眼看着桌上的饭菜 , 不时用舌头舔过自己的牙齿 , 上唇鼓起又落下 。 除了夹菜时会面向餐桌 , 其余时间他都侧着身子 , 面向着饭桌和电视之间的空隙 。开饭时 , 坐在沙发正中的是婶婶 , 她身边坐着的堂姐 。 堂姐肤色暗 , 烫过的头发没怎么打理 , 杂乱地向各个方向卷曲 , 栗红色的头发配着深色的毛衣 , 这搭配和壮硕的身材 , 让她的气质显得有些彪悍 , 更像是这个家里的男主人 。婶婶伸手摸了摸脚边的泰迪 , 问我:“你抽烟吗?”“不抽 。 ”“喝酒呢?”“也不喝 。 ”“哦?你爸他可是抽烟喝酒的 , 你一点儿都不会?”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提及我父亲 , 不自觉地紧绷了身体 , 然后抬起头看着她 。 而此时大伯仍然保持刚才的姿态 , 他的身体转到一个奇怪的角度 , 既看不到饭菜也看不到电视 。我放下手里的筷子:“现在年轻人不沾烟酒很正常的 。 ”她微微点头 , 筷子拨了拨碗里的米饭 , 稍作停顿 , 然后又说道:“现在还放在那儿呢?”她说完话便将饭菜拨进了嘴里 , 不断咀嚼着 。她说的是父亲的骨灰 , 仍然没有下葬 , 存放在公墓的安灵苑:“早点埋了吧 , 入土为安 。 ”我暗暗吸了口气 , 没有回话 。 姑姑坐在一个较高的蓝色塑料凳子上 , 类风湿让她的膝盖和髋部都不能轻松地弯折 , 每次吃饭 , 她都要坐在一个高点的地方 。“嫂子 , 你家这个挂饰挺好看的呀 , 哪里买的?”姑姑的语气有些讨好的意味 , 她吃力地回过身 , 指着墙上的一副颜色鲜红的编花 。“以前家里还有一个紫色的 , 但是后来都找不着了 。 ”婶婶没有回答姑姑的问题 , 自顾自地说 , “毛巾也是 , 买回来好几条 , 过阵子就只剩一条了 。 ”她说话时眼睛没看姑姑 , 而是有意无意地瞟着大伯 。 姑姑回过身 , 没有接话 , 而大伯一如既往地沉默 。饭局上的对话到了这一步 , 我大概可以理解婶婶了 。 我隐约知道父亲和她关系并不好 , 姑姑又需要大伯不断地接济照顾 , 而我这个晚辈之前也从没主动联系过她 。 从她的视角来看 , 这不仅是一次家庭聚会 , 还是一次发泄的机会 。我忽然觉得自己有些自讨没趣 , 不自然地转了转脖子 , 余光看到了茶几边上鲜红的礼盒和电视里的枪战片 , 身边的姑姑用手撑着凳子 , 吃力地转动身体 , 试图让自己舒服些 , 而一直沉默的大伯起身夹起一块鱼 , 放进我的碗里:“别光说话 , 多吃点 。 ”饭局很快结束 , 大伯与我们一起离开 , 到了地铁站 , 他回想起刚才的场景 , 激动地说道:“那毛巾我根本就没有动 , 她们自己找不到了 。 ”“那人家就是觉得被你拿给我了 , 你有什么办法?”姑姑语气怪异的附和着 。兄妹俩一唱一和地表达着内心的不满 , 大伯背着手昂起头 , 讲话时眉飞色舞 , 变得无比健谈 , 姑姑也不见了刚才的拘谨 , 我跟在他们身后走上了扶梯 , 双眼不聚焦地看着前方 , 扶梯开始加速运行 , 于是他们的身影在我的视野中渐渐下降 。82018年 , 东三环又开始了拆迁 , 外婆居住的小产权房在拆迁范围之外 , 但附近刚刚热闹起来的街区 , 又被淹没在挖掘机掀起的尘土中 。 暑假回家时 , 看着街道边上一堵堵白色围墙和墙后堆积残砖破瓦 , 拎着行李的我几乎又一次迷失了 。这年9月 , 我继续留校读研 , 也是在那段时间 , 姑姑从铁路小区搬到了大伯单位分配的房子里 。 这房子位置好 , 附近也热闹 , 可惜是在六楼 。 她一直想让大伯把这间房租出去 , 然后换一间低一点的房子 , 但一直没能如愿 。 就在姑姑搬过来半年后 , 我们就听说这边的房子也可能面临拆迁 , 不过这次似乎只是传闻 。这一年 , 政策发生了变化 , 姑姑所在社区的医保终于将类风湿性关节炎列入可报销项目中 , 比例是50% 。 但姑姑并不开心 , 因为她这时查出心脏二尖瓣闭合不全 , 日常的开销中 , 又多了心脏病的药物费用 。类风湿和心脏病都属于慢性病 , 姑姑本以为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 但工作人员告诉她 , 一个人只能申报一种慢性病的报销 , 也就是说 , 要么报销类风湿的费用 , 要么报销心脏病的费用 , “政策就是这样儿的” 。相比于从前 , 姑姑的生活好转了不少——相对舒适的生活环境和上涨的退休金给了她些许信心 。 只是她的病情依然在加重 , 关节畸变对坐卧姿态的影响 , 让她的腰椎间盘突出已经有了滑脱的可能性 。 医生建议她做手术 , 但她拒绝了 。 在医院的大厅 , 她告诉我:“这个手术 , 我做了有可能就动不了了 , 到那时怎么办呢?”我站在她身后 , 本想说些什么 , 但最终只是张了张嘴 , 像是一条搁浅的鱼 , 挣扎着呼吸一口空气 。是啊 , 如果她真的动不了 , 我有能力面对接下来的事情吗?搬到新家后 , 姑姑常常会做一些我不能理解的行为——比如她时常会拖着行动不便的身体 , 花很久的时间 , 转战数个商场 , 只为参加可以免费领取礼品的活动 。“反正我也没事 。 ”她总是这样解释 。她几乎每天都群发一些商场的海报和文案 , 海报的样式千篇一律 , 大红色打底配上烫金色的字体 , 没有丝毫美感 。 点开她的朋友圈 , 一滑到底几乎都是某某商场有活动的信息 。 商场会利用这些拥有时间却无事可做的妇女们 , 让她们把这些信息转发给一定数量的人 , 然后在指定时间到商场 , 便可以获得报酬——保温杯或者是牙刷 。后来每次去姑姑家 , 她都询问我需不需要保温杯 , “我已经领了十几个杯子啦 , 全在这里面放着” 。 她说着便拍拍家里那个暗黄的矮柜 , 类风湿让她没有办法轻松地弯下腰 , 不然她一定会拿出来给我看看 。“姑 , 我有保温杯了 。 ”“没事 , 家里放一个 , 教室放一个 。 ”她会板着手指 , 细数我可以拥有几个杯子 , 一般这个时候大伯会插一嘴:“多拿几个 , 坏了就换一个 。 ”我已经记不清这样的对话发生过多少次 , 我也不清楚她是否意识到自己在不断地重复一些对话 。 她很喜欢提及小时候的我 , 讲述四五岁的我在那片已变成废墟的棚户区里蹦蹦跳跳的情景 , 为了要玩具睡在谁家门口 , “跟其他生活在福村的小孩不一样 , 从来不说脏话” 。她仿佛忘记了时间在向前流动 , 还沉缓地停滞在早已泛黄的昨日 。 对啊 , 她的生活中已经太久没有填充进新的东西 , 于是她只得不断地重复 。她一定无比怀念20年前的日子吧 , 在那片棚户区里 , 早晨推开门便能看到邻里的炊烟和越过槐树落在门前的阳光 , 幼年的我在她眼皮底下玩闹 。 到了夜晚 , 枕着野猫踩过瓦片发出的轻微声响进入梦乡 , 关节的疼痛还不像现在这般让她难以入眠 。9读研之后 , 我回家的时间变得更少 , 时间的流动仿佛变快了 , 转眼便到了2020年 。全市范围内的棚改仍然在进行 , 一个个棚户区的名字出现在了公示的拆迁规划之内 , 原本聚集在这些区域的人们又要奔向下一个容身之所 。他们同姑姑一样 , 低下的经济水平迫使他们一遍遍筛选着城市里的住所 , 于是他们总是居住在被城市视为“污点”的棚户区、城中村或是被锁在断头路里的老旧小区 。 随着城市变得更加精致 , 他们却如同风中的砂砾一般四处飘荡 。疫情的影响逐渐褪去 , 东二环的安泰造林工程又开始日夜尘土飞扬 , 这个从2016年就开始的项目 , 据说是当年苏联专家最初提出设想 , 将要在明年底完工 。 看着宣传视频里面充满科技的渲染效果 , 和“三带三轴三中心”、“全国最大综合体”等无比诱人的宣传词 , 我也想象着漫步在其中的滋味 。外婆那个小产权房附近的工地还在叮叮当当 , 飞扬的灰尘让我的鼻炎常常复发 , 但宽敞的大路终于通到了东三环外 。 每个夜晚 , 附近新开的凯德茂商场门前满是跳广场舞的人 , 有些烤肉店还会请来驻唱歌手 , 光影声色 , 样样不缺 。铁路小区早已拆掉 , 那里原本狭窄破旧的道路现在变成了宽敞整洁的八车道 , 道路的尽头 , 一条地下隧道正在修建 , 通过它 , 往来的车辆可以直接绕过那条多年前阻拦我上学的铁轨 。但对姑姑来说 , 2020年最有价值的消息 , 是听说福村原本停滞的拆迁安置工作又有了新进展 。 自从2012年开始拆迁以来 , 福村的居民陆续搬了出去 , 有人早已谈妥 , 也有很多像姑姑一样的人 , 没有能量去推动这场“谈判” , 只能等待 , 然后期待赔偿的政策能够变得优渥 。去年年底 , 听说有了新的开发商来接手 , 姑姑都觉得拆迁的进程会加快 , 他们或许会成为吃到“锅底肉”的人 。 最近这些年 , 她的身体状况逐渐变差 , 免疫系统的紊乱带来各种病变 , 有时与她通话 , 电话那头的声音 , 虚弱得像是无法呼吸 。 我察觉到某些悲伤的事情就潜伏在不远的将来 , 也知道自己没力气阻止这一切发生 。“等疫情过去 , 我们几个准备再去拆迁办闹一次 , 这次一定要把事情定下来 , 至少得给我弄到一个能住的地方 。 ”她倚着沙发 , 将无法伸直的腿搭载在小板凳上 , 信誓旦旦地对我说道 。我低着头 , 挠了挠头发 , 没有说话 。 在她面前 , 我觉得自己的话语失去了力量 , 说得越多 , 便越觉得无力 。于是我也开始期待 , 期待政策能让她同时报销两种慢性病的费用 , 期待来年的我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 , 期待那些悲伤晚一点或者永远不要到来 。(文章人名皆为化名)征稿无论主动还是被动 , 城市正成为我们最为主要的生活空间 。与乡土生活的静止和重复不同 , 城市生活充满了惊奇和变化 , 它满足我们关于幸福生活的欲望、野心和理想;也隐伏着孤独、残酷等各类心理和精神危机 。 一代又一代的人 , 被城市所塑造着 , 也塑造着城市 , 审视着生活 , 也被生活审视 。正如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写下:“在路过而不进城的人眼里 , 城市是一种模样;在困守于城里而不出来的人眼里 , 她又是另一种模样;人们初次抵达时 , 城市是一种模样 , 而永远离别时 , 她又是另一种模样 。 ”我们每个人 , 都因不同的时代与个人遭际 , 在心底建构出城市的万般模样 。2020是个被迫禁足的年份 。 无论我们人在何处 , 是淡定、是烦躁 , 是一筹莫展、是心有余悸 , 都是一个适合的机会 , 让很多人重新审视自己与“一座城市”的关系 。这个夏天 , 人间编辑部大型征文再一次开启——「人间· 人在城中Living in City」 。我们期待你 , 记录下你与自己现在或曾经所处城市的故事 , 记录下它对我们每一个人所提出的 , 关于梦想、爱与希望问题的答复 , 记录下所有你在此处念念不忘的人与事 , 记录下它只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模样 。编辑:唐糖题图:《纺织城》剧照
推荐阅读
- 大同随想,城市的面貌该由谁来决定?
- 玉林|起飞!玉林福绵机场今日正式通航,通达7个城市
- 蔡莉不就是说话直率不够老奸巨滑
- 城市百角|拥有800多万人口的徐州,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上,一定会赶超常州
- 高铁|山东“最牛”的城市,火车直达223个城市,市内有四个铁路客运站
- 涿州|赋能前行!涿州加大务实创新举措,为城市建设擦亮了新“底色”……
- 涵涵大世界|中国第一个拥有公交车的城市,不是北上广,而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他
- 潇湘晨报|共建共治共享|花溪区提升改造园亭路小记:用“绣花功夫”扮靓城市“里子”
- 城市内涝|城市内涝,坠井事故频发生,如何通过物联网手段避免事故发生?
- 退休选一线城市还是老家,哪个退休金能拿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