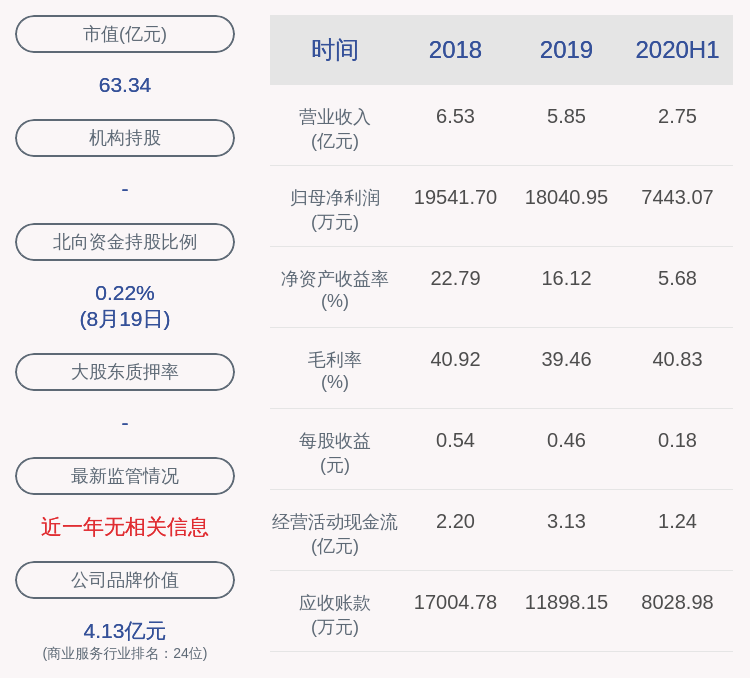йғЁйҳҹ|и®°иҖ…жүӢи®° | жҲ‘еҺ»жқЁж №жҖқйғЁйҳҹжӢҚдәҶдёҖжңҹвҖңеҸҳеҪўи®ЎвҖқ

ж–Үз« еӣҫзүҮ
еҮәеҸ‘еҺ»вҖңжқЁж №жҖқиҝһвҖқжӢҚж‘„д№ӢеүҚпјҢе·Із»ҸжңүдёӨдёүз»„зҡ„йҮҮи®ҝжҺҘиҝ‘дәҶе°ҫеЈ°гҖӮ他们жңүзҡ„жҳҜеңЁйӣӘеҹҹй«ҳеҺҹпјҢжңүзҡ„жҳҜеңЁзғӯеёҰдёӣжһ—пјҢзҺҜеўғжһҒиҮҙпјҢз”»йқўе”ҜзҫҺпјҢжӢҚзҡ„жҜҸдёҖеё§йғҪжҳҜеӨ§зүҮе„ҝгҖӮжүҖд»ҘеҪ“ж—¶жҲ‘д№ҹдёҖеүҜи·ғи·ғж¬ІиҜ•зҡ„ж ·еӯҗпјҢд№ҹжғіжҠҳи…ҫеҮәзғӯиЎҖжІёи…ҫзҡ„зҡ„еӨ§еңәйқўгҖӮ
иҝҷдёӘжғіжі•еңЁжҲ‘еҲ°дәҶйғЁйҳҹд№ӢеҗҺпјҢеҹәжң¬дёҠе°ұж”ҫејғдәҶгҖӮеӣ дёә他们зҡ„й©»и®ӯең°еҸӘжҳҜдёҖеқ—е№іе№іж— еҘҮзҡ„иҚүең°пјҢеӣӣе‘ЁйғҪжҳҜж°‘жҲҝпјҢи®ӯз»ғдёҖз»“жқҹпјҢжҲҗзҫӨзҡ„зүӣзҫҠдҫҝжҷғжӮ жӮ ең°иҝҮжқҘеҗғиҚүдәҶгҖӮ
еҲқеҲ°йғЁйҳҹзҡ„еүҚдёӨеӨ©пјҢжҲ‘зҡ„дё»иҰҒе·ҘдҪңе°ұжҳҜиҒҠеӨ©пјҢжүҫдёҚеҗҢзҡ„е…өе“Ҙе“ҘиҒҠпјҢдёҖиҢ¬еҸҲдёҖиҢ¬пјҢеқҗеңЁд»–们и®ӯз»ғеңәзҡ„еӨ§ж ‘еә•дёӢгҖӮ他们е’ҢжҲ‘иҒҠеӨ©ж—¶пјҢйқһеёёжңүзӨјиІҢпјҢеҫҲи°ҰиҷҡпјҢзӣҙеҲ°дёҖдёӘеҸ«жһ—жҖқзҗҰзҡ„е№ҙиҪ»жҲҳеЈ«еңЁжҲ‘йқўеүҚеқҗдёӢжқҘгҖӮжүҚиҜҙеҮ еҸҘиҜқпјҢжҲ‘е°ұжңүдёҖдёӘж„ҹеҸ—пјҢйӮЈе°ұжҳҜвҖңж”»еҮ»жҖ§вҖқгҖӮ
жңүж”»еҮ»жҖ§пјҢеңЁеҪ“дёӢйӮЈдёҖеҲ»пјҢжҳҜиӨ’д№үиҜҚгҖӮ
жһ—жҖқзҗҰ23еІҒпјҢж№–еҚ—еёёеҫ·дәәпјҢжҳҜ家дёӯзӢ¬еӯҗпјҢд»Һе°ҸйЎҪзҡ®еҸӣйҖҶпјҢ12еІҒж—¶пјҢиў«зҲ¶жҜҚйҖҒеҺ»е°‘жһ—жӯҰж ЎпјҢз»“жһңдёӨе№ҙеӯҰжӯҰвҖңж”№йҖ вҖқдёӢжқҘпјҢдҫқ然жҳҜзҲ¶жҜҚзңјдёӯзҡ„вҖңжө‘е°ҸеӯҗвҖқгҖӮжңҖеҗҺпјҢеҸӘеҘҪе°Ҷд»–йҖҒиҝӣдәҶеҶӣиҗҘгҖӮеҪ“е…ө第дёүе№ҙпјҢжһ—жҖқзҗҰеҺ»дәҶеҚ—иӢҸдё№еҪ“з»ҙе’ҢжҲҳеЈ«пјҢ2016е№ҙвҖң7В·8вҖқдәӨзҒ«дәӢ件еҗҺпјҢд»–дёҺжҲҳеҸӢз»„жҲҗвҖңе…«дәәж•ўжӯ»йҳҹвҖқпјҢеңЁиҒ”еҗҲеӣҪиҗҘеҢәеӨ§й—ЁеҸЈдёҺжӯҰиЈ…еҲҶеӯҗеҜ№еіҷдәҶ13дёӘе°Ҹж—¶гҖӮзҺ°еңЁд»–жҳҜвҖңжқЁж №жҖқиҝһвҖқдёҖзҸӯе°–еҲҖзҸӯзҡ„зҸӯй•ҝгҖӮеүҜж•ҷеҜје‘ҳеңЁдёҖж—Ғи°ғдҫғпјҢжһ—жҖқзҗҰе°ұжҳҜжқҘеҶӣиҗҘвҖңеҸҳеҪўвҖқзҡ„гҖӮ
жһ—жҖқзҗҰй•ҝдәҶдёҖеј еңҶи„ёпјҢиҷҺеӨҙиҷҺи„‘зҡ„пјҢжҖ§ж јд№ҹйқһеёёиҷҺгҖӮе’ҢжҲ‘иҒҠеӨ©ж—¶пјҢжҲ‘иғҪж„ҹи§үеҲ°д»–жңүж„ҸеңЁз»ҙжҢҒе®ўж°”пјҢдҪҶжҳҜдёҚз»Ҹж„Ҹй—ҙд»–д»Қ然жөҒйңІеҮәдәҶд»–зҡ„вҖңж”»еҮ»жҖ§вҖқвҖ”вҖ”йқһеёёиҮӘдҝЎпјҢз”ҡиҮіжңүдәӣзӢӮеҰ„пјҢеҜ№еӘ’дҪ“зҡ„йҮҮи®ҝд№ҹдёҚжҳҜеҫҲеңЁд№Һзҡ„ж ·еӯҗпјҢдёҖиҒҠе®ҢеӨ©пјҢд»–е°ұз«Ӣ马иө·иә«жҲҙеҘҪеӨҙзӣ”еҺ»и®ӯз»ғдәҶпјҢе®Ңе…ЁжІЎжңүз»ҷжҲ‘дёҖдёӘ笑脸гҖӮ
жҲ‘еҝғйҮҢжғіпјҢе°ұжҳҜд»–дәҶгҖӮ
ж–Үз« еӣҫзүҮ
第дёҖж¬Ўе’Ңжһ—жҖқзҗҰи§Ғйқў
既然没жңүжһҒиҮҙзҡ„зҺҜеўғз»ҷжҲ‘жӢҚпјҢйӮЈе°ұжӢҚеҘҪиҝҷдёӘдәәеҗ§гҖӮ
еңЁжҲ‘зҡ„зҗҶи§ЈйҮҢпјҢжӢҚеҘҪдёҖдёӘдәәпјҢе°ұжҳҜе°Ҷд»–зңҹе®һең°еңЁй•ңеӨҙйҮҢе‘ҲзҺ°еҮәжқҘпјҢдёҚзІүйҘ°пјҢдёҚйҡҗеҢҝпјҢи®©д»–иҝҷдёӘдәәзңӢиө·жқҘйҘұж»ЎиҖҢжңүиҙЁж„ҹгҖӮ
дёәдәҶзңҹжӯЈдәҶи§Јжһ—жҖқзҗҰпјҢжҲ‘жІЎжңүзқҖжҖҘеҺ»еҒҡд»–зҡ„дёӘдәәйҮҮи®ҝпјҢиҷҪ然йӮЈж ·еӯҗиғҪе°Ҷд»–зҡ„дәәз”ҹеҘҪеҘҪжҚӢдёҖйҒҚгҖӮжҲ‘и§үеҫ—иҰҒе…Ҳи·ҹд»–жҲҗдёәжңӢеҸӢпјҢд»–еңЁжҲ‘йқўеүҚе°ұжүҚжҳҜзңҹе®һзҡ„гҖӮ
жңҖејҖе§Ӣзҡ„еҮ еӨ©пјҢ他们е®һеј№е°„еҮ»зҡ„и®ӯз»ғд»»еҠЎеҫҲйҮҚпјҢеҮҢжҷЁ4зӮ№е°ұиө·еәҠпјҢжү“еҲ°жҷҡдёҠеҚҒзӮ№жүҚеӣһиҗҘгҖӮйўҶеҜјдҫҝе®үжҺ’д»–жҜҸеӨ©жҠҪеҮәеҚҠеӨ©е·ҰеҸізҡ„ж—¶й—ҙз»ҷжҲ‘жӢҚж‘„гҖӮд»–жҜҸеӨ©дёҖзңӢеҲ°жҲ‘пјҢ第дёҖеҸҘиҜқж°ёиҝңйғҪжҳҜвҖңйӮ“иҖҒеёҲпјҢд»ҠеӨ©жӢҚд»Җд№ҲвҖқпјҢеҘҪеғҸд»–жүҚжҳҜеҜјжј”дёҖж ·пјҢзӣ®ж ҮжҳҺзЎ®гҖӮ
еңЁжӢҚж‘„дёӯпјҢд»–йқһеёёй…ҚеҗҲпјҢжҲ‘иҰҒд»Җд№ҲдёңиҘҝпјҢд»–з«Ӣ马е°ұиғҪйўҶжӮҹеҲ°пјҢ然еҗҺе°ҶжҲ‘зҡ„жғіжі•е®һзҺ°еҮәжқҘгҖӮдҪҶжҳҜжҲ‘жҖ»и§үеҫ—д»–жғ…з»ӘдёҚдҪіпјҢд»Қ然жҳҜжҠұзқҖдёҖз§Қе®ҢжҲҗдёҠзә§дәӨдәҲзҡ„д»»еҠЎзҡ„еҝғжҖҒеңЁжӢҚж‘„гҖӮеҗҺжқҘи¶ҒзқҖдј‘жҒҜзҡ„й—ҙйҡҷпјҢжҲ‘й—®д»–еҝғйҮҢжҳҜдёҚжҳҜжңүд»Җд№ҲдәӢжғ…пјҢе®Ңе…ЁеҸҜд»ҘиҜҙеҮәжқҘгҖӮ
з»“жһңжһ—жҖқзҗҰйқһеёёзҲҪеҝ«ең°дәӨдәҶеә•пјҡ第дёҖпјҢйӮЈеӨ©еӨ§ж ‘еә•дёӢи§ҒйқўпјҢжҳҜд»–еӨұжҒӢзҡ„第дёүеӨ©пјӣ第дәҢпјҢд»–жң¬жқҘжҳҜиҰҒдј‘е№ҙеҒҮеӣһж№–еҚ—зҡ„пјҢз»“жһңеӣ дёәжҲ‘们зҡ„йҮҮи®ҝпјҢд»–зҡ„е№ҙеҒҮеҫҲеҸҜиғҪиҰҒжіЎжұӨдәҶгҖӮ
жҲ‘жӢҚдәҶжӢҚд»–зҡ„иӮ©пјҢзңјзҘһжҖңжӮҜпјҢиҜӯйҮҚеҝғй•ҝең°еҜ№д»–иҜҙпјҡжҲ‘们иҰҒеңЁиҝҷйҮҢеҫ…дёҠеҚҠдёӘжңҲпјҢжҳҜдёҚеҸҜиғҪи®©дҪ еӣһеҺ»дј‘еҒҮзҡ„пјҢдҪ е°ұжӯ»дәҶиҝҷжқЎеҝғеҗ§гҖӮ
д»ҺйӮЈд»ҘеҗҺпјҢжҲ‘们дҝ©е°ұжӯЈејҸжҲҗдёәжңӢеҸӢдәҶгҖӮ
жҲҗдёәжңӢеҸӢд»ҘеҗҺпјҢдёҖеҲҮйғҪеҸҳеҫ—жңүи¶ЈдәҶгҖӮд»–дјҡеңЁйҮҮи®ҝдёӯпјҢзү№еҲ«еҫ—з‘ҹең°д»Ӣз»Қ他们еҸ–еҗҚдёәвҖңеӨ©дёӢ第дёҖвҖқзҡ„жҲҳиҪҰпјҢдјҡж—¶дёҚж—¶ең°жөҒйңІеҮәиҮӘе·ұжңүеӨҡд№ҲеҺүе®іпјҢд№ҹдјҡеғҸе№іеёёдёҖж ·ж•ҷи®ӯзҸӯдёҠйӮЈдәӣжҲҳеЈ«гҖӮе®Ңе…ЁдёҚдјҡеӣ дёәжңүй•ңеӨҙеңЁпјҢе°ұеҲ»ж„Ҹж‘ҶеҮәи°ҰйҖҠзҡ„ж ·еӯҗгҖӮе°Өе…¶жҳҜеңЁдёҺзҲ¶жҜҚи§Ҷйў‘йҖҡиҜқд№ӢеҗҺпјҢд»–дјҡж•һејҖеҝғжүүең°иЎЁиҫҫеҮәиҮӘе·ұеҶ…еҝғзҡ„иӢҰй—·вҖ”вҖ”еңЁзҲ¶жҜҚзңјйҮҢпјҢд»–еҘҪеғҸж°ёиҝңжҳҜдёӘдёҚиғҪеҲҶжӢ…家еәӯеҺӢеҠӣзҡ„еӯ©еӯҗгҖӮиҝҷдёҺд»–жғіжҲҗй•ҝдёәдёҖдёӘйЎ¶еӨ©з«Ӣең°зҡ„з”·дәәзҡ„ж„ҝжңӣпјҢжҳҜзӣёиҝқиғҢзҡ„гҖӮ
жҲ‘еҚ°иұЎжңҖж·ұеҲ»зҡ„пјҢжҳҜе’Ңд»–иҒҠз»ҙе’Ңж—¶зҡ„йӮЈж®өз»ҸеҺҶпјҢйӮЈжҳҜ他第дёҖж¬ЎзӣҙйқўзңҹжӯЈзҡ„жҲҳдәүпјҢ第дёҖж¬ЎзӣҙйқўжөҒиЎҖе’Ңжӯ»дәЎгҖӮеҪ“жҲҳеҸӢжқЁж ‘жңӢе’ҢжқҺзЈҠзүәзүІеҗҺпјҢд»–дё»еҠЁз”іиҜ·еҠ е…ҘвҖңе…«дәәж•ўжӯ»йҳҹвҖқгҖӮиҝһй•ҝжҳҺзЎ®иЎЁзӨәпјҢзӢ¬з”ҹеӯҗдёҚиғҪеҺ»пјҢеҸҜжһ—жҖқзҗҰиҝҳжҳҜдёҫиө·дәҶжүӢгҖӮеҮәеҸ‘жү§иЎҢд»»еҠЎд№ӢеүҚпјҢд»–з»ҷзҲ¶жҜҚеҶҷдәҶдёҖе°ҒиҜҖеҲ«дҝЎпјҢдәӨд»ЈдәҶиҮӘе·ұзҡ„银иЎҢеҚЎеҜҶз ҒпјҢиҝҳеңЁдҝЎзҡ„жңҖеҗҺдёҖеҸҘеҶҷйҒ“пјҢзҘ–еӣҪдёҚдјҡеҝҳи®°еҝ иҜҡдәҺзҘ–еӣҪзҡ„дәәгҖӮйӮЈдёҖе№ҙпјҢд»–19еІҒпјҢ已然еҒҡеҘҪдәҶд»Һе®№иөҙжӯ»зҡ„еҮҶеӨҮгҖӮжүҖи°“зғӯиЎҖз”·е„ҝпјҢ家еӣҪеӨ©дёӢпјҢдёҚе°ұжҳҜд»–зҡ„еҶҷз…§еҗ—пјҹ
иҮӘжӯӨпјҢд»–еңЁжҲ‘йқўеүҚжүҖеұ•зҺ°еҮәжқҘзҡ„пјҢе°ұжҳҜдёҖдёӘжңүиЎҖжңүиӮүзҡ„дәәпјҢдёҖдёӘжңүжҲҗй•ҝеҸҳеҢ–зҡ„дәәгҖӮз”Ёд»–иҮӘе·ұзҡ„иҜқиҜҙпјҢд»–еңЁеҶӣиҗҘвҖңеҸҳеҪўвҖқжҲҗеҠҹдәҶгҖӮжҲ‘жӢҚзҡ„иҝҷжңҹиҠӮзӣ®пјҢе°ұжҳҜд»–зҡ„еҶӣиҗҘвҖңеҸҳеҪўи®ЎвҖқгҖӮ
и§ЈеҶідәҶвҖңдәәвҖқзҡ„й—®йўҳд№ӢеҗҺпјҢж–°зҡ„йҡҫйўҳеҸҲжқҘдәҶпјҢйӮЈе°ұжҳҜж•…дәӢдё»зәҝгҖӮ
既然иҠӮзӣ®еҗҚеҸ«гҖҠжҲҳж——зҫҺеҰӮз”»гҖӢпјҢйӮЈд№ҲвҖңжҲҳж——вҖқиӮҜе®ҡжҳҜж ёеҝғзҡ„йҒ“е…·гҖӮжӢҚж‘„еҮ еӨ©д№ӢеҗҺпјҢжҲ‘еҸ‘зҺ°пјҢвҖңжқЁж №жҖқиҝһвҖқж—ўжІЎжңүжһҒз«ҜзҺҜеўғпјҢд№ҹжІЎжңүйҮҚеӨ§д»»еҠЎпјҢжҜҸеӨ©йғҪжҳҜеңЁй©»и®ӯең°иҝӣиЎҢж—Ҙеёёи®ӯз»ғгҖӮжүҖд»Ҙзјәе°‘дёҖжқЎеҗҲзҗҶзҡ„ж•…дәӢдё»зәҝпјҢе°Ҷжһ—жҖқзҗҰе’ҢжҲҳж——иһҚеҗҲиө·жқҘгҖӮеҪ“ж—¶йқһеёёж„ҒпјҢе№ёеҘҪжҲ‘们иҠӮзӣ®з»„дјҡз»ҸеёёеңЁжүӢжңәдёҠејҖи§Ҷйў‘зӯ–еҲ’дјҡпјҢжңҖеҗҺеӨ§е®¶дҫҝе•ҶйҮҸеҮәдәҶдёҖдёӘвҖңеӨәжҲҳж——вҖқзҡ„еҲӣж„ҸпјҢи®©еҺҹжң¬йқҷжҖҒзҡ„гҖҒзҗҗзўҺзҡ„гҖҒж— е…іиҒ”зҡ„дёңиҘҝеҫ—д»ҘдёІиҒ”иө·жқҘгҖӮ
жҲ‘马дёҠе’Ңиҝһй•ҝи®Ёи®әдәҶиҝҷдёӘеҲӣж„ҸпјҢиҝһй•ҝд№ҹйқһеёёиөһеҗҢгҖӮеӣ дёәвҖңжқЁж №жҖқиҝһвҖқиҝҷйқўжҲҳж——жҳҜеңЁжҠ—зҫҺжҸҙжңқзҡ„зӮ®зҒ«дёӯжҺҲдәҲзҡ„пјҢд»Ҡе№ҙжҒ°йҖўеҸҲжҳҜдёӯеӣҪдәәж°‘еҝ—ж„ҝеҶӣжҠ—зҫҺжҸҙжңқеҮәеӣҪдҪңжҲҳ70е‘Ёе№ҙпјҢеңЁиҝҷдёӘж—¶й—ҙиҠӮзӮ№дәүеӨәжҲҳж——пјҢдёҚд»…еҸҜд»ҘжҝҖеҸ‘ж–—еҝ—пјҢжӣҙжҳҜдёҖж¬Ўе…·жңүйҮҚеӨ§ж„Ҹд№үзҡ„жҖқжғіж•ҷиӮІжҙ»еҠЁгҖӮ
зЎ®е®ҡдәҶж•…дәӢдё»зәҝпјҢжҲ‘们зҡ„жӢҚж‘„д№ҹеҸҳеҫ—жё…жҷ°иө·жқҘгҖӮжҲҳеүҚеҠЁе‘ҳгҖҒжҲҳеүҚи®ӯз»ғгҖҒдәүеӨәжҲҳж——зҡ„зәўи“қеҜ№жҠ—д»ҘеҸҠжңҖеҗҺзҡ„жҺҲж——д»ӘејҸпјҢж•ҙдёӘж•…дәӢеҹәжң¬дёҠе°ұеҲҶжҲҗдәҶиҝҷеӣӣеӨ§жқҝеқ—гҖӮеҸҜжҳҜеҜ№дәҺдёҖдёӘеҘійҮҮи®ҝдәәе‘ҳиҖҢиЁҖпјҢжңҖйҡҫжӢҚж‘„зҡ„е°ұжҳҜжҲҳдәүжҲҸпјҢиҖҢзәўи“қеҜ№жҠ—е°ұжҳҜеӨәжҲҳж——зҡ„й«ҳжҪ®пјҢд№ҹжҳҜеңәйқўжңҖеӨ§зҡ„жҲҳдәүжҲҸгҖӮ
жҺЁиҚҗйҳ…иҜ»
- еӣҪж°‘и®°иҖ…|гҖҠиҖҒд№қй—ЁгҖӢеҪұзүҲжқҘиўӯпјҢжүҖйҖүжј”е‘ҳе…ЁжҚўж–°пјҢдёҚзҹҘиғҪеҗҰи¶…и¶ҠйҷҲдјҹйңҶеј иүәе…ҙ
- и§Јж”ҫеҶӣй©»жҫій—ЁйғЁйҳҹ第дәҢеҚҒдёҖж¬Ўе»әеҲ¶еҚ•дҪҚиҪ®жҚўе·ҘдҪңйЎәеҲ©е®ҢжҲҗ
- и®°иҖ…жҡ—и®ҝпјҡй•ҝжІҷвҖңеҗҚеҢ»вҖқзңӢз—…иҰҒе…ҲзӯҫвҖңз”ҹжӯ»зҠ¶вҖқпјҢеҘіеӯҗжңҚиҚҜдёүжңҲеҗҺиә«дәЎпјҢз§°пјҡеҘ№еҲ®з—§жү“д№ұдәҶжІ»з–—и®ЎеҲ’
- еӣҪж°‘и®°иҖ…|з”·еӨҙ| еј еӣҪиҚЈ
- йҮҚзӮ№иҖғиҷ‘ж–°еҶ иӮәзӮҺжІ»з–—иҚҜзү©гҖҒйҮҠж”ҫйј“еҠұеҲӣж–°дҝЎеҸ·вҖ”вҖ”еӣҪ家еҢ»дҝқеұҖзӣёе…іиҙҹиҙЈдәәе°ұ2020е№ҙеҢ»дҝқзӣ®еҪ•и°ғж•ҙзӯ”и®°иҖ…й—®
- е•ҶдёҡеҒҘеә·дҝқйҷ©|йҮҚзӮ№иҖғиҷ‘ж–°еҶ иӮәзӮҺжІ»з–—иҚҜзү©гҖҒйҮҠж”ҫйј“еҠұеҲӣж–°дҝЎеҸ·вҖ”вҖ”еӣҪ家еҢ»дҝқеұҖзӣёе…іиҙҹиҙЈдәәе°ұ2020е№ҙеҢ»дҝқзӣ®еҪ•и°ғж•ҙзӯ”и®°иҖ…й—®
- е®үйҳі|е®үйҳіпјҡж—…жёёжңүзңӢеӨҙ жёёе®ўиғҪеӣһеӨҙ
- ж·„еҚҡ|й«ҳиҙЁйҮҸеҸ‘еұ•зңӢж·„еҚҡд№Ӣи®°иҖ…жүӢи®°дёЁеӣӣеӨ© и®ӨиҜҶдёҖдёӘдёҚдёҖж ·зҡ„ж·„еҚҡ
- йӣҶиҒҡеҢә|иЎҢиө°иҮӘиҙёеҢәпҪңйӣҶиҒҡеҸ‘еұ•еҠЁиғҪжү“йҖ ејҖж”ҫж–°й«ҳең° еӨ®еӘ’и®°иҖ…иөһдёүдәҡжңӘжқҘеҸҜжңҹ
- гҖҗиЎҢиө°иҮӘиҙёеҢәгҖ‘йӣҶиҒҡеҸ‘еұ•еҠЁиғҪжү“йҖ ејҖж”ҫж–°й«ҳең° еӨ®еӘ’и®°иҖ…иөһдёүдәҡжңӘжқҘеҸҜжң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