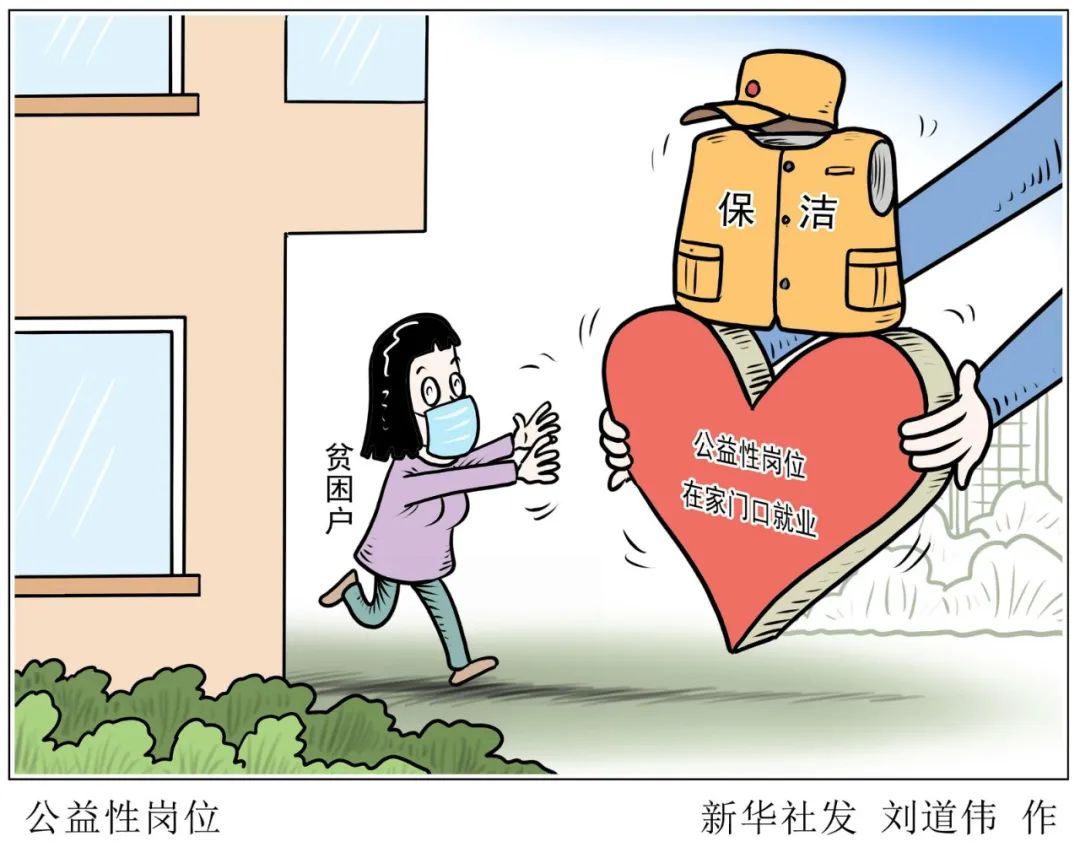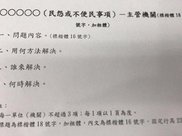有啥让你一见就被深深吸引的美文( 三 )
那时候,你的面目早已因潜伏的病灶难靖,稍稍地倾斜着,反正已经割过了而且是个慢性子的瘤,就不必管吧,只在你心力用瘁的时候,才憔悴起来,我叫你当心,你复来的信不痛不痒地说:“今早文心课见你挽抱书本飘然而去,霎时间萌生一种远飏的感觉,没来得及跟你说。有回上声韵,下了课,正见你倦极而伏案,其时感觉也是一惊。记得有次夜深,与你不期然遇,你说从总图出来,回宿舍去。夜色下的你步履决定,却透着层弱倦后的苍白。一直没能多问候你,反而是你看出我的憔悴。”你始终不愿意称我“简媜”,说这二字太坚奇铿锵,带了点刀兵,你宁愿正正经经地写下“敏媜”,说有了这“敏”字,行云流水起来,不遭忌的。我深深动容,你一片片莲灿,都为我惜生,而我能为你做什么?性格里横槊赋诗的草莽气质,总让我对最亲近的人杀伐征讨。难得有一回清清淡淡的小聚,临别时,我不经心窜出那头兽、那忘情负义恩将仇报的猛禽:“保重哟,下一次见面或许九天,或九年。”你清和的面容浮掠一丝秋瑟,宽怀地笑纳这些语锋契机,你报平安的信通常这么作结:“写信、说话,欢喜日复一日。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小谈。我担心一语成谶。”
尔后,我离了学院,日复日载饥载渴,过的是牛饮而后快的星夜。偶有不死的诗心,才写些哀哀怨怨的信给亲近的人,你总是快快地回:“外出三天,深夜踏雨归来,檐前出现一小叠信。中有你亲切的字迹,你的信柬自然令我喜欢。……
我的病情,好好坏坏,终须挨上一刀才见分晓。近两个月来的抱病自守,旦夕之间,情知对于生命的千般流转,尽须付与无尽的忍爱。我想,他朝小痊,如你之奔驰,亦须这样。一步一履,无非修行。至此,我依然深心乐观,来日或聚,愿其时你的事业大势底定,我亦澡雪精神。”
我们深心乐观着未来,几次击掌切磋,暗暗以创格自许,不屑袭调。负气使才如我,滔滔洒墨,似欲与千夫万夫一拚。
你见我清瘦异常,只吩咐我不可太夜太累,我委屈了,说:
“就活这么一次,我要飞扬跋扈!”你语重心长地说:“早慧,难享天年的,古来如此。”
你珍贵我这顽桀的生命,大大地甚于你自己的。那一回生日,你特地去寻玉送我,一龙一凤绕着净瓶(啊!会是观音的净瓶吗?),你说鬻玉的老者称这块玉的肌理具荷质,返家的途中经过南海路,你去植物园的荷花池,轻轻地轻轻地将这玉沁了又沁……你说:“生命恒有繁华落尽的感觉,只不过,不染淤泥!”
病魔却与你弄斧耍戗,你的眼开始不自觉地泪,夜半常因拭泪而难以入眠,你谦称这是宿业使然。在你卜居的深山穷野,你宛若处子与生灭大化促膝而谈,抱病独居的信,不改涓涓细流的字迹:“有天半夜不能安睡,出至阳台。山间天象澄明,月光大片大片洒落一地。忽然间,我看见自己月下的影子,细细瘦瘦,怯怯地,触目竟十分眼熟,但那分明不是日光中的‘我’。我呆呆地忖忖想想,啊,是了——是童话时候的‘我’!我好感动地望着那片身影,然后牵他入梦。偶得一悟,心情愿如庄周,处于病与不病之间。”
你第二度开刀,除去右颜面突变的肉瘤,我将一串琥珀念珠赠你,那是寺里一名师父突然脱下赠我的,我欢喜生命中“突然”的意象。你认真地戴在手腕,虚弱地在病榻上闭目。我又天真起来了,仿佛一名间谍,在你短兵相接的战场之前,先给你解药,你此后可以大胆地无惧地去迎喂毒的流箭。病后,你说:“我渐渐愿意把所有的悲沉、蒙昧、大痛、无明都化约到一种素朴的乐观上,我认为它是生命某种终极的境界。你知我知。”
最珍贵而美丽的,应该是你赴港念比较文学之前的半年。
你诗写得少了,专志狼吞文学批评的典籍,你戏谑这是一桩“反美”的工程,但要我千万注意,你并非不爱美。我说:
“管你家的什么美不美,天天念原文书,把一个人念得豆芽菜似的,这种美简直王八蛋!”你每星期总要回长庚医院追踪病情,我们相约在中午,趁我歇班的时刻,你教我念书。常常在市嚣流矢的小咖啡店里,你取出一叠白纸、一支钢笔,在喝了一口微冷的红茶之后,开始以沙哑沉浊的声音,为我唤来“福寇”(Michel Foucault),我静静地抱膝听着,进入神思所能触摸的最壮阔与最阴柔的空间,你的话幽浮起来:
“……如今,书写已和献祭发生关联,甚至和生命的献祭发生关联……”我幡然有悟:“等等,我下一本书的架构出来了,你要不要听!”知识的考掘通常转化为创作的考掘,我是锈刀,拿你当磨刀石。你不也说了吗,我的生命太千军万马,终究不会听你这座“紫微”。实而言之,你是一则遥远的和平,为了你,我必须不断地战争。
有一回,茶冷言尽,你取出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让我瞧:
一名十岁男童倚在漫画书店的租台边,白白净净的怯生生的,眼睛里有一股神秘的招引与微燃的悲喜,静静地与世界相看。
我惊叹起来:“多美啊!是你吗?”你欢喜地说:“是!”
那一回,你送我回报社上班,沿着木棉击掌、械实落墨的砖道,你微微地喟叹:“天!给我时间!”
香港一年,你终因病发大量出血而辍学,从中正机场直奔林口长庚,医师已开了病危通知书。你却幽幽转醒,看着病床边来来往往的友好、同窗,或者,你还在等,当养育的父母双亡,亲生的父母待寻。你那时已不能进食,肉瘤塞住口舌,话也不能说了。你见我来,兀自挣身下床,从杂乱的行李中掏出一块精致的香皂,多少年前,我说过一日三浴更甚于心头欢喜,你在纸上写着:“多洗澡!”那一刹——那百千万亿年只可能有一回的一刹,我想狠狠地置你于死。
半年来,我抗拒着再去看你,想回向给你七七四十九遍的经诵终于不能尽读,我压抑每一丝丝一缕缕一角角关于你的挂念。只有两回梦见,一次你以赤子的形象从半空掠过,我仰首不复寻踪;一次你款款而来,白白净净的面目,我大喜,问:“你好了?”你笑而不答,许久许久才说:“还没开始生病啦!”梦醒后,深深地痛恨自己,现世里的大欢大美被解构得还不够吗?连在可以作主的梦土,也要懦怯地缴械。我终究是个懦夫,不配英雄谈吐。
那么,敬爱的兄弟,我们一起来回忆那一日午后,所有已死的神鬼都应该安静敷座,听我娓娓诉说。
那一日,我借了轮椅,推你到医院大楼外的湖边,秋阳绵绵密密地散装,轮转空空,偶尔绞尽砖岸的莽草。我感觉到你的瘦骨宛若长河落日,我的浮思如大漠孤烟。当我们面湖静坐,即将忘却此生安在,突然,遥远的湖岸跃出一行白鹭,抟扶摇直上掠湖而去,不复可寻。湖水仍在,如沉船后,静静的海面,没有什么风,天边有云朵堆聚着。
你在纸上问我:“几只?”
我答:“十二只。”你平安地颔首。
也许,不再有什么诘屈聱牙的经卷难得了你我。当你恒常以诗的悲哀征服生命的悲哀,我试图以小说的悬崖瓦解宿命的悬崖;当我无法安慰你,或你不再关怀我,请千万记住,在我们菲薄的流年,曾有十二只白鹭鸶飞过秋天的湖泊。
犹似存在主义,
或是老庄,
或是一杯下午茶,
或两本借来的书。
百般凌虐你,你都不生气,或,只生一小会儿气。好似在你那里存了一笔巨款,我尽情挥霍,总也不光。有时失了分寸,你肃起一张沧桑后的脸,像一个蹇途者思索不可测的驿站,我就知道该道歉了,摸摸你深锁的额头说:“什法子,谁叫你欠我。不生气,生气还得付我利息。”
常常在早餐约会,或入了夜的市集。热咖啡、双面煎荷包蛋、烘酥了土司,及三分早报。你总替我放糖、一圈白奶,还打了个不切实际的哈欠。我喜欢晨光、翻报、热咖啡的烟更甚于盘中物,你半哄半骗,说瘦了就丑,我说:“喂,就吃!”
你果真叉起蛋片进贡而来,我从不吝惜给予最直接的礼赞:
“今天表现不错,记小功一支。”
早晨恒常令我欢心,仿佛摄取日出的力量,从睡眼沉静射入惊蛰的流动,有了奔驰的野性及征服的欲望。早晨对你却是苛责的,你雾着一张脸,听我意兴风发地擘画每一桩工作,帮你整理当日的行程及争辩的重点,战役的成果未必留给我们,但我们联手打过漂亮的仗。
入夜的城市更显得蠢蠢欲动,入夜的我通常是一只安静的软体动物,容易认错、善于仆役,不扎别人的自尊。你活跃于墨色的时空,以锐利的精神带着我游走于市集。一碗卤肉饭、石斑鱼汤、水煮虾也是令人难忘的饮食起居。我擅于剥虾、剔无刺的鱼肉,伺候你。你尽管放心地细数我的不对,定谳白日的蛮悍,我一向从善如流,乖乖地向你忏悔。
当市集悄悄撤退,夜也恹了,我打起一枚长长的呵欠,你说:“走吧!回家。”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归途。这城市无疑是我们巨构的室家,要各自走过冗长的通道,你回你的卧室,我有我的睡榻。
那么,的确必须用更宽容的律法才能丈量你我的轨道。你不曾因为我而放弃熟悉的生命潮汐——不管是过往的情涛、现实的波澜,或即将逼近的浪潮;我也不必为你而修改既定的秩序——我有我不能割舍的人际、工作的程序,及关于未来的编排。当我们相约,其实是趁机将自己从曲曲折折的轨道释放出来,以大而无当的姿势携手、寻路。你四十过二的音色里仍留有不肯成熟的童话(要不,你怎么老是叉橡皮筋偷袭我!);我二十又七的华容仍忘怀不去初为儿女的恣意(挺喜欢捧你的大手,一支一支地啃你的指头!);你时而化童时而老迈,我时而为人时而原兽,我们生动地演出内心被禁锢的角色,以城市为舞台,行人当盲目的观众。那些令人疲惫的典章制度不容推翻总可以暂忘,你虽然抱怨半生颠踬无以转圈,我却不曾怂恿你或然言弃——那些包袱早已变成心头肉,在我们分手后仍然继续由你背负的。如是,我期望每一次相聚,透过理智的剖析与情感之疏浚,更助益你昂然驼行。我深知,情会淡爱会薄,但作为一个坦荡的人,通过情枷爱锁的鞭笞之后,所成全的道义,将是生命里最昂贵的碧血。因而,你可以原始地袒露,常常促膝一夜,谈你孑然成长的大江南北、谈梦幻与现实互灭、谈你云烟过眼的诸多女人、谈你远去的妻与儿女……常常,我看到那一颗三十多年未落的噙泪。
同等地,我得以在你身上复习久违的伦常,属于父执与兄长的渴望。过于阴柔的家境,促使我必须不断训练自己雄壮、摹仿男系社会的权威;而我生命的基调,却是要命的抒情传统,三秋桂子十里芰荷的那种,遂拿你砌湖,我得以歌尽舞影,临水照镜(啊!我终究必须恋父情结)。实则如此,每一桩生命的垦拓,须要吮取各式情爱的果实,凡是亏空的滋味,人恒以内在的潜力去做异次元的再造。你在不知不觉中已被我修改,按着我心中的形象发音;正如我愿意为你而俯身,将自己捏成宽口的罍,以盛住你酒后崩塌的块垒——
任何一桩情缘,如果不能激励出另一种角色与规则,以弥补梦土与现实之间的断崖,终究不易被我珍爱。
于是,我们很理智地辩论着婚姻。
你说,不曾歇息的情涛,总难免落得一身萧索,过往的女人不是不爱,却发现愈爱得深愈陷泥淖;我说,这是剥夺,爱情之中藏有看不见的手。你说,如果我们结婚如何?我问,你视我为何?难道纷落的情锁不曾令你却步?你说,我在你心中不等同于女人,属于一种透明的中性——像白昼与黑夜,时而如男人清楚,时而如女性张皇,你能充分享受诉说,从最崔嵬的男峰吐露至最婉柔的女泽(你有时细心得像一名婢女),我欢愉你所陈述的,那表示,一个人对他(她)内在生命做多元创造的无限可能。而我开始叙述,关于多年来我们另辟蹊径,如今俨然一条轨道的情爱(请注意,放弃世俗轨道的通常要花更多心血为自己领航,且不再有回头的可能)。
我们成就一种无名的名分,住在无法建筑的居室,我不要求你成为我的眷属如同我厌烦成为任何人的局部,你不必放弃什么即能获得我的灌注,我亦有难言的顽固却能被你呵护,我们积极相聚也品尝不得不的舍离,遂把所能拥有的辰光化成分分秒秒的惊叹。如果爱情是最美的学习,我愿意作证,那是因为我们学到了布施胜于占取,自由胜于收藏,超越胜于厮守,生命道义胜于世俗的华居。想必你了解,婚姻只是情爱之海的一叶方舟,如果我们愿意乘桴浮于海,何必贪恋短暂的晴朗——要纵浪就纵浪到底吧!我已拍案下注,你敢不敢坐庄?
我们还要一座壳吗?让壳内众所皆知的游戏规则逐渐吞噬我们的章法。以我不靖的个性,难以避免对你层层剥夺;以你根深柢固的男系角色,终究会逐步对我干涉。原宥我深沉的悲观,婚姻也有雄壮的大义,但不适合于我——我喜于实验,易于推翻,遂有不断地、不断地裂帛。
我情愿把这城市当成无人的旷野,那一夜,我爬上大厦广场的花台,你一把攫住,将我驼在肩上,哼着歌儿,凛凛然走过两条街;被击溃之后如果有内伤,那内伤也带着目中无人的酣畅。有一日,深夜作别,我内心击打着滔滔逝水的悲切,不忍责忍你什么,只想一个人把漫漫长夜走完,你说起风了,脱下外衣披我,押我上车,在站牌旁频频向我挥手,然后孤独地走向你候车的街口。那一刹,我又剑拔弩张,想狠狠刺大化的心脏,遂在下一站下车,拚命地跑,越过城市将灭的灯色,汗水淋漓地回到你的背后,你多么单薄,掏烟、点火,长长地向夜空喷雾,像一名手无寸铁的人!我倏地蒙住你的眼睛,重重地咬你的耳朵:“不许动!”你回头,看我,错愕的神情转化成放纵的狂笑,我胜利了我说。
推荐阅读
- 快餐吃多了对以后会有啥影响
- 进行跑步等有氧训练完成后,饮食有啥需要注意的
- 高中生每天喝红牛对身体有啥影响
- 在家中办酒水有啥注意点
- 现在和好朋友住在一起,但是时常会有很多矛盾,而且现在住的地方离公司也比较远,有啥好的解决方法么也不伤害彼此之间的感情
- 女孩学医,选啥科比较好
- 北京2日游,可以咋安排,清明假期,有啥合适的希望知友可以推荐下
- 去美国读心理学博士有啥出路
- 北京有名有特色的店铺有啥
- 一见钟情的心理原因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