ж—Ҙеёё|40еӨҡе№ҙеҶҷдәҶиҝ‘дёӨеҚғдёҮеӯ—дҪңе“ҒпјҢеј зӮңпјҡеҶҷдҪңеҰӮеҗҢж—ҘеёёеҠіеҠЁ( дёү )
вҖңжңүдәәд»ҘдёәиҜ—зҡ„иҜ»иҖ…еӨӘе°‘пјҢжҲ‘еҸҜдёҚйӮЈж ·и®ӨдёәгҖӮиҜ—зҡ„иҜ»иҖ…жңҖеӨҡпјҢ他们еңЁиҜ»еҗ„з§ҚиҜ—пјҢеҢ…жӢ¬жІЎжңүжҢүз…§иҜ—зҡ„йҖҡеёёж јејҸеҲҶиЎҢзҡ„ж–Үеӯ—гҖӮжІЎжңүиҜ—е°ұжІЎжңүж–ҮеӯҰпјҢж–ҮеӯҰжңүиҜ»иҖ…пјҢиҜ—е°ұжңүиҜ»иҖ…гҖӮиҜ—зҡ„常规еҪўејҸеҮәзҺ°еңЁеҶҷдҪңдёӯпјҢиҝҷд№ҹжҳҜиҮӘ然иҖҢ然зҡ„пјҢдҪҶеҚҙдёҚдјҡжҳҜе…ЁйғЁгҖӮвҖқеј зӮңеҶҷж»ЎдәҶдёҖдёӘеҸҲдёҖдёӘеӨ§з¬”и®°жң¬пјҢзІҫиҮҙең°жҗҒеңЁд№Ұжһ¶дёҠпјҢиҝҷдәӣиҜ—жӯҢи®©д»–ж»Ўи¶ідё”еҝ«д№җгҖӮе°ҶжқҘжҠҠе®ғ们еҮәзүҲпјҢжҲ–з•ҷдҪңиҮӘиҜ»пјҢйғҪжҳҜжңүж„Ҹд№үзҡ„дәӢжғ…гҖӮиҜ—йҖҡеҗ‘еҝғзҒөж·ұеӨ„гҖӮзҰ»ејҖдәҶиҜ—зҡ„еҶҷдҪңпјҢе°ұдјҡжһҜж§ҒгҖӮзңҹжӯЈзҡ„иҜ—дәәжңӢеҸӢжҳҜжңҖеҘҪзҡ„жңӢеҸӢпјҢжҳҜеҝөеҝөдёҚеҝҳзҡ„жңӢеҸӢпјҢдҪҶ他们дёҚдёҖе®ҡжҖ»жҳҜдҪҝз”ЁиҜ—зҡ„еёёз”Ёж јејҸеҺ»еҒҡгҖӮ
вҖңжҲ‘и®ӨдёәеҶҷдҪңжҳҜеҝ«д№җзҡ„пјҢжҳҜе°Ҫе…ҙе°Ҫжғ…зҡ„дәӢжғ…гҖӮжҠҠзңҹжҖ§жғ…и—Ҹиө·жқҘзҡ„еҶҷдҪңдёҖе®ҡжҳҜз—ӣиӢҰзҡ„гҖҒиү°ж¶©зҡ„гҖӮеҰӮжһңжҲ‘жңүдёҖеӨ©еҶҷеҫ—иү°ж¶©дәҶпјҢе°ұдёҖе®ҡжҳҜйЎҫеҝҢеӨӘеӨҡдәҶпјҢжҳҜжҺ©еҺ»дәҶзңҹжҖ§жғ…пјҢжҳҜеҒҡзқҖжһҒдёҚеҝ«д№җзҡ„е·ҘдҪңпјҢйӮЈд№ҹе°ұжІЎжңүеёҢжңӣдәҶгҖӮдёҖйў—иҜ—еҝғи·іеҠЁзқҖпјҢдё–з•ҢзңӢдёҠеҺ»е°ұз”ҹжңәзӣҺ然гҖӮиҜ—дәәзҡ„еҝ§ж„Өе’Ңе–ңд№җйғҪжҳҜиҮӘ然иҖҢ然зҡ„пјҢдёҚжҳҜиғҪиЈ…еҮәжқҘзҡ„пјҢжӣҙдёҚжҳҜиғҪж №жҚ®йңҖиҰҒи®ҫи®ЎеҮәжқҘзҡ„гҖӮжҲ‘еёҢжңӣдёҖз”ҹйғҪжҳҜиҝҷж ·зҡ„дёҖдёӘиҜ—дәәгҖӮвҖқдәәжҙ»зқҖз—ӣиӢҰеӨӘеӨҡдәҶпјҢдҪҶеңЁиҝҷз§Қз—ӣиӢҰдёӯеҺӢиҝ«дәҶе…ЁйғЁзҡ„еӨ©зңҹпјҢдәәе°ұдјҡеҸҳеҫ—жӣҙеҸҜжӮІгҖӮд»–жғіиұЎиҮӘе·ұеҚідҪҝеҲ°дәҶе…«еҚҒеІҒзҡ„ж—¶еҖҷпјҢдҫқ然дјҡдҝқжҢҒеӨ©зңҹзғӮжј«зҡ„еӨ©жҖ§гҖӮ
马尔е…Ӣж–ҜиҜҙпјҢз”ҹжҙ»еҸӘжҳҜжҲ‘们иғҪеӨҹи®°дҪҸзҡ„ж—ҘеӯҗгҖӮвҖңеҰӮжһңз”ҹжҙ»д»…д»…жҳҜиҝҷж ·пјҢйӮЈеҶҷдҪңеҜ№дёҖдёӘдәәжқҘиҜҙжңүеӨҡд№ҲйҮҚиҰҒпјҒе№ёдәҸжңүдәҶеҶҷдҪңпјҢиҝҷжүҚиғҪдҪҝе·Із»ҸиҝҮеҺ»зҡ„ж—¶й—ҙи®°еҪ•дёӢжқҘгҖӮвҖқеј зӮңиҜҙпјҢжҺҘдёӢеҺ»зҡ„дәӢжғ…е°ұжҳҜеҘҪеҘҪеҶҷдҪңгҖӮд»–иҰҒеҶҷи®ёеӨҡи®ёеӨҡиҜ—пјҢеӣ дёәе®ғжҳҜи®°еҝҶзҡ„жңҖеҘҪж–№ејҸгҖӮ
д»Һе Ҷд№Ұзҡ„зӘқйҮҢиө°еҮәеҺ»
дёҚе°‘дәәжҲ–и®ёиҝҳи®°еҫ—пјҢ1993е№ҙеҸ‘з”ҹдәҶдёҖеңәдәәж–ҮзІҫзҘһеӨ§и®Ёи®әпјҢе…¶дёӯвҖңдәҢеј дәҢзҺӢвҖқд№ӢдәүйўҮдёәеј•дәәжіЁзӣ®гҖӮжүҖи°“вҖңдәҢеј вҖқжҳҜеј зӮңе’Ңеј жүҝеҝ—пјҢвҖңдәҢзҺӢвҖқеҲҷжҳҜзҺӢи’ҷе’ҢзҺӢжң”гҖӮиҝҷеңәеӨ§и®Ёи®әдёҺ1990е№ҙд»Јзҡ„зӨҫдјҡиҪ¬еһӢжңүе…іпјҢдҪҶд№ҹдёҚеҸӘеҰӮжӯӨпјҢе®ғе®һйҷ…дёҠеҸҚжҳ дәҶдёҖд»ЈдәәзІҫзҘһдёҠзҡ„еӣ°жғ‘гҖӮеҜ№дәҺ1950е№ҙд»ЈеүҚеҗҺеҮәз”ҹзҡ„дәә们жқҘиҜҙпјҢеҸ—зқҖзҗҶжғідё»д№үзҡ„ж•ҷиӮІй•ҝеӨ§пјҢйқўеҜ№дёҖдёӘ全然дёҚеҗҢзҡ„дё–з•Ңж—¶пјҢжҖҺиғҪдёҚж„ҹеҲ°еӣ°жғ‘пјҹеј зӮңиҜҙпјҡвҖңжҲ‘жҖ»и§үеҫ—пјҢдёҚдәҶи§Јиҝҷжү№дәәпјҢе°ұдёҚдјҡзҗҶи§ЈиҝҷдёӘж°‘ж—Ҹзҡ„зҺ°еңЁе’ҢжңӘжқҘгҖӮдәҺжҳҜжҲ‘е§Ӣз»Ҳжңүз§ҚеҶІеҠЁпјҢеҘҪеҘҪеҶҷеҶҷ他们гҖӮвҖқ
еҜ№дәҺиҝҷдёҖд»ЈдәәпјҢеј зӮңз”ЁвҖңдәҶдёҚиө·зҡ„гҖҒз»қйқһеҸҜжңүеҸҜж— зҡ„дёҖд»ЈдәәвҖқжқҘеҪўе®№гҖӮд»–иҜҙпјҢиҮӘе·ұиә«дёҠжңүиҝҷдёҖжӢЁдәәе…ұеҗҢзҡ„дјҳзӮ№е’ҢејұзӮ№гҖӮдёҚеҒңең°еҸҚжҖқе’Ңжү№еҲӨпјҢдҪңе“ҒеҶҷзҡ„е°ұжҳҜиҝҷдёӘиҝҮзЁӢгҖӮвҖңжҲ‘еҠЁжүӢеҶҷдёӢ第дёҖ笔зҡ„ж—¶еҖҷжҳҜпјҲдәҢеҚҒдё–зәӘпјүе…«еҚҒе№ҙд»Јжң«гҖӮеҰӮжһңдәӢе…ҲзҹҘйҒ“иҝҷжқЎй•ҝи·ҜжңҖз»ҲдјҡжҖҺж ·еҙҺеІ–еқҺеқ·пјҢжҲ‘жҲ–и®ёдјҡз•Ҹжғ§жӯўжӯҘгҖӮвҖқеј зӮңиҜҙпјҢеҶҷиҝҷйғЁд№Ұе®һеңЁжҳҜзӣӣе№ҙд№ӢдёҫгҖӮд»–ж— и®әеҰӮдҪ•д№ҹжғідёҚеҲ°пјҢиҰҒдёәе®ғиҠұеҺ»ж•ҙж•ҙ20е№ҙжңҖеҘҪзҡ„е…үйҳҙгҖӮеҚҒеҚ·жң¬зҡ„гҖҠдҪ еңЁй«ҳеҺҹгҖӢпјҢеҗҺжқҘиҺ·еҫ—第八еұҠиҢ…зӣҫж–ҮеӯҰеҘ–гҖӮз»Ҷз»ҶиҝҪ究иө·жқҘпјҢжҠҠдҪңе“Ғзҡ„дё»дәәе…¬е®ҡдҪҚдәҺең°иҙЁе·ҘдҪңиҖ…пјҢеӨ§жҰӮзјҳиҮӘеј зӮңз«Ҙе№ҙзҡ„зҗҶжғігҖӮ
вҖңжҲ‘еҮәз”ҹзҡ„ең°ж–№еңЁжө·иҫ№зҡ„жһ—еӯҗйҮҢгҖӮе°Ҹж—¶еҖҷпјҢжҜҚдәІе’ҢеӨ–зҘ–жҜҚйғҪеҫҲеҝҷпјҢжҲ‘еёёеёёзӢ¬иҮӘеңЁжһ—еӯҗйҮҢгҖҒжө·иҫ№зҺ©гҖӮеҗҺжқҘзңӢеҲ°еҫҲеӨҡеёҗзҜ·пјҢеҺҹжқҘйӮЈйҮҢеҸ‘зҺ°дәҶзҹіжІ№гҖҒйҮ‘зҹҝгҖҒз…ӨзҹҝпјҢең°иҙЁйҳҹжқҘдәҶгҖӮжҲ‘еҫҲеӯӨзӢ¬пјҢе°ұеёёеёёеҺ»еёҗзҜ·зҺ©пјҢеҺ»зқЎи§үпјҢеҗ¬ең°иҙЁйҳҹе‘ҳи®Іж•…дәӢпјҢзңӢ他们е·ҘдҪңгҖӮвҖқең°иҙЁйҳҹе‘ҳзҡ„з”ҹжҙ»е’Ңе·ҘдҪңеҜ№еј зӮңжҳҜжһҒеӨ§зҡ„иҜұжғ‘пјҢеҗҢж—¶д№ҹеҹӢдёӢдәҶеҪ“ең°иҙЁе·ҘдҪңиҖ…зҡ„жўҰжғіе’Ңжғ…з»“гҖӮеҗҺжқҘе…ҘиҜ»еёҲиҢғзҡ„еј зӮңпјҢд№ҹе§Ӣз»Ҳе…іжіЁең°иҙЁе·ҘдҪңиҖ…зҡ„дәӢгҖӮиҮід»ҠпјҢд»–зҡ„еёҗзҜ·зӯүең°иҙЁиЎҢеӨҙд»ҚжҳҜдёҖеә”дҝұе…ЁгҖӮ
еј зӮңе°ҶиҝҷеҚҒеҚ·д№Ұз§°дёәвҖңдёҖдҪҚең°иҙЁе·ҘдҪңиҖ…зҡ„жүӢи®°вҖқгҖӮд»–з”ЁеӨҡе№ҙж—¶й—ҙиө°йҒҚдәҶйӮЈдёӘең°еҢәзҡ„еұұеұұж°ҙж°ҙпјҢзҶҹжӮүдәҶжҜҸдёҖжқЎжІіжөҒе’Ңеұұи„үпјҢзҶҹжӮүдәҶйӮЈйҮҢзҡ„еӨ§еӨҡж•°жӨҚзү©е’ҢеҠЁзү©гҖӮд»–е°ҶйӮЈж¬ЎеҶҷдҪңзңӢдҪңжҳҜдёҖеңәжҢҒд№…зҡ„жҲҳеҪ№пјҢиҖҢйқһдёҖж¬ЎжҲҳж–—гҖӮ
еј зӮңжё…жҘҡең°и®°еҫ—пјҢ1987е№ҙеӨҸз§Ӣд№ӢдәӨпјҢд»–жӯЈеңЁйІҒиҘҝзҡ„дёҖзүҮжһ—еңәйҮҢйҮҮи®ҝпјҢзӘҒ然жҺҘеҲ°дәҶеӣһеҹҺејҖдјҡзҡ„йҖҡзҹҘгҖӮеҺҹжқҘжҳҜи®©д»–е’ҢеҮ дҪҚдҪң家дёҖиө·еҲ°еҹәеұӮжҢӮиҒҢгҖӮиө·еҲқд»–еӣ дёәз”ҹжҙ»е’ҢеҲӣдҪң秩еәҸзҡ„еҸҳеҠЁиҖҢж„ҹеҲ°жңүдәӣдёҚйҖӮпјҢдҪҶиҝҮдәҶдёҖж®өж—¶й—ҙд№ӢеҗҺпјҢеҫҲеҝ«еғҸд»–зҡ„дҪңе“ҒгҖҠиһҚе…ҘйҮҺең°гҖӢжүҖеҶҷзҡ„дёҖж ·пјҢжңүдәҶдёҖз§ҚжҠ•иә«иҮӘ然жҖҖжҠұзҡ„ж„үеҝ«гҖӮеңЁеҚҒеҮ еІҒж—¶пјҢд»–еҮ д№Һиө°йҒҚдәҶиғ¶дёңеҚҠеІӣзҡ„еұұеҢәе№іеҺҹгҖӮж•…ең°йҮҚиҝ”пјҢеҶҚж¬Ўз»ҸеҺҶиҝҷйҮҢзҡ„еұұж°ҙгҖҒж–ҮеҢ–гҖҒж°‘дҝ—пјҢеҗ¬еҲ°дёӣжһ—зҡ„йёҹеҸ«пјҢж„ҹеҸ—еұұйЈҺд»ҘеҸҠжө·йЈҺзҡ„ж°”е‘іпјҢд»–дјјд№ҺеӣһеҲ°е°‘е№ҙзҡ„е…үжҷҜвҖҰвҖҰеңЁгҖҠиһҚе…ҘйҮҺең°гҖӢдёӯпјҢд»–зғӯеҲҮең°еҶҷйҒ“пјҡвҖңдёҖдёӘдәәеҸӘиҰҒеҪ’жқҘе°ұдјҡеҜ»жүҫпјҢеҸӘиҰҒеҜ»жүҫе°ұдјҡеҰӮж„ҝгҖӮеӨҡд№ҲеҘҮжҖӘеҸҲеӨҡд№Ҳзҙ жңҙзҡ„дёҖжқЎеҺҹзҗҶпјҢжҲ‘дёҖејҜи…°е°Ҷе®ғжӢЈдәҶиө·жқҘгҖӮеҢҚеҢҗеңЁжіҘеңҹдёҠпјҢеғҸдёҖжЈөж¬ІиҰҒжүҺж №зҡ„ж ‘вҖ”вҖ”иҝҷз§Қж¬ІжұӮеӨҡж¬Ўиў«й№Ұй№үеӯҰиҲҢиҖ…з»ҷеј„и„ҸгҖӮжҲ‘иҰҒе°Ҷе…¶иҝҳеӣһеҺҹжқҘгҖӮжҲ‘еҝғзҒөйҮҢйӮЈдёӘйңҖжұӮжӯЈеғҸз«Ҙе№ҙдёҖж ·зғӯеҲҮзәҜжҙҒгҖӮвҖқ
жҺЁиҚҗйҳ…иҜ»
- дёӯеӣҪзҪ‘з»ңж–ҮеӯҰиғҪеҗҰж’•жҺүвҖңдәҢзӯүж–ҮеӯҰвҖқж Үзӯҫпјҹ
- дә”д»Јзҡ„з–Ҝеӯҗе®°зӣёпјҢеӣ е°ҸдәӢеҶҷдәҶ63дёӘеӯ—пјҢеҸ·з§°еӨ©дёӢ第дә”иЎҢд№Ұ
- е•Ҷжңқеӣ дҪ•иҖҢдәЎпјҹ专家жү“ејҖ3000еӨҡе№ҙеүҚзҡ„еҸӨеў“пјҢжүҫеҲ°дәҶзңҹзӣё
- жӯӨеү‘еңЁең°дёӢдёӨеҚғеӨҡе№ҙпјҢдёҚд»…д»ҺжңӘз”ҹй”ҲпјҢиҝҳй”ӢеҲ©ж— жҜ”пјҢиҝҷжҳҜдёәдҪ•
- е”җжңқз»ҸжөҺз№ҒиҚЈгҖҒиҙёжҳ“е•Ҷе“Ғз№ҒеӨҡпјҢдёәдҪ•й…’еҷЁжҲҗдёәж—Ҙеёёз”ҹжҙ»зҡ„ж Үй…Қпјҹ
- еј дёүдё°зҡ„з»ҸеҺҶеҫҲдј еҘҮпјҢйҮ‘еәёдёәдҪ•дёҚи®©д»–еҪ“дё»и§’еӣ дёәеҶҷдәҶе°ұдјҡжңүжјҸжҙһ
- еҸӨ代科дёҫз»ҸеҺҶ1300еӨҡе№ҙпјҢе…ӯйҰ–зҠ¶е…ғд»…жңүдёӨдҪҚпјҢ他们и°ҒжӣҙеҺүе®і
- дёӯеӣҪвҖңд»ҺжңӘж”№еҗҚвҖқзҡ„дёҖеә§еҹҺеёӮпјҢжІҝз”Ё3000еӨҡе№ҙпјҢеҸӘеӣ еҮәдәҶдёҖдҪҚзҫҺдәә
- д№ҫйҡҶзҡҮеёқдёҖз”ҹеҶҷдәҶеӣӣдёҮйҰ–иҜ—пјҢдҪҶд»…дёҖйҰ–е…ҘйҖүе°ҸеӯҰиҜҫжң¬пјҢеӯҰз”ҹеҚҙеҫҲе–ңж¬ўпјҒ
- ж•…е®«иҝҷеқ—зҘһеҘҮзҡ„зҹіеӨҙпјҢ200еӨҡе№ҙж— дәәж•ўеҠЁпјҢеҫҲеӨҡжёёе®ўж…•еҗҚиҖҢжқҘпјҒ



![[иҫ…еҠ©и®ӯз»ғ]еҲҶжё…дё»ж¬ЎпјҢиҫ…еҠ©и®ӯз»ғеҸӘиғҪжҳҜиҫ…еҠ©пјҒ](http://ttbs.guangsuss.com/image/a9e56a600a9c6f896d0b8d5345ff816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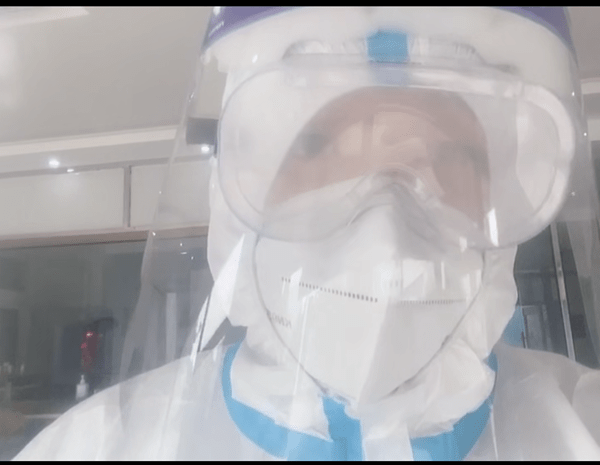


![[иө°з§Ғ]иӯҰж–№зӘҒиўӯиө°з§Ғд»“еә“пјҢеҸ‘зҺ°10жһ¶е…ұиҪҙж—ӢзҝјзӣҙеҚҮжңәпјҢеұ…然жҳҜзәҜжүӢе·Ҙжү“йҖ](http://img88.010lm.com/img.php?https://image.uc.cn/s/wemedia/s/2020/c8ccb32baca45ed2b7fdedb939dbab14.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