дәәй—ҙ | д№қеІҒеӨҡпјҢд»–жүҚиў«дәәд»ҺжҜҚдәІжүӢйҮҢи§Јж•‘еҮәжқҘ
жң¬ж–Үзі»зҪ‘жҳ“вҖңдәәй—ҙвҖқе·ҘдҪңе®ӨпјҲthelivingsпјүеҮәе“Ғ гҖӮ иҒ”зі»ж–№ејҸпјҡthelivings@vip.163.com

жҲ‘жҳҜжҠұзқҖеҗҢжғ…еҝғиө°иҝ‘иҝҷдёӘз”·еӯ©зҡ„ гҖӮеңЁйӮЈд№ӢеҗҺ пјҢ жҲ‘еҝҚдёҚдҪҸж„ҹж…Ё пјҢ ж„ҹж…Ёз”ҹе‘ҪеҠӣзҡ„дјҹеӨ§вҖ”вҖ”еңЁдёҚи®әдҪ•з§ҚйҖҶеўғйҮҢ пјҢ еӯ©еӯҗз«ҹйғҪиғҪжҲҗй•ҝпјӣд№ҹж„ҹж…ЁжҲ‘们зҡ„ж— зҹҘвҖ”вҖ”еңЁжҜҸдёҖжүҮй—ЁеҗҺ пјҢ еңЁе°Ғй—ӯзҡ„家еәӯзҺҜеўғйҮҢ пјҢ иҝҳжңүеӨҡе°‘еӯ©еӯҗеңЁжүҝеҸ—зқҖд»Өдәәйҡҫд»ҘзҪ®дҝЎзҡ„дәӢ гҖӮиҝҷдёӘз”·еӯ© пјҢ д»Һи®°дәӢејҖе§Ӣе°ұиў«жҜҚдәІвҖңеӣҡзҰҒвҖқеңЁе®¶дёӯ пјҢ зӣҙеҲ°иў«вҖңи§Јж•‘вҖқйӮЈеӨ© пјҢ е№ҙиҝ‘10еІҒзҡ„д»–й•ҝеҸ‘жҠ«иӮ© пјҢ з«ҷеңЁж»ЎеұӢзҡ„еһғеңҫйҮҢ гҖӮе°Ҹе„ҝеӯҗдә®дә®пјҡз»ҷжҜҚдәІиҜҙд№ҹжІЎз”Ё пјҢ жҲ‘з…§ж ·еҮәдёҚеҺ» гҖӮ2019е№ҙеә• пјҢ жҲ‘и§ҒеҲ°дә®дә®ж—¶ пјҢ д»–еҲҡиў«вҖңи§Јж•‘вҖқеҮәжқҘдёҖдёӘжңҲ пјҢ еңЁдёҖжүҖдё“й—ЁеӯҰж ЎйҮҢ гҖӮдёӢеҚҲдёӨзӮ№ пјҢ еӯҰз”ҹ们еҲҡз»“жқҹеҚҲдј‘ пјҢ ејҖе§Ӣз»ғд№ з«ҷйҳҹ гҖӮ дә®дә®з«ҷеңЁйҳҹе°ҫ пјҢ з©ҝзқҖз»ҹдёҖзҡ„ж ЎжңҚ пјҢ иў–еӯҗе’ҢиЈӨи…ҝйғҪй•ҝеӨӘеӨҡ гҖӮ д»–зҡ„еҠЁдҪңжңүдәӣеғөзЎ¬ пјҢ жҖ»жҳҜж…ўдёҖжӢҚ пјҢ еҲ«зҡ„еӯ©еӯҗйғҪиҪ¬иә«е®ҢжҜ• пјҢ д»–жүҚзңӢзңӢиә«иҫ№дәәејҖе§ӢжЁЎд»ҝ гҖӮи®ӯз»ғз»“жқҹеҗҺ пјҢ жҲ‘й—®дә®дә®д№ жғҜзҺ°еңЁзҡ„з”ҹжҙ»еҗ— гҖӮвҖңзҺ°еңЁд№ жғҜдәҶ пјҢ д»ҘеүҚдёҚд№ жғҜ гҖӮ вҖқжҲ‘еҜ№д»–иҜҙ пјҢ д»–еңЁиҝҷе„ҝжңҖе°Ҹ пјҢ дёӘеӯҗжҜ”е…¶д»–дәәзҹ®дёҖжҲӘ гҖӮ жҲ‘еҪ“然没жңүеҸ–笑зҡ„ж„ҸжҖқ пјҢ дҪҶд»–иҝҳжҳҜдёҚжңҚж°”ең°дәүиҫ© пјҢ вҖңе“Ҙе“Ҙ们йғҪжҜ”жҲ‘й«ҳеҫҲжӯЈеёёе•Ҡ пјҢ жҲ‘ж„ҹи§үжҲ‘е·Із»Ҹй•ҝй«ҳдәҶ пјҢ еҸӘжҳҜжҡӮж—¶иҝҳзңӢдёҚеҮәвҖҰвҖҰвҖқжҲ‘еҸ‘зҺ°иҮӘе·ұе…ҲеүҚзҡ„еҲӨж–ӯеӨұиҜҜдәҶ гҖӮ жҲ‘еҺҹжғіе’Ңдә®дә®зҡ„жІҹйҖҡеҸҜиғҪеҮәзҺ°й—®йўҳ пјҢ дҪҶ并没жңү пјҢ д»–зҡ„еә”еҜ№дјјд№ҺеҫҲиҮӘеҰӮ гҖӮжҲ‘еҸҲй—®д»–пјҡвҖңдҪ еҺҹжқҘжҳҜе’Ңи°ҒдёҖиө·з”ҹжҙ»зҡ„пјҹвҖқвҖңйҳҝиҠі гҖӮ вҖқйҳҝиҠіжҳҜдә®дә®жҜҚдәІйҫҡйңһзҡ„иЎЁеҰ№ гҖӮ иў«и§Јж•‘еҪ“жҷҡ пјҢ йҫҡйңһе°ұиў«йҖҒеҺ»еҪ“ең°зҡ„зІҫзҘһз—…йҷў пјҢ дә®дә®еңЁиЎЁе§ЁеҰҲ家дҪҸдәҶеҚҒеҮ еӨ© гҖӮжҲ‘дёҚзҹҘйҒ“дә®дә®жҳҜжҢүз…§ж—¶й—ҙйЎәеәҸеӣһзӯ”зҡ„й—®йўҳ пјҢ иҝҳжҳҜеңЁжңүж„Ҹең°йҒҝејҖдёҖдәӣд»Җд№Ҳ гҖӮ еҶҚй—® пјҢ йӮЈе’ҢиЎЁе§ЁеҰҲд№ӢеүҚе‘ўпјҹд»–йЎҝдәҶйЎҝ пјҢ иҜҙ пјҢ вҖңе’ҢжҲ‘еҰҲвҖқ гҖӮдә®дә®е’Ңд»–жҜҚдәІйҫҡйңһз”ҹжҙ»зҡ„ең°ж–№ пјҢ жҲ‘жӯӨеүҚе·Із»ҸеҺ»иҝҮ гҖӮ йӮЈжҳҜдёӘйқўз§Ҝи¶…иҝҮ90е№ізҡ„дёӨе®ӨдёҖеҺ… пјҢ зӣ®е…үжүҖеҸҠд№ӢеӨ„е…ЁжҳҜйӣ¶йЈҹгҖҒиЎЈзү©гҖҒжқӮзү©е’Ңеҗ„з§Қеҝ«йҖ’з®ұвҖ”вҖ”зӣёеҪ“дёҖйғЁеҲҶеҝ«йҖ’еҺӢж №е„ҝжІЎжӢҶ пјҢ е ҶжҲҗдёҖеә§еҸҲдёҖеә§е°Ҹеұұ гҖӮжҲ‘еҺ»зҡ„ж—¶еҖҷ пјҢ дә®дә®дёҚеңЁ пјҢ йҫҡйңһзҡ„зҲ¶жҜҚжӯЈеңЁе°Ҹеҝғзҝјзҝјең°з»ҷ收жӢҫ гҖӮ иҖҒдәәиҜҙйҫҡйңһд№ӢеүҚйғҪдёҚеҮҶдәәиҝӣеұӢ пјҢ зҺ°еңЁйҫҡйңһиў«йҖҒиө°дәҶ пјҢ 他们иҝҳеҶіе®ҡ收жӢҫдёҖдёӢвҖ”вҖ”вҖңзӨҫеҢә收еһғеңҫзҡ„дәәиҜҙ пјҢ жҜ”дёҖиҲ¬еһғеңҫе Ҷиҝҳи„ҸвҖқ гҖӮ иҖҢд№ӢжүҖд»ҘвҖңе°ҸеҝғзҝјзҝјвҖқ пјҢ жҳҜеӣ дёәеҮ еӨ©еүҚ пјҢ йҫҡйңһзҲ¶дәІеҺ»зІҫзҘһз—…йҷўзңӢеҘіе„ҝж—¶ пјҢ иў«е‘ҠзҹҘвҖ”вҖ”вҖңжҲ‘зҡ„дёңиҘҝдҪ 们дёҚеҮҶеҠЁ пјҢ иҰҒжҳҜдёўдәҶдёҖж · пјҢ еӣһеӨҙжҲ‘жүҫдҪ 们иө”вҖқ гҖӮдёӨдёӘиҖҒдәәеңЁеҮ еӨ©еҶ…зҝ»зңӢдәҶйҫҡйңһзҡ„дёҠзҷҫдёӘеҝ«йҖ’ пјҢ еҸӘжңүе·ІиҝҮжңҹдёӨдёүе№ҙгҖҒд»ҺеӨ–и§ӮдёҠйғҪе·Із»ҸйңүеҸҳдәҶзҡ„дёңиҘҝ пјҢ жүҚж•ўжү”жҺү гҖӮ иҝҷж—¶д№ҹжүҚеҲҡеҲҡжё…зҗҶеҮәе®ўеҺ… пјҢ дёҚеҲ°ж•ҙдҪ“е·ҘдҪңйҮҸзҡ„дёүеҲҶд№ӢдёҖ гҖӮ жҲ‘еҫҖеұӢеӯҗйҮҢиө°дәҶиө° пјҢ еұҸдҪҸе‘јеҗё пјҢ еҮ дёқи…җиҮӯе‘ід»Қжү§зқҖең°еҫҖйј»йҮҢй’» гҖӮжҲ‘еҪ“ж—¶еҫҲйҡҫжғіиұЎдә®дә®жҳҜеҰӮдҪ•еңЁиҝҷйҮҢи¶ідёҚеҮәжҲ·ең°з”ҹжҙ»дәҶе°Ҷиҝ‘10е№ҙ гҖӮеҫ…еҗ¬дә®дә®з»ҷжҲ‘жҸҸиҝ°еҗҺ пјҢ жғ…еҶөжҜ”жҲ‘жғіиұЎзҡ„иҝҳиҰҒзіҹ гҖӮ еҪ“жҲҝй—ҙзҡ„з©әй—ҙиў«жқӮзү©е Ҷж»ЎеҗҺ пјҢ дә®дә®зҡ„жҙ»еҠЁиҢғеӣҙи¶ҠжқҘи¶Ҡе°Ҹ гҖӮ жңүж—¶ пјҢ д»–жғіиҰҒдёӢеәҠ пјҢ вҖңз»“жһңиҫ№дёҠдёҖеӨ§еҸ иЎЈжңҚеҖ’дёӢжқҘдәҶ пјҢ еҘ№е°ұеҫҲз”ҹж°” гҖӮ вҖқдә®дә®ж јеӨ–委еұҲең°иЎҘе…… пјҢ вҖңдҪҶжҲ‘д№ҹжІЎеҠһжі• пјҢ еҘ№дёңиҘҝеӨӘеӨҡдәҶ пјҢ еј„д№ұжҳҜжІЎеҠһжі•зҡ„дәӢ гҖӮ йӮЈдәӣеҢ…иЈ№гҖҒзәё пјҢ жҲ‘дёҚзҹҘйҒ“еҺҹжқҘжҖҺд№Ҳж”ҫзҡ„ пјҢ еҸҲжғіеј„еҘҪ пјҢ еҸҲж”ҫдёҚеҘҪ гҖӮ еҘ№е°ұз”ҹж°” пјҢ е°ұи®ӯжҲ‘ гҖӮ вҖқйҖҗжёҗ пјҢ дә®дә®зҡ„еҗғе–қжӢүж’’йғҪеңЁеәҠдёҠиҝӣиЎҢ гҖӮ жҜҸеӨ©зқЎеҲ°11зӮ№е·ҰеҸіиө·еәҠ пјҢ еҗғ第дёҖйЎҝйҘӯ пјҢ вҖңзғӯе№Ійқў гҖӮ вҖқд»–еҸЈдёӯзҡ„зғӯе№ІйқўдёҚжҳҜжӯҰжұүзү№дә§ пјҢ иҖҢжҳҜйҫҡйңһз»ҷз…®зҡ„зғӯжҢӮйқў гҖӮ жҖ•жҲ‘дёҚжё…жҘҡ пјҢ дә®дә®иҝҳиҖҗеҝғи§ЈйҮҠвҖ”вҖ”вҖңе°ұжҳҜйӮЈз§Қе№Ізҡ„гҖҒжҜ”иҫғзӣҙзҡ„йқў гҖӮ жіЎйқўжҳҜжҜ”иҫғејҜзҡ„йӮЈз§Қ гҖӮ вҖқйҫҡйңһз»ҷд»–з…®вҖңзғӯе№ІйқўвҖқ пјҢ жҜҚеӯҗдҝ©дёҖдәәдёҖзў— гҖӮ иҝҷйЎҝйҘӯеҗҺ пјҢ иҰҒжҳҜжҷҡйҘӯж—¶й—ҙйҘҝдәҶ пјҢ йҫҡйңһдјҡз»ҷд»–еҗ„з§Қеҗ„ж ·йӣ¶йЈҹ пјҢ жІҷзҗӘзҺӣгҖҒйҘје№ІгҖҒзі–вҖҰвҖҰиҰҒжҳҜиҝҳйҘҝ пјҢ е°ұеҶҚз…®дёҖж¬Ўйқў гҖӮ йҫҡйңһзҹҘйҒ“иҝҷдәӣдёңиҘҝжІЎиҗҘе…» пјҢ еҗҺжқҘеҘ№д№ҹи§ЈйҮҠиҝҮ пјҢ вҖңжҲ‘еҸӘиғҪеңЁиҮӘе·ұзҡ„иҢғеӣҙд№ӢеҶ…еЎ«иӮҡеӯҗ гҖӮ жҲ‘жІЎжңүй’ұ пјҢ йҡҫйҒ“еҺ»еҒ·еҺ»жҠўеҗ—пјҹвҖқеҺ•жүҖд№ҹе®Ңе…Ёе өдҪҸдәҶ пјҢ дёҚжҳҜиғҪдҪҝз”Ёзҡ„ж ·еӯҗ гҖӮ жҲ‘й—®дә®дә® пјҢ жҖҺд№ҲдёҠеҺ•жүҖпјҹд»–иҜҙ пјҢ вҖңдёҠдёҚдәҶвҖқ гҖӮжҲ‘иҝҪй—® пјҢ йӮЈиҰҒжғіе°ҝе°ҝжҖҺд№ҲеҠһ гҖӮд»–е°Ҹе°Ҹзҡ„и„ёдёҠйңІеҮәдәҶдёҚйҖӮзҡ„иЎЁжғ… пјҢ вҖңиҝҷдёӘдёҚз”Ёй—®жҲ‘ пјҢ вҖқжҲ‘ж„ЈдҪҸдәҶ пјҢ дә®дә®еҸҲж‘ҮдәҶж‘ҮеӨҙиҜҙ пјҢ вҖңе°ұжӢҝдёӘзў—жӢүеұҺ пјҢ жҲ–иҖ…жӢҝдёҖдёӘжҜ”иҫғе№ІеҮҖзҡ„гҖҒеәҹжҺүзҡ„йӮЈз§Қзәёжқҝ пјҢ еңЁдёҠйқўжӢү гҖӮ вҖқдә®дә®иҮӘе·ұд№ҹиҜҙ пјҢ иҝҷж ·вҖңеҘҪи„ҸвҖқ пјҢ дҪҶвҖңжІЎеҠһжі•вҖқ гҖӮвҖңйӮЈдҪ зҹҘдёҚзҹҘйҒ“еӨ–йқў пјҢ дҪ жғідёҚжғіеҮәеҺ»пјҹвҖқжҲ‘й—®дә®дә® гҖӮд»–еӣһзӯ”жҲ‘ пјҢ вҖңжғі гҖӮ вҖқжҲ‘еҶҚй—® пјҢ вҖңдҪ жңүжІЎжңүи·ҹжҜҚдәІиҜҙиҝҮиҝҷ件дәӢпјҹвҖқвҖңиҜҙд№ҹжІЎз”Ё гҖӮ жҲ‘з…§ж ·еҮәдёҚеҺ» гҖӮ вҖқд»–и®°еҫ—жҜҚдәІи·ҹд»–и§ЈйҮҠиҝҮ пјҢ вҖңжҖ•жҲ‘иў«еҳІз¬‘ пјҢ жүҚдјҡдёҚи®©жҲ‘еҮәеҺ»вҖқ пјҢ вҖңеӣ дёәжҲ‘иў«зҲ¶жҜҚе«Ңејғ гҖӮ еҘ№дёҚжғіе…»жҲ‘зҡ„ пјҢ жҲ‘еҲҡдёҖеҮәз”ҹеҘ№е·®зӮ№жҠҠжҲ‘е®іжӯ» пјҢ з»ҷжҲ‘дёўеҲ°ж№–йҮҢ гҖӮ вҖқ9еІҒеҚҠзҡ„д»–зҘһжғ…еғҸдёӘе°ҸеӨ§дәә пјҢ еҸЈеӨҙзҰ…д№ҹжҳҜвҖңжІЎеҠһжі•вҖқгҖҒвҖңйӮЈд№ҹжІЎз”ЁвҖқд№Ӣзұ»зҡ„иҜқ гҖӮ д»–иҜҙжҳҜеңЁжүӢжңәйҮҢи§Ҷйў‘еӯҰзҡ„вҖ”вҖ”йӮЈжҳҜд»–зҡ„вҖңеӯҰд№ ж–№ејҸвҖқ гҖӮжҲ‘й—®д»–д»Җд№Ҳж—¶еҖҷејҖе§ӢжңүжүӢжңәзҡ„ гҖӮ д»–иҜҙ пјҢ е…«д№қеІҒж—¶жүҚзңӢ гҖӮ жҲ‘иҜҙ пјҢ дҪ зҺ°еңЁжүҚд№қеІҒ гҖӮ д»–зә жӯЈжҲ‘ пјҢ вҖңд№қеІҒеҚҠ гҖӮ вҖқзӨҫеҢәе·ҘдҪңдәәе‘ҳпјҡ第дёҖзңјзңӢеҲ°е°Ҹеӯ© пјҢ еӨ§е®¶йғҪе“ӯдәҶзӨҫеҢәд№Ұи®°иҜҙ пјҢ 2016е№ҙ пјҢ дә®дә®зҡ„еӨ–е©ҶжӣҫжүҫеҲ°зӨҫеҢә пјҢ дёҖеүҜж¬ІиЁҖеҸҲжӯўзҡ„ж ·еӯҗ гҖӮ еӣһйҒҝдәҶе…¶д»–дәә пјҢ иҖҒдәәжүҚеӢүејәиҜҙеҮә пјҢ иҮӘе·ұжңүдёӘеӨ–еӯҷ пјҢ е·Із»Ҹдә”е…ӯеІҒдәҶ пјҢ дёҖзӣҙжІЎжңүдёҠжҲ·еҸЈ пјҢ еҘ№жғіеҒҡдё»з»ҷеӯ©еӯҗдёҠжҲ·еҸЈгҖҒеёҰеӯ©еӯҗдёҠеӯҰ гҖӮвҖңжғ…еҶөеҫҲзү№ж®ҠвҖҰвҖҰвҖқиҖҒдәәи§ЈйҮҠиҜҙ пјҢ иҮӘе·ұзҡ„еҘіе„ҝйҫҡйңһжӮЈжңүзІҫзҘһз–ҫз—… пјҢ дә®дә®еҸҲжҳҜйқһе©ҡеӯҗ пјҢ зҲ¶дәІжүҫдёҚеҲ° пјҢ жүҖд»ҘеҮәз”ҹеҗҺдёҖзӣҙжІЎдёҠжҲ·еҸЈ пјҢ жӢ–еҲ°зҺ°еңЁ гҖӮзӨҫеҢәе·ҘдҪңдәәе‘ҳеҫҲеҝ«е°ұеҺ»ж ёе®һдәҶ гҖӮвҖңжҲ‘жүҫеҲ°йҫҡйңһ家 пјҢ ж•ІеӨ§й—Ё пјҢ еҚҠеӨ©жІЎдәәеә” гҖӮ еҗҺжқҘж•ІзӘ—жҲ·й—Ё пјҢ еҘ№еә”дәҶ пјҢ иө°еҲ°зӘ—жҲ·иҫ№й—®жҲ‘们д»Җд№ҲдәӢ гҖӮ жҲ‘иҜҙжғідәҶи§ЈдёҖдёӢеӯ©еӯҗдҪҸдёҚдҪҸеңЁиҝҷйҮҢ пјҢ иғҪеҗҰи§ҒдёҖдёӢ гҖӮ еҘ№иҜҙе°Ҹеӯ©еңЁзқЎи§ү пјҢ дёҚж–№дҫҝ гҖӮ вҖқзӨҫеҢәд№Ұи®°еҪ“ж—¶е°ұи§үеҫ—еҘҮжҖӘ пјҢ вҖңеҘ№д№ҹжІЎејҖй—Ёи·ҹжҲ‘们дәӨи°Ҳ пјҢ йӮЈдёӘзӘ—жҲ·д№ҹжҳҜз”ЁзәёзіҠиө·жқҘзҡ„ пјҢ зңӢдёҚи§ҒйҮҢйқў гҖӮ вҖқдёҚеӨ§еҘҪжҺҘи§Ұ пјҢ жҳҜзӨҫеҢәд№Ұи®°еҜ№йҫҡйңһзҡ„第дёҖеҚ°иұЎ гҖӮ е·ҘдҪңдәәе‘ҳйҷҶз»ӯеҺ»жүҫдәҶеҮ ж¬Ў пјҢ йҫҡйңһеҗҺжқҘд№ҹеҮәй—ЁдәҶ пјҢ з«ҷеңЁйҷўеӯҗйҮҢе’ҢеӨ§е®¶иҒҠдәҶеҮ еҸҘ пјҢ иҜҙеёҢжңӣзӨҫеҢәиғҪеё®еҝҷжүҫжүҫдә®дә®зҡ„зҲ¶дәІ гҖӮ вҖңеҘ№зҡ„еҺҹиҜқжҳҜ пјҢ еҸӘиҰҒжүҫеҲ°еӯ©еӯҗзҡ„зҲ¶дәІ пјҢ йӮЈе°ұд»Җд№ҲйғҪеҘҪиҜҙ пјҢ д»Җд№ҲйғҪеҘҪеҠһ гҖӮ вҖқеҸӘжҳҜиҜқиҷҪиҝҷд№ҲиҜҙ пјҢ йҫҡйңһеҚҙеҸҲжҸҗдҫӣдёҚеҮәд»Җд№Ҳжңүж•ҲдҝЎжҒҜ гҖӮ вҖңеҘ№иҜҙе’Ңдә®дә®зҲ¶дәІжҳҜQQеҘҪеҸӢ пјҢ дҪҶеҜ№ж–№ж—©е°ұеҲ жҺүеҘ№дәҶ пјҢ еҘ№еҸӘи®°еҫ—еҜ№ж–№зҡ„QQеӨҙеғҸ пјҢ иҝҳжҳҜзі»з»ҹйҖҡз”Ёзҡ„йӮЈз§Қ гҖӮ вҖқе·ҘдҪңдәәе‘ҳиҷҪ然д»ҺжІЎи§ҒиҝҮдә®дә® пјҢ дҪҶд№ҹзЎ®и®ӨжңүдёӘеӯ©еӯҗдҪҸеңЁйӮЈйҮҢ гҖӮ вҖңжңүдёҖж¬ЎжҲ‘们йҡ”зқҖзҺ»з’ғе–Ҡдә®дә® пјҢ еӯ©еӯҗеңЁйҮҢйқўеә”дәҶдёҖеЈ° гҖӮ вҖқжңҖз»ҲзӨҫеҢәж°‘иӯҰйҖҡиҝҮзү№ж®ҠзЁӢеәҸ пјҢ з”ұдә®дә®еӨ–е©ҶжҸҗдҫӣеҮәз”ҹиҜҒжҳҺ пјҢ иҝҷжүҚз»ҷдә®дә®дёҠдәҶжҲ·еҸЈ гҖӮ2019е№ҙ пјҢ дә®дә®еӨ–е©ҶеҶҚеәҰжүҫеҲ°зӨҫеҢә пјҢ иҜҙиҝҷдәӣе№ҙжғ…еҶөйқһдҪҶжІЎжңүеҘҪиҪ¬ пјҢ еҸҚиҖҢжҒ¶еҢ–дәҶ гҖӮ жҚ®еҘ№жүҖзҹҘ пјҢ йҫҡйңһиҝҷеҮ е№ҙжқҘжІЎи®©е„ҝеӯҗеҮәиҝҮй—Ё пјҢ иҝҷи®©зӨҫеҢәд№Ұи®°еҫҲж„ҸеӨ– гҖӮвҖңжҲ‘и®°еҫ—пјҲеҪ“е№ҙпјүеҘ№иҜҙиҝҮ пјҢ дә®дә®дёҚйҖӮеҗҲеңЁжҷ®йҖҡеӯҰж ЎйҮҢиҜ»д№Ұ пјҢ еҘ№дјҡжүҫж—¶й—ҙеёҰе°Ҹеӯ©еҒҡдёӘжҷәеҠӣжЈҖжҹҘ пјҢ з»“жһңеҚҙдёҖзӣҙжІЎеҠЁйқҷ гҖӮ вҖқдёҖж–№йқў пјҢ зӨҫеҢәе·ҘдҪңдәәе‘ҳеқҡжҢҒеҠқеҜј пјҢ иҝҳз»ҷдә®дә®еёҰеҺ»д№ҰеҢ…гҖҒж–Үе…·зӯүзӨјзү©вҖ”вҖ”вҖңйҫҡйңһд№ҹ收дёӢдәҶ пјҢ иҜҙи°ўи°ўжҲ‘们 пјҢ еӯ©еӯҗеңЁдј‘жҒҜ пјҢ еҘ№дјҡиҪ¬дәӨвҖқпјӣеҸҰдёҖж–№йқў пјҢ еҢәйҮҢд№ҹжҲҗз«ӢдәҶдё“й—Ёзҡ„е·ҘдҪңз»„ пјҢ иҒ”еҗҲж°‘ж”ҝгҖҒжі•йҷўгҖҒе…¬е®үгҖҒж•ҷиӮІеұҖзӯүеӨҡйғЁй—Ё пјҢ еҮҶеӨҮеүҘеӨәйҫҡйңһзҡ„зӣ‘жҠӨдәәиө„ж ј гҖӮ2019е№ҙ6жңҲеә• пјҢ еҢәж°‘ж”ҝеұҖдҪңдёәз”іиҜ·дәә пјҢ еҗ‘жі•йҷўжҸҗдәӨдәҶиҜүи®ј пјҢ жі•йҷўйҡҸеҗҺејҖеұ•и°ғжҹҘ гҖӮ 2019е№ҙ8жңҲ пјҢ жі•йҷўд»ҘвҖңзӣ‘жҠӨдҫөе®івҖқдёәз”ұ пјҢ ж’Өй”ҖдәҶйҫҡйңһзҡ„зӣ‘жҠӨдәәиө„ж ј пјҢ 并жҢҮе®ҡдә®дә®зҡ„еӨ–е…¬дҪңдёәд»–зҡ„жі•е®ҡзӣ‘жҠӨдәә гҖӮж’Өй”Җзӣ‘жҠӨдәәиө„ж ј пјҢ е…¶е®һе°ұжҳҜдёҖз§Қжғ©зҪҡ пјҢ иЎЁжҳҺзӣ‘жҠӨдәә并没жңүеұҘиЎҢеә”жңүзҡ„иҒҢиҙЈ гҖӮ еҰӮжһңжңүиҜҒжҚ®иҜҒжҳҺйҫҡйңһиҷҗеҫ…еӯ©еӯҗ пјҢ еҘ№еҸҜиғҪиҝҳдјҡиў«иҝҪ究еҲ‘дәӢиҙЈд»» гҖӮ жі•е®ҳд№ҹжғіиҝҮиҝҷдёҖзӮ№ гҖӮ еҸӘжҳҜеңЁзҺ°жңүзҡ„жі•еҫӢ规е®ҡйҮҢ пјҢ зҰҒй”ўе„ҝеӯҗиҝҳдёҚеұһдәҺвҖңиҷҗеҫ…вҖқ гҖӮжі•йҷўеҲӨеҶіз”ҹж•ҲеҗҺ пјҢ е·ҘдҪңдәәе‘ҳд№ҹеңЁзӯү пјҢ зңӢзңӢйҫҡйңһжҳҜеҗҰдјҡдё»еҠЁеұҘиЎҢ гҖӮ еҸҜеҘ№д»Қж—§еӨ§й—Ёзҙ§й—ӯ пјҢ 9жңҲ1ж—Ҙ пјҢ ж•ҷиӮІеұҖе·ҘдҪңдәәе‘ҳдёҠй—Ё пјҢ дәӨз»ҷйҫҡйңһдёҖд»ҪвҖңд№үеҠЎж•ҷиӮІе…ҘеӯҰйҖҡзҹҘд№ҰвҖқ пјҢ е‘ҠзҹҘеҘ№ пјҢ е„ҝз«Ҙдә«жңүжҺҘеҸ—д№үеҠЎж•ҷиӮІзҡ„жқғеҲ© пјҢ иҰҒжұӮйҫҡйңһйҖҒеӯ©еӯҗдёҠеӯҰ гҖӮ вҖңдҪҶйҫҡйңһд»ҚеңЁж•·иЎҚ гҖӮ жҲ‘们еӨ§е®¶и®Ёи®ә пјҢ дёҖе®ҡиҰҒйҮҮеҸ–жҺӘж–Ҫ пјҢ жҠҠе°Ҹеӯ©и§Јж•‘еҮәжқҘ гҖӮ вҖқи§Јж•‘еҫ—зӯүйҫҡйңһеҮәй—Ёж—¶жүҚиғҪиҝӣиЎҢ пјҢ дёҚ然жҲҝеӯҗеҶ…йғЁзҡ„жғ…еҶөжІЎдәәзҹҘйҒ“ пјҢ еӯ©еӯҗзҡ„е®үе…Ёж— жі•дҝқиҜҒ гҖӮ2019е№ҙ11жңҲ пјҢ зӨҫеҢәж°‘иӯҰеңЁжҡ—дёӯи§ӮеҜҹдәҶеҮ еӨ© пјҢ зЎ®и®ӨйҫҡйңһдјҡеңЁеӮҚжҷҡејҖй—ЁеҸ–еҝ«йҖ’ пјҢ вҖңпјҲеҪ“ж—¶пјүиҝҳжңүдёҖдёӘз»ҶиҠӮ пјҢ еҘ№еҮәжқҘжҷҫдәҶдёӢиў«еӯҗ пјҢ жҷҫдёҠеҺ»гҖҒж”ҫдёӢжқҘ пјҢ еҶҚжҷҫдёҠеҺ» пјҢ иҝҷж ·йҮҚеӨҚдәҶдёҖдёӘеӨҡе°Ҹж—¶вҖҰвҖҰвҖқжңҖз»Ҳ пјҢ еңЁдёҖеӨ©жҷҡдёҠ7зӮ№еӨҡ пјҢ иӯҰеҜҹеңЁйҫҡйңһеҮәй—ЁеҸ–еҝ«йҖ’зҡ„ж—¶еҖҷе°ҶеҘ№жҺ§еҲ¶ пјҢ йҖҒеҺ»дәҶеҢ»йҷў пјҢ е·ҘдҪңдәәе‘ҳиҝҷжүҚз»ҲдәҺеҫ—д»Ҙиө°иҝӣйҫҡйңһ家вҖ”вҖ”еҪ“еӨ§е®¶иё©зқҖеәҹзәёеЈігҖҒжқӮзү©з©ҝиҝҮе®ўеҺ… пјҢ зңӢи§Ғз”·еӯ©з«ҷеңЁйҮҢйқўдёҖдёӘжҲҝй—ҙзҡ„еәҠдёҠ гҖӮ иҜҙжҳҜеәҠ пјҢ е°ұжҳҜеһғеңҫе°Ҹеұұдёӯй—ҙз©әзқҖзҡ„гҖҒеҸӘеӨҹд»–дёҖдёӘе°ҸеЁғеЁғз«ҷзқҖзҡ„ең°ж–№ гҖӮвҖңжҲ‘第дёҖзңјзңӢеҲ°е°Ҹеӯ© пјҢ зңјжіӘе°ұжөҒеҮәжқҘдәҶ гҖӮ д»–еӨҙеҸ‘й•ҝй•ҝзҡ„ пјҢ з©ҝдәҶдёҖ件еҸ‘зҡ„йӮЈз§ҚеӨ–зҪ© пјҢ дёҖжқЎеә”иҜҘжҳҜд»–еҰҲеҰҲзҡ„зІүиүІиЈӨеӯҗ гҖӮ вҖқзӨҫеҢәд№Ұи®°иҜҙ гҖӮзңӢеҲ°иҝҷд№ҲеӨҡйҷҢз”ҹдәәеҮәзҺ° пјҢ дә®дә®зҡ„第дёҖеҸҘиҜқз«ҹ然жҳҜиӢұж–Үзҡ„вҖңwhatвҖқ пјҢ иҝҳжңүдёҖеҸҘи„ҸиҜқвҖңWhat the fxxk.вҖқзӨҫеҢәд№Ұи®°зҡ„иҝҷдёӘиҪ¬иҝ°еӣ°жү°дәҶжҲ‘и®ёд№… гҖӮ жҲ‘еҗҺжқҘй—®иҝҮдә®дә®е“ӘйҮҢеӯҰзҡ„ пјҢ д»–иҮӘе·ұд№ҹиҜҙдёҚжё… пјҢ жҲ‘зҢңжөӢ пјҢ еҸҜиғҪд№ҹжҳҜеҲ·жүӢжңәдёҠзҡ„е°Ҹи§Ҷйў‘и·ҹзқҖеӯҰзҡ„ гҖӮдёҖејҖе§Ӣ пјҢ дә®дә®дёҚж„ҝж„Ҹиө°еҮәеҺ» гҖӮ еҗҺжқҘ пјҢ дёҖдёӘеҘіж°‘иӯҰдёҠеүҚй—®д»–йҘҝдёҚйҘҝ пјҢ з”ЁвҖңеҘҪеҗғзҡ„еҘҪзҺ©зҡ„вҖқиҜҙеҠЁдәҶд»– пјҢ жүҚжҠҠд»–жҠұеҮәдәҶй—Ё гҖӮ иө°д№ӢеүҚеӯ©еӯҗиҝҳдёҚеҝҳиҜҙ пјҢ вҖңжҠҠжҲ‘зҡ„зүӣеҘ¶жӢҝдёҠвҖқ гҖӮ й—ЁеӨ– пјҢ д»–зҡ„еӨ–е…¬еӨ–е©Ҷд№ҹжқҘдәҶ пјҢ вҖңеӨ–е©Ҷ第дёҖеҸҘиҜқе°ұжҳҜ пјҢ дә®дә® пјҢ еӨ–е©ҶеҘҪжғідҪ гҖӮ дёӨдёӘиҖҒдәәйғҪжҺүжіӘдәҶ гҖӮ вҖқзӯүдәәеҮәжқҘдәҶ пјҢ еӨ§е®¶жүҚжіЁж„ҸеҲ°дә®дә®зҡ„зҡ®иӮӨеҚҒеҲҶиӢҚзҷҪ пјҢ вҖңзҷҪеҫ—еҗ“дәә пјҢ д»ҺжқҘжІЎжҺҘеҸ—йҳіе…үзҡ„йӮЈз§Қ гҖӮ йӮЈжҷҡйЈҺеҘҪеӨ§ пјҢ дә®дә®з©ҝзқҖд»–еҰҲеҰҲзҡ„жӢ–йһӢ пјҢ иҝҳжІЎз©ҝиўңеӯҗ гҖӮ вҖқеҸҰдёҖдёӘе·ҘдҪңдәәе‘ҳиө¶зҙ§дёҠиЎ—еҺ»з»ҷеӯ©еӯҗд№°иЎЈжңҚ гҖӮдә®дә®иө°еҮәжҲҝй—ҙеҗҺжҳҫеҫ—еҫҲжҙ»и·ғ пјҢ зңӢд»Җд№ҲйғҪи§үеҫ—ж–°еҘҮ гҖӮ жҠ¬еӨҙзңӢи§Ғдә”еұӮжҘј пјҢ иҜҙдәҶеҸҘ пјҢ вҖңе“ҮеЎһ пјҢ йӮЈдёӘжҘјеҘҪй«ҳ гҖӮ вҖқеҶҚеҫҖеүҚиө°жҳҜе°ҸеҢәж“Қеңә пјҢ дә®дә®еҸҲй—® пјҢ йӮЈдәӣеӯ©еӯҗ们踢зқҖзҡ„еңҶеңҶзҡ„дёңиҘҝжҳҜд»Җд№Ҳ гҖӮи№Ұи№Ұи·іи·іең°иө°дәҶдёҖдјҡе„ҝ пјҢ дёҖдҪҚж°‘иӯҰз«ҜжқҘдәҶдёҖд»Ҫе°ҸйҰ„йҘЁ пјҢ еӨ§е®¶еқҗеңЁй©¬и·ҜзүҷеӯҗдёҠ пјҢ дә®дә®иҜҙ пјҢ вҖңжҲ‘дёҚзҹҘйҒ“иҝҷдёӘжҖҺд№Ҳеҗғ гҖӮ вҖқж°‘иӯҰе‘ҠиҜүд»– пјҢ йҰ„йҘЁе°ұжҳҜйқўзҡ®еҢ…зқҖйҰ… пјҢ зӣҙжҺҘе’¬ пјҢ еҸҲиҜҙ пјҢ вҖңиҝҷ家жҲ‘з»Ҹеёёеҗғ пјҢ еҫҲеҘҪеҗғ пјҢ д»ҘеҗҺдҪ д№ҹеҸҜд»ҘеҺ»д№° гҖӮ вҖқдә®дә®й©¬дёҠиҜҙ пјҢ вҖңеҸҜжҲ‘дёҚзҹҘйҒ“жҖҺд№Ҳд№° пјҢ жІЎд№°иҝҮ гҖӮ вҖқеӨ§жҰӮд№ҹжҳҜ第дёҖж¬ЎзңӢи§ҒдёҖж¬ЎжҖ§зҡ„еЎ‘ж–ҷеӢәеӯҗ пјҢ дә®дә®жӢҝзқҖй—® пјҢ вҖңдҪ иҝҷдёӘжҳҜд»Җд№Ҳ пјҢ е’Ң家йҮҢз”Ёзҡ„дёҚдёҖж · гҖӮ вҖқеҗғе®ҢйҰ„йҘЁеҗҺ пјҢ ж°‘иӯҰеёҰдә®дә®еҺ»зҗҶеҸ‘ пјҢ вҖңжң¬жқҘжғіеүӘзҹӯ пјҢ еҗҺжқҘдёҖзңӢеӨҙзҡ®йғҪз»“з—ӮдәҶ пјҢ еҸӘиғҪе…ЁйғЁеүғжҺү гҖӮ вҖқ他们з»ҷдә®дә®еүғдәҶдёӘе…үеӨҙ пјҢ д№ӢеҗҺз»ҷд»–жҙ—жҫЎ пјҢ вҖңд»–й—®жҲ‘жІҗжөҙйңІжҳҜд»Җд№Ҳ пјҢ д»–иҜҙиҮӘе·ұд»ҺжқҘжІЎжҙ—иҝҮжҫЎ гҖӮ вҖқжҜҚдәІйҫҡйңһпјҡдёәд»Җд№Ҳд№ӢеүҚдёҚжқҘе…іеҝғжҲ‘пјҹжҲ‘еҸҲжІЎиҷҗеҫ…жҲ‘еӯ©еӯҗвҖңжҲ‘ж„ҹи§үеҫҲеҸҜжҖ• пјҢ жҲ‘и§үеҫ—еҫҲдёҚе…¬е№і пјҢ еӣ дёәжҲ‘жІЎжңүй”ҷ гҖӮ дёәд»Җд№ҲиҰҒжҠҠжҲ‘жҠ“еҲ°иҝҷйҮҢе…ізқҖпјҹвҖқ2019е№ҙ12жңҲзҡ„дёҖеӨ©дёҠеҚҲ пјҢ жҲ‘еҺ»еҢ»йҷўжүҫйҫҡйңһ пјҢ жғіе’ҢеҘ№и°Ҳи°Ҳ пјҢ еҘ№еҰӮжӯӨеҜ№жҲ‘иҜҙ гҖӮйҫҡйңһз”ҹдәҺ1968е№ҙ пјҢ иӮІжңү3дёӘеӯ©еӯҗ пјҢ дҪҶйқўе®№зңӢдёҚеҮәе·Іе№ҙиҝҮдә”ж—¬ гҖӮ еңЁеҢ»йҷўйҮҢ пјҢ еҘ№д»Қ然画дәҶеҰҶ пјҢ йҷӨдәҶй»‘й»‘зҡ„зңјзәҝжңүдәӣеҮәжҲҸ пјҢ е…¶д»–йғЁеҲҶжҢәе’Ңи°җ гҖӮ еҘ№зҡ„дёӘеӯҗе°Ҷиҝ‘дёҖзұідёғ пјҢ иә«жқҗиӢ—жқЎ пјҢ еӣӣиӮўдҝ®й•ҝ пјҢ еңЁиҝҷеҚ—ж–№еҹҺеёӮйҮҢеҫҲзӘҒеҮә гҖӮеҘ№иҜҙ пјҢ иҰҒзӯүеҘ№еҮәйҷўеҗҺеҶҚи°Ҳ пјҢ 并и·ҹжҲ‘жҸҗдәҶиҰҒжұӮпјҡвҖңдҪ еҺ»й—®еҢ»з”ҹ пјҢ жҲ‘д»Җд№Ҳж—¶еҖҷиғҪеҮәйҷўпјӣжҲ–иҖ…дҪ и·ҹеҢ»з”ҹиҜҙ пјҢ и®©жҲ‘еҮәеҺ» гҖӮ вҖқжҲ‘иҜҙ пјҢ иҝҷдәӢжҲ‘еҸҜеҒҡдёҚдәҶдё» пјҢ дҪҶиҝҳжҳҜеёҢжңӣжңүжңәдјҡдәҶи§ЈеҘ№зҡ„жғіжі• гҖӮеҘ№жҖқзҙўдәҶдёҖдјҡе„ҝ пјҢ ж”№еҸҳдәҶжғіжі• пјҢ иҜҙиҮӘе·ұиҰҒе…ҲвҖңж•ҙзҗҶдёҖдёӢжҖқи·ҜвҖқ гҖӮвҖңдҪ и§үеҫ—иҮӘе·ұжңүз—…еҗ—пјҹвҖқжҲ‘й—®еҘ№ гҖӮвҖңиҝҷдёӘ пјҢ жҲ‘иҝҳйңҖиҰҒзЎ®и®ӨдёӢ гҖӮ е…¶е®һжҲ‘и§үдёҚи§үеҫ—并дёҚйҮҚиҰҒ пјҢ йҮҚиҰҒзҡ„жҳҜеӣҪ家法еҲ¶дёҚжҳҜеҫҲеҒҘе…Ё гҖӮ вҖқйҫҡйңһжҠұжҖЁ пјҢ иҜҙиҮӘе·ұ11жңҲ13ж—Ҙиў«дәәи®ҫи®ЎвҖңжҠ“вҖқиҝӣжқҘ пјҢ вҖңжқҘдәҶеҫҲеӨҡдәәжҠҠжҲ‘з»‘еҲ°иҝҷйҮҢ пјҢ жҲ‘зҲёжҲ‘еҰҲдёҚеҗҢж„Ҹзҡ„ гҖӮ еҚідҪҝжҲ‘жңүз—… пјҢ д№ҹдёҚиғҪжҠ“дәә пјҢ иҰҒиҮӘе·ұиҮӘж„ҝеҗғиҚҜ пјҢ жҳҜеҗ§пјҹвҖқйҫҡйңһдёҚзҹҘйҒ“ пјҢ жӯЈжҳҜеҘ№зҡ„зҲ¶жҜҚгҖҒеҘ№зҡ„зӣ‘жҠӨдәәпјҲжіЁпјҡйҫҡйңһжӮЈжңүзІҫзҘһз–ҫз—… пјҢ жҳҜйҷҗеҲ¶ж°‘дәӢиЎҢдёәиғҪеҠӣдәә пјҢ жүҖд»ҘжҲҗе№ҙеҗҺд»Қжңүзӣ‘жҠӨдәәпјүеҗҢж„ҸеҘ№е…ҘйҷўжІ»з–—зҡ„ гҖӮ еҸӘжҳҜиҖҒдёӨеҸЈжҖ•еҘіе„ҝи®°жҒЁ пјҢ дёҚж•ўзӣҙиҜҙ гҖӮеҘ№иҜҙ пјҢ 2009е№ҙ6жңҲ пјҢ еҘ№иў«дёҖдёӘеҸ«жқҺж–Ңзҡ„зҪ‘еҸӢејәеҘёдәҶ гҖӮвҖңжҲ‘е’ҢжқҺж–ҢеңЁдёҖдёӘд»Җд№ҲејҖеҝғзҫӨйҮҢи®ӨиҜҶ пјҢ еҗҺжқҘдёҖиө·еҸӮеҠ зәҝдёӢжҙ»еҠЁ гҖӮ з»“жқҹд№ӢеҗҺ пјҢ д»–иҜҙд№ҹеҫҖиҝҷиҫ№иө° пјҢ йҖҒдёҖдёӢжҲ‘ пјҢ еҗҺжқҘеҸҲиҜҙд»Җд№Ҳж—¶й—ҙеҫҲжҷҡ пјҢ ејҖдёҖдёӘжҲҝ пјҢ жңҖеҗҺдёҖзӣҙжӢ– пјҢ е°ұеңЁжҲҝй—ҙдҫөзҠҜжҲ‘дәҶ гҖӮ вҖқйҫҡйңһеқҡз§°еҪ“ж—¶е°ұжҠҘиӯҰдәҶ пјҢ иҜҙд№ҹжІЎжғіеҲ°иҮӘе·ұдјҡжҖҖеӯ• гҖӮ вҖңжҲ‘з»ҷжқҺж–ҢеҸ‘QQдҝЎжҒҜ пјҢ еҫҲеҸҠж—¶ең°йҖҡзҹҘдәҶд»– пјҢ иҜҙиҝҷе°Ҹеӯ©жҳҜд»–зҡ„ пјҢ еҗҺжқҘз»ҷд»–еҸ‘Bи¶…еӣҫзүҮ гҖӮ д»–дёҖзӣҙжІЎзҗҶжҲ‘ пјҢ жңҖеҗҺеӣһеӨҚжҲ‘ пјҢ иҜҙдҪ 全家жӯ»е…үе…ү гҖӮ вҖқйҫҡйңһиҜҙ пјҢ иҮӘе·ұжғіиҝҮжү“жҺүеӯ©еӯҗ пјҢ дҪҶиҖҪиҜҜдёҖйҳөеҗҺ пјҢ еӯ©еӯҗжңҲд»ҪеӨ§дәҶ пјҢ еҸӘиғҪз”ҹдёӢдәҶ гҖӮиҜҙиө·е’ҢзҲ¶жҜҚзҡ„е…ізі» пјҢ йҫҡйңһеҪўе®№жҳҜвҖңеҫҲеҸӨжҖӘзҡ„дёӨдёӘдәәвҖқ пјҢ еҘ№з»“иҝҮдёӨж¬Ўе©ҡ пјҢ д№ҹжІЎи®©зҲ¶жҜҚжқҘеҸӮеҠ пјҢ вҖңжҲ‘еүҚеӨ«д№ҹи§үеҫ—еҫҲйҡҫеҗҲеҫ—жқҘ пјҢ жІЎжңүйӮҖиҜ·д»–们вҖқ гҖӮиҝҷж¬ЎжҖҖеӯ•гҖҒеҢ…жӢ¬еҗҺжқҘз”ҹдә§ пјҢ йҫҡйңһйғҪжІЎе‘ҠзҹҘзҲ¶жҜҚ гҖӮ вҖңеҗҺжқҘйҳҝиҠіжқҘз…§йЎҫжҲ‘ пјҢ йҖҡзҹҘдәҶ他们 пјҢ з»“жһң他们иҜҙ пјҢ жҠҠеӯ©еӯҗдёўзҰҸеҲ©йҷўеҺ»еҗ§ гҖӮ вҖқеңЁйҫҡйңһзҡ„зңјйҮҢ пјҢ еҘ№жүҚжҳҜйӮЈдёӘдёәдә®дә®д»ҳеҮәдәҶеҫҲеӨҡзҡ„дәә пјҢ вҖңжҲ‘з”ҡиҮіи®©жҲ‘еӨ§е„ҝеӯҗйғҪиҫҚеӯҰдәҶ гҖӮ жҲ‘们еҸӘжңүи·іжҘјзҡ„и·ҜдәҶ пјҢ йҡҫйҒ“зңҹиҰҒз»ҷеҲ«дәәеёҰгҖҒжҲ–иҖ…жҳҜдёўзҰҸеҲ©йҷўеҗ—пјҹвҖқйҫҡйңһиҜҙ пјҢ дә®дә®дёӨдёүеІҒж—¶еҘ№зҡ„жҜҚдәІзӘҒ然йҖ и®ҝ пјҢ вҖңжүҜж·Ў пјҢ д»ҺдёҚжқҘзҡ„ пјҢ и·‘еҲ°жҲ‘们家иҜҙиҰҒеҖҹй’ұз»ҷжҲ‘们用 пјҢ 然еҗҺеҸ«жҲ‘еӨ§е„ҝеӯҗеёҰдёҠз”өи„‘ пјҢ еҺ»дәҶеҘ№е®¶ гҖӮ вҖқйӮЈд№ӢеҗҺзҡ„дәӢеңЁйҫҡйңһйӮЈйҮҢжө“зј©жҲҗдёҖж®өвҖңжӮІжғЁз»ҸеҺҶвҖқвҖ”вҖ”вҖңиҝҮдёҚдәҶеӨҡд№… пјҢ е°ұжҠҠжҲ‘жҠ“зІҫзҘһз—…йҷўеҺ»дәҶ пјҢ иҝҳжҠҠжҲ‘еӨ§е„ҝеӯҗиө¶еҲ°еӨ§иЎ—дёҠ гҖӮ вҖқйҫҡйңһжҢҮзҡ„жҳҜ2012е№ҙ пјҢ йҫҡйңһжӣҫиў«йҖҒжқҘзІҫзҘһз—…йҷўжІ»з–—иҝҮдёҖж¬Ў гҖӮ йҫҡйңһи§үеҫ—жҳҜзҲ¶жҜҚе…Ҳи®ҫеұҖгҖҒжҠҠеҘ№иҜ“еӣһ家 пјҢ 然еҗҺжҠ“еҘ№еҺ»еҢ»йҷў гҖӮ вҖңжҲ‘и§үеҫ—жҲ‘жҜ”еҫҲеӨҡдәәйғҪејәвҖқ пјҢ еҘ№ејәи°ғ пјҢ вҖңжҲ‘иҝҮеҺ»жҳҜжңүе·ҘдҪңзҡ„ пјҢ еңЁй…’еә—гҖҒеңЁж—…иЎҢзӨҫйғҪе·ҘдҪңиҝҮ пјҢ дҪ еҸҜд»ҘеҺ»й—® пјҢ жҲ‘е№Іеҫ—еҫҲеҘҪ пјҢ иҝҳз»ҷжҲ‘еҳүеҘ– гҖӮ вҖқйҫҡйңһиҮӘз§°еңЁеҮ д»Ҫе·ҘдҪңдёӯйғҪеҫҲжӢ”е°– пјҢ дҪҶжҲ‘жІЎжңүжүҫеҲ°д»»дҪ•дёҖдҪҚеҘ№иҝҮеҺ»зҡ„еҗҢдәӢиғҪз»ҷеҘ№иҜҒе®һ гҖӮ з”ҡиҮіеңЁжңҖеҗҺдёҖдёӘе·ҘдҪңеҚ•дҪҚ пјҢ йҫҡйңһеҲ°еә•жҳҜжҖҺд№ҲвҖңйҖҖеҮәвҖқзҡ„ пјҢ йғҪеҫҲйҡҫиҜҙжё…вҖ”вҖ”еҘ№жҜҚдәІиҜҙ пјҢ йҫҡйңһжҳҜеӣ дёәиЎҢдёәејӮеёёйҒӯдәәи§ЈйӣҮпјӣйҫҡйңһиҮӘе·ұеҚҙиҜҙ пјҢ еҘ№жҳҜдёәдәҶз…§йЎҫеӯ©еӯҗ пјҢ ж— еҘҲеҠһдәҶвҖңеҶ…йҖҖвҖқ пјҢ жҜҸдёӘжңҲжӢҝдёҖзӮ№йҖҖдј‘йҮ‘ гҖӮ2012е№ҙеә• пјҢ йҫҡйңһеҺ»еҢ»йҷўжІ»з–—дәҶдёӨдёӘжңҲ пјҢ е°ұеҮәдәҶйҷў гҖӮйҫҡйңһеқҡз§° пјҢ еҘ№жІЎжғізҰҒй”ўдә®дә® гҖӮ д»Һ2016е№ҙејҖе§Ӣ пјҢ зӨҫеҢәдәәе‘ҳйў‘йў‘дёҠй—Ё пјҢ еҘ№еҝғз”ҹжҒҗжғ§ гҖӮвҖңдёҖдёӘжҳҹжңҹжқҘдёҖи¶ҹ пјҢ дёҖдёӘжңҲе°ұжҳҜ4и¶ҹ пјҢ дёҖе№ҙе°ұжҳҜ4Г—11=44ж¬ЎпјҲйҫҡйңһи®ӨзҹҘй”ҷиҜҜпјү пјҢ жҳҜдёҚжҳҜпјҹдёҖзӣҙиҜҙе°Ҹеӯ©дёҚиҜ»д№ҰжҳҜеӨ§дәӢ пјҢ еӨ§дәәжҳҜзҷ«еӯҗиҰҒжҠ“еҢ»йҷў гҖӮ жҲ‘иҝҳиғҪеёҰд»–еҮәеҺ»еҗ—пјҹжҲ‘иҮӘе·ұиғҪеҮәеҺ»еҗ—пјҹвҖқиҮідәҺе Ҷз§ҜйӮЈд№ҲеӨҡжқӮзү© пјҢ йҫҡйңһиҜҙеҘ№еҺҹжң¬жғіеҒҡдәӣе°Ҹз”ҹж„Ҹиөҡй’ұ пјҢ вҖңдёүеқ—дә”еқ—ең°д№°жқҘ пјҢ дә”еқ—еҚҒеқ—ең°еҚ–еҮәеҺ» гҖӮ вҖқеҗҢж ·еӣ дёәдёҚж•ўеҮәй—Ё пјҢ з”ҹж„ҸжІЎжі•еҒҡдәҶ пјҢ д№ҹжІЎжі•ж•ҙзҗҶ гҖӮ еҸӘжҳҜеҘ№иҝҳеңЁдёҖзӣҙдёҚеҒңең°д№° гҖӮ вҖңжҲ‘д№°зҡ„йӮЈдәӣйғҪеҫҲдҫҝе®ңзҡ„ пјҢ д№ҹжҳҜиҰҒз”Ёзҡ„ гҖӮ вҖқеҘ№жңүдәӣйҖҖдј‘йҮ‘ пјҢ иҝҳжңүж®Ӣз–ҫиЎҘеҠ© пјҢ дҪҶдёҚеӨҡ гҖӮ еҫҲеӨҡдёңиҘҝжҳҜеҘ№з”ЁвҖңиҠұе‘—вҖқд№°зҡ„ гҖӮ вҖңдҪ 们еҸҜеҚғдёҮеҲ«еј„д№ұдәҶ гҖӮ жңүдәӣжІЎзЎ®и®Ө收иҙ§зҡ„ пјҢ еҰӮжһңжү”дәҶ пјҢ еҲ°ж—¶еҖҷиҠұе‘—иҰҒжүЈй’ұжҖҺд№ҲеҠһ гҖӮ иҰҒеј„д№ұдәҶ пјҢ жҲ‘жӯ»з»ҷдҪ 们зңӢ гҖӮ вҖқе’ҢеҘ№иҜҙйҒ“зҗҶиҜҙдёҚеӨӘйҖҡвҖ”вҖ”жҲ‘иҜҙ пјҢ еҚідҫҝжҳҜз”ЁиҠұе‘—д№°зҡ„ пјҢ еҫҲеӨҡдёӨдёүе№ҙеүҚзҡ„еҝ«йҖ’иӮҜе®ҡж—©е·ІжүЈиҝҮж¬ҫ пјҢ иҝҮжңҹдәҶдёәд»Җд№ҲдёҚжү”пјҹеҘ№зҡ„и„ёдёҠеҶҷж»ЎжӢ’з»қ пјҢ вҖңдёҚиҰҒ пјҢ зӯүжҲ‘еҮәеҺ» пјҢ жҲ‘иҮӘе·ұжқҘеӨ„зҗҶ гҖӮ вҖқеңЁйҫҡйңһзҡ„йҖ»иҫ‘йҮҢ пјҢ зӨҫеҢәе·ҘдҪңдәәе‘ҳзҡ„йӘҡжү°жҳҜеӣ пјҢ еҘ№зҡ„иЎҢдёәжҳҜжһң гҖӮвҖңз”·зҡ„еӨ§е®¶дёҚеҺ»з®Ў пјҢ еҸҚиҖҢдёҖзӣҙиҜҙжҲ‘жҳҜзҷ«еӯҗ гҖӮ дёәд»Җд№ҲиҰҒеҢ…еәҮејәеҘёзҠҜпјҹвҖңдёәд»Җд№Ҳд№ӢеүҚдёҚжқҘе…іеҝғжҲ‘пјҹд№ӢеүҚжҲ‘们家йӮЈд№Ҳиҙ«еӣ°жқҘиҝҮеҗ—пјҹзҺ°еңЁжңүд»Җд№Ҳиө„ж ји·ҹжҲ‘иҜҙиҝҷдәӣ пјҢ жҲ‘еҸҲжІЎиҷҗеҫ…жҲ‘еӯ©еӯҗ гҖӮвҖңе°Ҹеӯ©йғҪжё…жҘҡ пјҢ зҹҘйҒ“жҲ‘们家没зҲёзҲёгҖҒжІЎжңүй’ұ пјҢ йӘҡжү°жҲ‘们е°ұжҳҜдҫөзҠҜжҲ‘们зҡ„дәәжқғгҖҒеұ…дҪҸжқғ гҖӮ д»–иҜҙеҸ«д»–们ж»ҡ гҖӮ вҖқеңЁжҲ‘иЎЁзӨәеҘ№еҸҜиғҪеӨёеӨ§дәҶиҝҷз§ҚвҖңжҒҗжғ§вҖқж—¶ пјҢ еҘ№ж‘Үж‘ҮеӨҙ пјҢ вҖңжҲ‘и§үеҫ—дҪ еҸҜиғҪдёҚжҮӮ пјҢ жІЎеҗғиҝҮиӢ№жһңе°ұдёҚзҹҘйҒ“иӢ№жһңзҡ„е‘ійҒ“ гҖӮ зЎ®зЎ®е®һе®һеҘҪжҒҗжҖ–зҡ„ пјҢ жҲ‘дёҖдёӘдәәеёҰзқҖе°Ҹеӯ©еӯҗ пјҢ дёүеӨ©дёӨеӨҙеҮ еҚҒдёӘдәәжқҘвҖҰвҖҰдёҖзӣҙжҙ»еңЁжҒҗжғ§дёӯ гҖӮ жҲ‘жғіиҝҮжӯ»еҘҪеӨҡж¬Ў гҖӮ иҰҒдёҚдёәе„ҝеӯҗ пјҢ жҲ‘ж—©е°ұжӯ»дәҶ гҖӮ вҖқеҢ»з”ҹпјҡжҳҜзІҫзҘһеҲҶиЈӮз—Ү пјҢ д»ҘеҰ„жғідёәдё» пјҢ иЎҢдёәзҙҠд№ұзӨҫеҢәе·ҘдҪңдәәе‘ҳе’Ңйҫҡйңһжү“дәӨйҒ“зҡ„з»ҸеҺҶжҜ”жҲ‘еӨҡ пјҢ д»ҺдёҖејҖе§Ӣйҡ”зқҖзӘ—жҲ· пјҢ еҲ°еҗҺжқҘйқўеҜ№йқўиҜҙиҜқ пјҢ вҖңеҘ№дјҡжўізҗҶе№ІеҮҖгҖҒжү“жү®дёҖдёӢ пјҢ жҜ”еҰӮеӨҸеӨ©з©ҝдёӘиЈҷеӯҗеҮәжқҘ гҖӮ иҖҢдё”еҘ№еҫҲиғҪиҜҙвҖқ гҖӮ 他们д№ҹдёҚж•ўжҺүд»ҘиҪ»еҝғ гҖӮ2016е№ҙ пјҢ зӨҫеҢәж°‘иӯҰз»ҷдә®дә®дёҠжҲ·еҸЈд№ӢеҗҺ пјҢ еҫҲеҝ«жҺҘеҲ°дәҶжҠ•иҜү гҖӮ жҳҜйҫҡйңһжӢЁжү“дәҶеёӮй•ҝзғӯзәҝ пјҢ еҸҚжҳ ж°‘иӯҰеҠһзҗҶжҲ·еҸЈзЁӢеәҸиҝқжі• гҖӮ вҖңеҘ№и®ӨдёәдёҠжҲ·еҸЈжІЎжңүйҖҡиҝҮеҘ№ пјҢ е°ұжҳҜдёҚеҗҲзҗҶдёҚеҗҲжі• гҖӮ вҖқзӨҫеҢәж°‘иӯҰд№ӢеҗҺеҶҷдәҶж•°д»ҪжЈҖжҹҘ пјҢ иҜҰз»ҶдәӨд»ЈдәҶж•ҙдёӘиҝҮзЁӢ пјҢ жүҚиҝҮдәҶе…і гҖӮ2019е№ҙ пјҢ еҪ“е·ҘдҪңз»„еҲ¶е®ҡж–№жЎҲ пјҢ еҢәж°‘ж”ҝеұҖжҸҗиө·иҜүи®јеҗҺ пјҢ йҫҡйңһжқҘеҲ°дәҶж°‘ж”ҝеұҖеұҖй•ҝзҡ„еҠһе…¬е®Ө гҖӮ ж°‘ж”ҝеұҖеұҖй•ҝеӣһеҝҶ пјҢ вҖңеҘ№еҪ“ж—¶еҜ№жі•йҷўд»Ӣе…ҘжҢәйңҮж’ј пјҢ и§үеҫ—жҳҜеҠЁзңҹж јзҡ„дәҶ гҖӮ жҲ‘е°ұй—®еҘ№ пјҢ дҪ жңүд»Җд№Ҳжү“з®— гҖӮ еҘ№иҝҳжҳҜиҜҙ пјҢ еҮҶеӨҮеёҰе„ҝеӯҗеҺ»еҒҡйүҙе®ҡ гҖӮ еҘ№еҫҲеҒҘи°Ҳ пјҢ дҪҶе°ұжҳҜдёҖж №зӯӢ гҖӮ вҖқжі•йҷўз¬¬дёҖж¬ЎејҖеәӯ пјҢ йҫҡйңһжІЎеҲ°еңә пјҢ еҗҺжқҘеҘ№еҸ‘зҹӯдҝЎз»ҷжі•е®ҳ пјҢ иҜҙиҮӘе·ұеҸ‘зғ§з”ҹз—…дәҶпјӣ第дәҢж¬ЎејҖеәӯ пјҢ жі•йҷўйҖҡзҹҘеҘ№йўҶдј зҘЁ пјҢ еҘ№жІЎжңүеҺ» пјҢ жңҖеҗҺжі•е®ҳе°Ҷдј зҘЁйҖҒиҫҫеҲ°йҫҡйңһ家 гҖӮ вҖңд№ӢеҗҺеҘ№з»ҷжҲ‘еҸ‘зҹӯдҝЎ пјҢ иҜҙйҖҒиҫҫе°ұж”ҫ家门еҸЈ пјҢ дёўдәҶжҖҺд№ҲеҠһ гҖӮ вҖқжі•е®ҳз»ҷжҲ‘зңӢйҫҡйңһеҸ‘жқҘзҡ„зҹӯдҝЎ пјҢ жҜҸжқЎйғҪеҫҲй•ҝ пјҢ жҜ”еҰӮвҖ”вҖ”вҖңдҪ жҠҠдј зҘЁдёўеңЁжҲ‘们家门еҸЈйҒ—еӨұдәҶ пјҢ еҸҜжҳҜдҪ иҙҹиҙЈд»» гҖӮ жүҖи°“зҡ„жі•еҫӢ пјҢ жҳҜе…ЁеӣҪдәәеӨ§д»ЈиЎЁејҖдјҡеҲ¶е®ҡзҡ„ гҖӮ вҖқвҖңдәӢеңЁдәәдёә гҖӮ дё–дёҠж— йҡҫдәӢгҖҒеҸӘиҰҒиӮҜзҷ»ж”Җ гҖӮ еҸӘиҰҒжҲ‘жҳҜеҜ№зҡ„ пјҢ жҲ‘д»Җд№ҲйғҪдёҚжҖ• гҖӮ вҖқвҖңжң¬дәәзҡ„е·ҘдҪңиЎЁзҺ°е’ҢиғҪеҠӣ пјҢ еҸҜжҳҜиў«жҹҗеҚ•дҪҚз§°дёәжңҖеҗҺдёҖеј зҺӢзүҢ гҖӮ дҪ жңҖеҘҪжҳҜдәҶи§ЈдёҖдёӢ пјҢ еҶҚеҶіе®ҡжҖҺд№ҲеҜ№еҫ…жҲ‘д№ҹдёҚиҝҹ гҖӮ вҖқвҖҰвҖҰйҫҡйңһе§Ӣз»ҲеңЁиҮӘе·ұзҡ„йҖ»иҫ‘йҮҢжү“иҪ¬ гҖӮвҖңеҘ№жӮЈзҡ„жҳҜзІҫзҘһеҲҶиЈӮз—Ү пјҢ д»ҘеҰ„жғідёәдё» пјҢ е…¶дёӯиў«е®іеҰ„жғіжҳҺжҳҫ пјҢ иЎҢдёәзҙҠд№ұ гҖӮ вҖқйҫҡйңһзҡ„дё»жІ»еҢ»з”ҹеҜ№еҘ№еҸЈдёӯзҡ„вҖңеҲ«дәәжғіжҠ“жҲ‘вҖқиҝҷдёҖиҜҙ法并дёҚйҷҢз”ҹ гҖӮ йҫҡйңһеҲҡе…Ҙйҷўж—¶иЎЁзҺ°жӣҙз”ҡ пјҢ вҖңеҘ№и§үеҫ—жүӢжңәд№ҹиў«зӣ‘жҺ§дәҶ пјҢ дёҚиғҪз”Ё пјҢ д№ҹдёҚж•ўеҮәй—Ё пјҢ и§үеҫ—жңүдәәиҰҒж—¶ж—¶еҲ»еҲ»еҜ№еҘ№е’Ңе°Ҹеӯ©иҝ«е®і гҖӮ вҖқз–ҫз—…дҪҝйҫҡйңһзҡ„зӨҫдјҡеҠҹиғҪеҸ—еҲ°еҪұе“Қ пјҢ вҖңиҖҢдё” пјҢ дёҚе…үеҪұе“ҚеҲ°еҘ№жң¬дәә пјҢ иҝҳеҪұе“ҚеҲ°еҘ№е°Ҹеӯ© пјҢ ж—Ҙеёёз”ҹжҙ»жІЎжі•жӯЈеёёиҝӣиЎҢ гҖӮ вҖқеҢ»з”ҹзҡ„жІ»з–—д»ҘиҚҜзү©дёәдё» пјҢ иҖҢдё”еүӮйҮҸеҒҸеӨ§ гҖӮ вҖңеҘ№дёҖзӣҙдёҚеӨӘй…ҚеҗҲ пјҢ еҲҡејҖе§Ӣз”Ёй’ҲеүӮ пјҢ еҗҺжқҘй…ҚеҗҲеҸЈжңҚиҚҜзү© гҖӮ д»ҺиҝҷдёҖдёӘеӨҡжңҲиҜ„дј° пјҢ еҘ№жҒўеӨҚеҫ—дёҚз®—зү№еҲ«зҗҶжғі пјҢ еҸӘжҳҜйғЁеҲҶеҘҪиҪ¬ гҖӮ жңҖе…ій”®зҡ„жҳҜ пјҢ еҘ№еҜ№иҮӘиә«з–ҫз—…зҡ„дёҖдёӘи®ӨиҜҶвҖ”вҖ”д№ҹе°ұжҳҜжҲ‘们иҜҙзҡ„вҖҳиҮӘзҹҘеҠӣвҖҷвҖ”вҖ”иҝҳжІЎжңүжҒўеӨҚ гҖӮ еҘ№зҺ°еңЁдёҚеҶҚи§үеҫ—иҮӘе·ұзҡ„дёҖиЁҖдёҖиЎҢеҸ—еҲ°зӣ‘жҺ§ пјҢ дҪҶиҝҳжҳҜдјҡиҜҙдёҚе®үе…Ё гҖӮ вҖқжҲ‘й—®еҢ»з”ҹ пјҢ зІҫзҘһз–ҫз—…йҡҫйҒ“д№ҹжңүдёҖе®ҡзҡ„жҪңдјҸжңҹеҗ—пјҹдёәд»Җд№ҲйҫҡйңһеңЁиҝҷеҮ е№ҙйҮҢиЎҢдёәејӮеёёжҳҺжҳҫпјҹеҢ»з”ҹиҜҙ пјҢ дёҚжҳҜжҪңдјҸжңҹ пјҢ иҖҢжҳҜз–ҫз—…е…·жңүжіўеҠЁжҖ§жҲ–иҖ…иҜҙдёҚзЁіе®ҡжҖ§ гҖӮ вҖңе®ғеҸҜиғҪйҖҡиҝҮжІ»з–—еҘҪдәҶдёҖж®өж—¶й—ҙ пјҢ жҲ–иҖ…дёҚжІ»з–—д№ҹдјҡжңүж®өж—¶й—ҙеҘҪдёҖдәӣ гҖӮ иҝҷжҳҜз–ҫз—…иҮӘиә«зҡ„жіўеҠЁ гҖӮ вҖқиҖҢд»ҺиҝҷдёҖж¬ЎзңӢ пјҢ еҢ»з”ҹеҲӨж–ӯйҫҡйңһвҖңеүҚеүҚеҗҺеҗҺдёҚеӨӘеҘҪ пјҢ иҮіе°‘дёүе№ҙеӨҡж—¶й—ҙвҖқ гҖӮ жҳҫ然 пјҢ йҫҡйңһ2012е№ҙйӮЈж¬ЎеҮәйҷўеҗҺ пјҢ жІЎжңү规еҫӢең°еқҡжҢҒз”ЁиҚҜ гҖӮжҲ‘й—®дәҶеҢ»з”ҹжңҖеҗҺдёҖдёӘй—®йўҳ пјҢ иҝҷз§Қз–ҫз—…жҳҜйҒ—дј жҖ§зҡ„еҗ—пјҹеҢ»з”ҹиҜҙ пјҢ зңӢжҰӮзҺҮ гҖӮеӨ–е©ҶпјҡдёҚжҳҜжҲ‘们дёҚж„ҝж„Ҹз®Ў пјҢ е°ұжҖ•вҖңжҝҖеҢ–зҹӣзӣҫвҖқвҖңжҲ‘дј°и®ЎиҝҷдёӘз—… пјҢ дј еҘідёҚдј з”· гҖӮ вҖқйҫҡйңһзҡ„жҜҚдәІеқҗеңЁжҲ‘еҜ№йқў гҖӮ иҝҷдёӘе…«ж—¬иҖҒдәә收жӢҫеҫ—е№ІеҮҖеҲ©зҙў пјҢ иө°еңЁиЎ—дёҠеә”иҜҘд№ҹжҳҜи¶іеӨҹиў«з§°иөһжҳҜдҪ“йқўзҡ„ гҖӮйҫҡйңһзҡ„зҲ¶дәІиҖіжңөиғҢ пјҢ жӣҙеӨҡж—¶еҖҷжҲ‘жҳҜе’Ңйҫҡйңһзҡ„жҜҚдәІиҒҠ гҖӮ дёӨдҪҚиҖҒдәәз”ҹиӮІдәҶдёҖе„ҝдёҖеҘі пјҢ еҘіе„ҝйҫҡйңһд»Һе°Ҹе°ұе’Ң他们дёҚдәІ пјҢ зӯүдәҢеҚҒжқҘеІҒиҮӘе·ұжҲҗдәҶ家 пјҢ е’ҢзҲ¶жҜҚд»ҘеҸҠе“Ҙе“Ҙ家е°ұеҮ д№ҺжІЎжңүиө°еҠЁ гҖӮ иҷҪ然еҗҢеңЁдёҖдёӘеҹҺеёӮ пјҢ дҪҶжӯӨеүҚзҲ¶дәІж‘”и·ӨйӘЁжҠҳдәҶ пјҢ йҫҡйңһд№ҹжІЎеҺ»иҝҮеҢ»йҷўдёҖж¬Ў гҖӮйҫҡйңһжңүиҝҮдёӨж¬Ўе©ҡ姻 пјҢ еҲҶеҲ«еңЁ1988е№ҙз”ҹдёӢеҘіе„ҝгҖҒ1995е№ҙз”ҹдёӢе„ҝеӯҗйҳҝдјҹ гҖӮ вҖңдёәд»Җд№ҲжҲ‘иҜҙдј еҘі пјҢ еӣ дёәзҺ°еңЁеҘ№зҡ„еӨ§еҘіе„ҝд№ҹжңүй—®йўҳ пјҢ еҘҪеғҸзІҫзҘһдёҚеӨӘжӯЈеёё пјҢ йҳҝдјҹе°ұжІЎдәӢ гҖӮ вҖқиҖҒдәәиҜҙ пјҢ йҫҡйңһзҡ„еӨ§еҘіе„ҝе·Із»Ҹе«ҒдәәдәҶ пјҢ дҪҶеҗ¬иҜҙзІҫзҘһзҠ¶еҶөд№ҹдёҚеӨӘеҘҪ гҖӮ иҝҷдәӣе№ҙ пјҢ йҫҡйңһдёҖзӣҙеёҰзқҖе„ҝеӯҗйҳҝдјҹзӢ¬иҮӘеңЁеӨ–з§ҹдҪҸ гҖӮ2010е№ҙ3жңҲ пјҢ дә®дә®еҮәз”ҹдәҶ пјҢ вҖңжҳҜйҳҝиҠіжү“з”өиҜқжқҘиҜҙзҡ„ гҖӮ жҲ‘жңүеҘҪеҮ еӨ©жІЎзқЎзқҖ пјҢ д№°дәҶеҸӘйёЎ пјҢ еүҒзўҺ пјҢ и®©еӨ§еӨ–еӯҷйҳҝдјҹжӢҝеҺ» пјҢ жҲ‘жІЎеҺ»зңӢеҘ№ гҖӮ вҖқз”ұдәҺеӨҡе№ҙжІЎжңүеҫҖжқҘ пјҢ йҫҡйңһзҡ„е“Ҙе“Ҙд№ҹеҸҚеҜ№зҲ¶жҜҚеҶҚеҺ»з®Ўйҫҡйңһ гҖӮеҸҲиҝҮдәҶдёӨе№ҙ пјҢ йҫҡйңһжҜҚдәІиҝҳжҳҜдёҚж”ҫеҝғ пјҢ жүҫеҺ»дәҶеҮәз§ҹеұӢ гҖӮ вҖңжһң然 пјҢ жҲ‘зңӢеҲ°йӮЈдёӘжҲҝеӯҗеҘҪи„ҸеҘҪд№ұ гҖӮ дёүдёӘдәәзқЎдёҖдёӘй“ә пјҢ дёңиҘҝйғҪжҳҜй»‘й»‘зҡ„ гҖӮ вҖқиҖҒдәәжӣҙж”ҫеҝғдёҚдёӢзҡ„жҳҜе°ҸеӨ–еӯҷдә®дә® гҖӮ вҖңжҲ‘еҪ“ж—¶зңӢеҲ°д»– пјҢ еӣӣиӮўеҫҲз»ҶиӮҡеӯҗеҫҲеӨ§ пјҢ дёҖзңӢе°ұжҳҜдёҚжӯЈеёёйҘ®йЈҹеҜјиҮҙзҡ„ пјҢ д»–еҸҜиғҪжІЎжҖҺд№ҲеҗғеҘ¶ гҖӮ жҲ‘еҗ¬еӨ§еӨ–еӯҷпјҲйҳҝдјҹпјүиҜҙ пјҢ йҫҡйңһжӢҝеҗғзҡ„жү“жҲҗзІү пјҢ 然еҗҺз…®зҶҹ пјҢ д№ҹдёҚдёҖеӢәеӢәе–Ӯдә®дә® пјҢ е°ұз”ЁдёӘжјҸж–—еҜ№зқҖд»–еҳҙ пјҢ жјҸдёӢеҺ»зҡ„ гҖӮ жҲ‘еҺ»зҡ„ж—¶еҖҷ пјҢ зңӢеҲ°зҡ„е°ұжҳҜйҳҝдјҹзңӢзқҖз”өи„‘ пјҢ жҠұзқҖе°Ҹеӯ© пјҢ йҫҡйңһиәәзқҖдј‘жҒҜ гҖӮ вҖқиҖҒдәәеӣһ家еҗҺ пјҢ еҒҡдё»жҠҠйҫҡйңһжҺҘеӣһиә«иҫ№еҗҢдҪҸ гҖӮ вҖңдҪҶеҘ№жҜҸеӨ©йғҪи·ҹжҲ‘们дҪңеҜ№ пјҢ иҝҳи·ҹеҘ№еӨ§е„ҝеӯҗжү“жһ¶ гҖӮ жҲ‘们иҰҒзқЎи§үдәҶ пјҢ еҘ№еҸҲеҸ«е°Ҹе„ҝеӯҗи·‘жҲ‘们жҲҝй—ҙжқҘ гҖӮ вҖқжӯӨеүҚзҲ¶жҜҚдёҖзӣҙд»ҘдёәйҫҡйңһвҖңз”ҹжҙ»д№ жғҜдёҚеҘҪвҖқ пјҢ еҗҢдҪҸеҗҺ пјҢ з§Қз§ҚејӮеёёе·Із»ҸдёҚиғҪз”ЁвҖңд№ жғҜдёҚеҘҪвҖқжқҘи§ЈйҮҠ гҖӮ 他们ејҖе§Ӣж„ҸиҜҶеҲ° пјҢ йҫҡйңһзІҫзҘһжңүй—®йўҳ гҖӮвҖңжҲ‘йӮЈдәӣеҗҢдәӢиҜҙ пјҢ дҪ еҲ«дёҚиҲҚеҫ—иҠұй’ұ пјҢ иҰҒйҖҒеҘ№еҺ»зІҫзҘһз—…йҷў гҖӮ жңҖеҗҺжҲ‘们и·ҹжҙҫеҮәжүҖеҸҚжҳ пјҢ 他们жҙҫдәҶдёҖдёӘеҚҸиӯҰ пјҢ жңүеӨ©жҷҡдёҠжӢҝдәҶдёӘз»іеӯҗжқҘжҚҶеҘ№ пјҢ йҖҒеҘ№еҺ»еҢ»йҷўдәҶ гҖӮ вҖқ2012е№ҙйҫҡйңһиў«йҖҒеҺ»дҪҸйҷў пјҢ дёӨдёӘеӯ©еӯҗйғҪз”ұиҖҒдәәз…§йЎҫ гҖӮ иҖҒдәәиҜҙ пјҢ 他们дәӢе…ҲиҜ·еҘҪдәҶдҝқе§Ҷ пјҢ йҫҡйңһиө°зҡ„йӮЈжҷҡ пјҢ дҝқе§Ҷе°ұжқҘдәҶ гҖӮвҖңдә®дә®иҝҳдёҚжҮӮеҫ—еҸ«еҰҲеҰҲ пјҢ йӮЈдёӘдҝқе§Ҷж•ҷд»– пјҢ иҫ№иө°иҫ№ж•ҷ гҖӮ еёҰдәҶеҮ дёӘжңҲд№ӢеҗҺ пјҢ еӯ©еӯҗе°ұй•ҝеҫ—еҘҪиғ– пјҢ и…ҝиҝҷд№ҲзІ— пјҢ еҘҪз»“е®һ пјҢ еңЁж“ҚеңәйҮҢйқўжү“зҗғгҖҒи·‘жӯҘ гҖӮ вҖқиҖҒдәәиҫ№иҜҙиҫ№жҜ”еҲ’ гҖӮйҫҡйңһеҮәйҷўеҗҺ пјҢ дҝқе§Ҷиө°дәҶ пјҢ еҘ№йҮҚж–°иҮӘе·ұеёҰеӯ©еӯҗ гҖӮ зҲ¶жҜҚеңЁеҗҢе°ҸеҢәз§ҹдёӢдёҖеҘ—жҲҝеӯҗ пјҢ дёҚз”ЁеҗҢдҪҸ пјҢ дҪҶзҰ»еҫ—иҝ‘ гҖӮ вҖңжҲ‘её®еҘ№д№°иҸңгҖҒеҒҡйҘӯ гҖӮ еҘ№жҜҸеӨ©еҲ°жҲ‘们йӮЈиө°дёҖж¬Ў гҖӮ жҲ‘дё“й—Ёз”ЁдёҖдёӘжң¬еӯҗи®° пјҢ йқ’иҸңеӨҡе°‘й’ұ пјҢ зҢӘиӮүеӨҡе°‘й’ұ пјҢ и®°еҪ•еҘҪ пјҢ жҜҸдёӘжңҲеҘ№жқҘз»“иҙҰ гҖӮ вҖқжҲ‘й—® пјҢ дёәд»Җд№ҲйҫҡйңһдёҚиҮӘе·ұеҒҡйҘӯпјҹйҫҡйңһзҡ„жҜҚдәІж’Үж’Үеҳҙ пјҢ вҖңжҲ‘е“Әе„ҝзҹҘйҒ“ гҖӮ жҲ‘иҝҳеҮәй’ұеё®еҘ№жү“дәҶдёҖдёӘзҒ¶ гҖӮ еҘ№з…®дәҶеҮ еӨ©е°ұдёҚеҒҡдәҶ пјҢ жҲ‘д№ҹжІЎжңүиҝҪй—® гҖӮ иҝҷж¬ЎжҲ‘иҝӣеұӢ пјҢ жүҚзҹҘйҒ“иҝҷйҮҢйқўжҗһеҫ—дёҖеЎҢзіҠж¶Ӯ гҖӮ вҖқйҫҡйңһзҡ„жҜҚдәІд№ҹжІЎиө°иҝӣиҝҮдёәеҘіе„ҝз§ҹзҡ„жҲҝеӯҗйҮҢ гҖӮ еҘ№иҜҙ пјҢ дёҚжҳҜеҘ№дёҚж„ҝж„Ҹ пјҢ жҳҜжңүдёҖж¬ЎеҘ№и¶ҒзқҖйҫҡйңһејҖй—Ёж—¶еҮ‘дёҠеүҚ пјҢ з»“жһңйҫҡйңһз»ҷдәҶеҘ№дёҖдёӘиҖіе…үвҖ”вҖ”еҸҢж–№д№ҹд№ жғҜдәҶиҝҷз§ҚзӣёеӨ„жЁЎејҸвҖ”вҖ”йҫҡйңһжҜҸжҷҡе…«д№қзӮ№еҺ»зҲ¶жҜҚйӮЈйҮҢеҗғйҘӯ гҖӮ вҖңеҘ№дёҖеӨ©е°ұеҗғиҝҷдёҖйЎҝ гҖӮ еҗғдёҚе®Ңзҡ„еёҰиө° пјҢ 第дәҢеӨ©зғӯдёҖдёӢ гҖӮ вҖқеҺ»зҲ¶жҜҚйӮЈйҮҢ пјҢ йҫҡйңһд»ҺжІЎеёҰиҝҮдә®дә® пјҢ иҝһиҝҮе№ҙйғҪжІЎжңү пјҢ вҖңйғҪжҳҜеҘ№еҗғе®Ңд№ӢеҗҺ пјҢ жҲ‘们еҶҚз»ҷжү“дёҠдёҖзў— гҖӮ жүЈиӮүгҖҒиұҶи…җгҖҒдёёеӯҗ пјҢ жҲ‘жҖ»з»ҷеҘ№еӨҡеӨҡзҡ„ гҖӮ вҖқеӨ–е©ҶеҒ¶е°”д№ҹиғҪзһҘеҲ°дә®дә®зҡ„еӨ„еўғ гҖӮ вҖңжңүдёҖж¬ЎйҖҸиҝҮзӘ—жҲ· пјҢ жҲ‘зңӢеҲ°еӯ©еӯҗз«ҷеңЁеәҠдёҠ пјҢ иҝҷйҮҢжҠ“гҖҒйӮЈйҮҢжҢ пјҢ еҘҪз—’зҡ„ж„ҸжҖқ гҖӮ вҖқеҶҚе°ұжҳҜйҫҡйңһз»ҷзҲ¶жҜҚжү“з”өиҜқзҡ„ж—¶еҖҷ пјҢ дә®дә®дјҡеңЁдёҖж—ҒиҜҙеҮ еҸҘз®ҖеҚ•зҡ„иҜқ гҖӮ2016е№ҙ пјҢ еӨ–е©Ҷз»ҷдә®дә®дёҠдәҶжҲ·еҸЈ пјҢ йӮЈж¬ЎйҫҡйңһеҫҲдёҚж»Ў гҖӮ вҖңеҗҺжқҘжҠҠжҲ‘йӘӮдәҶдёҖйЎҝ гҖӮ еҘ№и®ІдҪ жҖҺд№Ҳеё®йӮЈдёӘз”·зҡ„зҡ„еҝҷ гҖӮ еҘ№зҡ„ж„ҸиҜҶжҳҜдёҚиҜҘз»ҷдә®дә®дёҠжҲ·еҸЈ пјҢ иҝҷж ·е°ұиғҪжҠҘеӨҚйӮЈдёӘз”·дәә гҖӮ вҖқдёҠжҲ·еҸЈеҗҺ пјҢ еӨ–е©ҶжҸҗеҮәиҰҒеёҰдә®дә®еҺ»дёҠеӯҰ пјҢ йҫҡйңһжІЎжӢҰзқҖ пјҢ йӮЈдёҖж¬Ў пјҢ еӨ–е©Ҷз»ҲдәҺи§ҒеҲ°дәҶдә®дә® гҖӮ вҖңд»–еӨҙеҸ‘еҫҲй•ҝ пјҢ еҘҪеғҸдёҖдёӘеҘіеӯ©еӯҗ гҖӮ жҲ‘е°ұжӢҝеүӘеҲҖ пјҢ жӢҝдёҖеқ—еӣҙеёғ пјҢ её®д»–еүӘеӨҙеҸ‘ гҖӮ вҖқеӨ–е©ҶжүҫеҲ°дёҖдёӘе°ҸеӯҰдё»д»» пјҢ еӨ®жұӮдәҶеҚҠеӨ© пјҢ жңҖеҗҺ主任让他们еёҰйҪҗиө„ж–ҷеҶҚеҺ»дёҖж¬Ў гҖӮ вҖңз»“жһңиҝҮдәҶдёӨеӨ© пјҢ йҫҡйңһе°ұдёҚеҶҚи®©еӯ©еӯҗеҮәй—ЁдәҶ гҖӮ еӣ дёәжҲ‘еёҰеҮәй—ЁйӮЈж¬Ў пјҢ еӯ©еӯҗеӣ дёәеҘҪд№…жІЎеҮәй—Ё пјҢ ж‘”дјӨдәҶеҘҪеӨҡең°ж–№ гҖӮ вҖқиҝҷ件дәӢд№ҹзЎ®е®һиў«йҫҡйңһжҸҗиө· пјҢ дҪңдёәдә®дә®дёҚйҖӮеҗҲеҮәй—Ёзҡ„еҮӯиҜҒ гҖӮдә®дә®дёҠжҲ·еҸЈд№ӢеҗҺ пјҢ йҫҡйңһеҺ»зҲ¶жҜҚйӮЈеҗғйҘӯзҡ„йў‘зҺҮйҷҚдҪҺеҲ°дёҖе‘ЁдёҖдёӨж¬Ў пјҢ иҖҒдәәд№ҹеҶҚжІЎи§ҒиҝҮдә®дә® гҖӮ дҪҶ他们дёҚж•ўеҺ»жүҫзӨҫеҢә пјҢ вҖңжҖ•жҝҖеҢ–зҹӣзӣҫвҖқ пјҢ е°ұиҝҷж ·жӢ–еҲ°2019е№ҙ гҖӮ вҖңе°Ҹеӯ©еӨӘеҸҜжҖңдәҶ гҖӮ еҰӮжһңдёҚи§Јж•‘ пјҢ еӨ©еӨ©зқЎе®¶йҮҢ пјҢ иҰҒжҠҠд»–еӣ°жӯ»дәҶ пјҢ е°ұжҳҜеҠіж”№зҠҜд№ҹиҰҒж”ҫйЈҺзҡ„ гҖӮ вҖқиҖҒдәәз»ҲдәҺеҶҚж¬ЎжұӮж•‘ гҖӮзӯүеҲӨеҶіеҗҺ пјҢ йҫҡйңһжү“з”өиҜқжқҘ пјҢ еӨ§йӘӮзҲ¶жҜҚвҖ”вҖ”вҖңдҪ 们йғҪ80еӨҡеІҒдәҶ пјҢ иҝҳиҰҒеҪ“д»Җд№Ҳзӣ‘жҠӨдәәпјҹдҪ 们иҮӘе·ұйғҪжҳҜеҝ«иҰҒжӯ»зҡ„дәәдәҶ гҖӮ вҖқйҫҡйңһжҜҚдәІд№ҹеҸ№ж°” пјҢ вҖңжҲ‘и§үеҫ—еҘ№жңүиҝҷз§Қз—… пјҢ ж—ўеҸҜжҒЁеҸҲеҸҜжҖң гҖӮ жҳҜеӨ§и„‘жҢҮеҜјеҘ№жҲҗиҝҷж ·еӯҗзҡ„ пјҢ еҘ№иҮӘе·ұжҺ§еҲ¶дёҚдәҶ гҖӮ вҖқ2012е№ҙгҖҒ2019е№ҙйҫҡйңһдёӨж¬ЎдҪҸйҷў пјҢ еҘ№зҡ„зҲ¶дәІдјҡжҜҸдёӨе‘ЁеҺ»жҺўжңӣдёҖж¬Ў гҖӮвҖңеүҚеҮ еӨ©еҘ№зҲёзҲёеҺ»зңӢ пјҢ иҜҙ пјҢ еҘ№ж”ҫиҜқдәҶ пјҢ еӣһжқҘиҰҒжқҖжҲ‘们 гҖӮ зӯүеҘ№зңҹзҡ„еӣһжқҘ пјҢ зңӢеҲ°е„ҝеӯҗд№ҹдёҚи§ҒдәҶ пјҢ жҲ‘们иҝҳжҠҠеҘ№зҡ„дёңиҘҝжҗһд№ұдәҶ гҖӮ жҲ‘дёҚж•ўжғі гҖӮ дҪ еҺ»её®жҲ‘й—®й—®еҢ»йҷў пјҢ еҘ№иғҪдёҖзӣҙдҪҸеңЁйӮЈйҮҢйқўеҗ—пјҹвҖқиЎЁе§ЁеҰҲйҳҝиҠіпјҡжҲ‘зҡ„е§җеҰ№д»¬йғҪеҠқжҲ‘ пјҢ д»ҘеҗҺеҮәдәӢдәҶжҖҺд№ҲеҠһи§Ғдә®дә®еҗҺ пјҢ жҲ‘е’Ңд»–зҡ„иЎЁе§ЁеҰҲйҳҝиҠізәҰеңЁе°ҸеҢәзҡ„ж“ҚеңәдёҠи§ҒдәҶдёҖйқў гҖӮ жҲ‘们зңӢзқҖеӯ©еӯҗ们跑жӯҘгҖҒиёўзҗғгҖҒзҺ©д№җ пјҢ д»ҺдёӢеҚҲдёҖзӣҙиҒҠеҲ°дәҶеӨңиүІжІүдёӢеҺ» гҖӮйҳҝиҠіиҜҙдәҶжӣҙеӨҡе…ідәҺйҫҡйңһзҡ„дәӢ гҖӮвҖңжҲ‘жҳҜзҰ»е©ҡеҗҺ пјҢ жүҚеӣһжқҘиҝҷдёӘеҹҺеёӮзҡ„вҖқ пјҢ йҳҝиҠіз®ЎйҫҡйңһеҸ«е§җ пјҢ вҖңе§җжІЎжңүд»Җд№ҲжңӢеҸӢ гҖӮ зӯүжҲ‘еӣһжқҘеҗҺ пјҢ еҘ№жңҖдәІзҡ„е°ұз®—жҲ‘ пјҢ жңүд»Җд№ҲдәӢеҘ№е°ұжү“з”өиҜқз»ҷжҲ‘ гҖӮ вҖқеҜ№дәҺйҫҡйңһзҡ„е©ҡ姻жғ…еҶө пјҢ йҳҝиҠіжңүиҖій—» пјҢ вҖңзҰ»е©ҡеә”иҜҘд№ҹжҳҜеӣ дёәеҘ№жңүз—… гҖӮ дҪҶеҘ№йӮЈж—¶иЎЁзҺ°жІЎиҝҷд№ҲдёҘйҮҚ пјҢ еӨ–дәәдёҚдјҡжіЁж„ҸеҲ° пјҢ дҪҶдәІиҝ‘зҡ„дәәдјҡжіЁж„Ҹ гҖӮ вҖқжҜ”еҰӮ пјҢ йҫҡйңһжҚўиҝҮеҘҪеҮ дёӘз§ҹеӨ„ пјҢ вҖңжҲ‘жҜҸж¬ЎеҺ»йғҪи§үеҫ—еҘҪд№ұ гҖӮ еұӢеӯҗжңүдёҖдёӘеёӯжўҰжҖқеәҠ пјҢ еәҠдёҠеҲ°еӨ„е Ҷж»Ў гҖӮ вҖқиҝҳжңү пјҢ йҫҡйңһеҮәй—ЁеүҚжҖ»иҰҒвҖңдёңзңӢиҘҝзңӢвҖқ гҖӮ вҖңжҲ‘еҺ»еҘ№е®¶йҮҢ пјҢ зңӢеһғеңҫжЎ¶ж»ЎдәҶ пјҢ жҲ‘е°ұиҜҙеё®еҘ№еҖ’еһғеңҫ пјҢ еҘ№жҖ»иҰҒжҠҠеһғеңҫе…ЁйғЁеҖ’еҮәжқҘгҖҒжӢҝдёӘй“ҒеӨ№еӯҗзҝ»еј„жқҘзҝ»еј„еҺ» пјҢ еҶҚеҸ«жҲ‘жӢҝеҮәеҺ»еҖ’ гҖӮ жҲ‘дёҙиө°еүҚеҘ№иҝҳиҰҒжҠҠжҲ‘е…Ёиә«ж‘ёдёҖйҒҚгҖҒзңӢдёҖйҒҚ гҖӮ вҖқ2009е№ҙ пјҢ жҖҖдә®дә®ж—¶ пјҢ йҫҡйңһе‘ҠиҜүдәҶйҳҝиҠі гҖӮ вҖңжҲ‘еҠқеҘ№еҲ«иҰҒдәҶ пјҢ еӣ дёәжҲ‘зҹҘйҒ“еҘ№дёҚжӯЈеёё пјҢ дҪ иҮӘе·ұжҳҜиҝҷж · пјҢ иҝҳиҰҒжҖҺд№Ҳз…§йЎҫеӯ©еӯҗе‘ўпјҹдҪҶеҘ№иҜҙжҳҜдёҖжқЎз”ҹе‘Ҫ пјҢ иҰҒз”ҹдёӢжқҘ гҖӮ вҖқзӣҙеҲ°2010е№ҙ3жңҲ пјҢ йҫҡйңһеҸҲжү“з”өиҜқз»ҷйҳҝиҠі пјҢ вҖңз”ҹе®ҢдәҶ пјҢ еңЁеҢ»йҷўйҮҢ пјҢ дёҖдёӘдәә пјҢ жҲ‘йҷӘеҘ№еқҗжңҲеӯҗ гҖӮ з»ҷе°Ҹеӯ©еӯҗжҙ—жҫЎ пјҢ еҒҡйҘӯз…®йқў пјҢ йғҪжҳҜжҲ‘еј„ гҖӮ жҲ‘еҠқеҘ№иҜҙдҪ иҝҷж ·дёҚиЎҢ пјҢ иҝҳжҳҜйҖҒдәәеҗ§ гҖӮ еҘ№зӯ”еә”дәҶ пјҢ жҲ‘иҝҳиҜҙеё®еҘ№еҺ»еҶңжқ‘зңӢдёҖдёӢжңүжІЎжңүдәәиҰҒ гҖӮ вҖқдҪҶд№ҹйғҪеҸӘжҳҜиҜҙиҜҙиҖҢе·І пјҢ зӯүйҫҡйңһеҮәдәҶйҷў пјҢ е°ұеҸҲдёҚи§ҒдәәдәҶ гҖӮвҖңеҶҚд№ӢеҗҺ пјҢ жҲ‘е°ұе’ҢеҘ№и§Ғйқўе°‘дәҶ пјҢ дё»иҰҒжҳҜжү“з”өиҜқ гҖӮ вҖқ
жҺЁиҚҗйҳ…иҜ»
- е…¬е®ү|3з”·еӯҗдәәй—ҙи’ёеҸ‘2дәәиў«зӮјжҲҗең°жІҹжІ№иӮүжёЈйҘјеҚ–жҺүпјҒиӯҰиҠұеҜ№е…¶жөӢи°ҺеҸ‘зҺ°зңҹзӣё
- жҪҮж№ҳжҷЁжҠҘ|3еҗҚз”·еӯҗвҖңдәәй—ҙи’ёеҸ‘вҖқпјҢе«ҢзҠҜз§°е…¶дёӯ2дәәиў«вҖңзӮјжҲҗең°жІҹжІ№е’ҢиӮүжёЈйҘјеҚ–жҺүдәҶвҖқпјҒиӯҰиҠұеҜ№е…¶жөӢи°ҺеҸ‘зҺ°зңҹзӣё
- дәәй—ҙдёЁй—№еҲ°иҝһзҲ¶жҜҚйғҪж— жі•иҗҪ葬зҡ„дәІе…„ејҹ
- дәәй—ҙдёЁ33еІҒиҫһиҒҢзҡ„е…¬еҠЎе‘ҳпјҡжҲ‘з®—жҳҜиҜҜе…Ҙжӯ§йҖ”дәҶ
- жІЎдәӢзһҺеҳҖе’•пјҢз»ҷдҪ е®ҡжӯ»зҪӘ
- е°ҸдәҶзҷҪдәҶе…”|иҫҪе®Ғж”№еҗҚеҫҲжҲҗеҠҹзҡ„еӨ§еӯҰпјҢжӣҫиў«дәәе«ҢејғпјҢеҰӮд»Ҡжҷ®йҖҡеӯҰз”ҹй«ҳж”ҖдёҚиө·
- еӨ©дёҠдәәй—ҙжўҒжө·зҺІжЎҲ
- еңЁдәәй—ҙ|жӢңзҷ»иғңйҖүеҗҺпјҢеңЁзҫҺеҚҺдәәжҖҺд№ҲзңӢпјҹ
- дёӯеҺҹдҪң家зҫӨ|зҪ—иҘҝпјҡдәәй—ҙеӨӘеұҖдҝғпјҢеӨҡз•ҷз»ҷд»–дәәдёҺиҮӘе·ұдёҖдәӣвҖңдҪҷең°вҖқпҪңеҗҚ家йҳ…иҜ»
- еӨ§зҢ«жқҘдәҶ|13еІҒз”·еӯ©еҫ’жүӢжҠҠиұ№еӯҗеҮ»йҖҖпјҢиў«дәәеҪ“жҲҗиӢұйӣ„



![[иҫ…еҠ©и®ӯз»ғ]еҲҶжё…дё»ж¬ЎпјҢиҫ…еҠ©и®ӯз»ғеҸӘиғҪжҳҜиҫ…еҠ©пјҒ](http://ttbs.guangsuss.com/image/a9e56a600a9c6f896d0b8d5345ff816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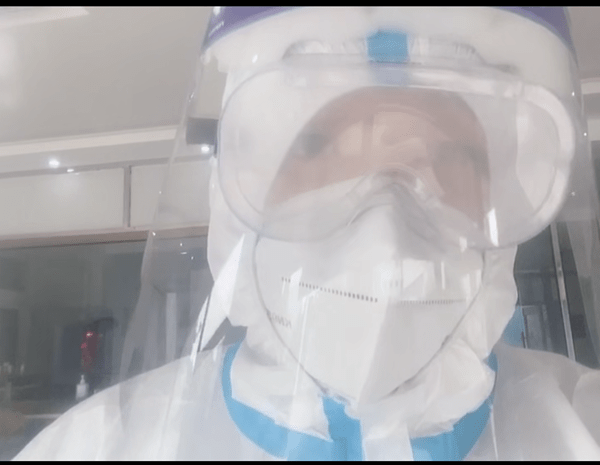


![[иө°з§Ғ]иӯҰж–№зӘҒиўӯиө°з§Ғд»“еә“пјҢеҸ‘зҺ°10жһ¶е…ұиҪҙж—ӢзҝјзӣҙеҚҮжңәпјҢеұ…然жҳҜзәҜжүӢе·Ҙжү“йҖ](http://img88.010lm.com/img.php?https://image.uc.cn/s/wemedia/s/2020/c8ccb32baca45ed2b7fdedb939dbab14.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