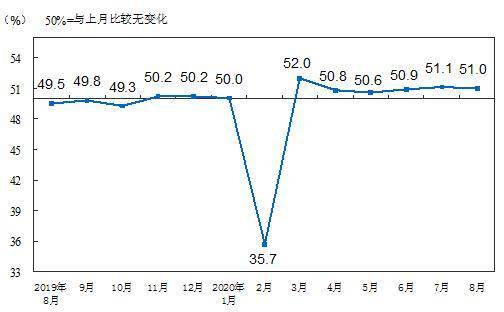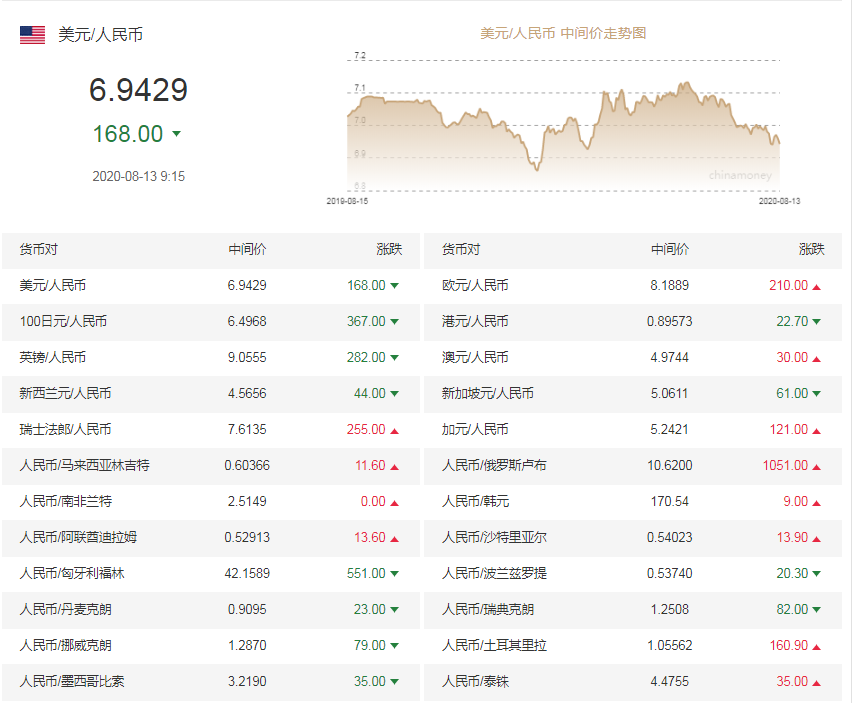第三章
第三章。第三章
收获季节之后 , 滇人开始准备对昆人的战争 , 这差不多已经成了两个地域之间的惯例 , 收获季节暂停战斗 , 而在冬季到来时 , 是最适宜交兵的时节 。晋城派来信使 。 这是一个刚刚成年的小伙子 , 滇人的少年武士们 , 大多是从充任信使开始他们的征战生涯的 , 信使不但需要一个好记性 , 还需要足够的精明和机灵 , 以及连续乘骑一两天的忍耐力 。信使传送的消息 , 是告知瀓城的武士们 , 晋城要组织在滇海北部向昆人发起的战斗 , 根据可靠情报 , 昆人开始建筑城池 , 据说已经基本完工 , 为了彻底摧毁昆人的城池堡垒 , 滇地必须全力出击 , 这一次 , 需要征召瀓城武士两百人 。滇海 , 是指滇人控制了其周边大部分地区 , 在晋城以北方向的那个大湖 , 那是滇人看到过的最大的湖 , 传说中的海 , 以出产海贝著称的海 , 一直是滇人向往的 , 滇人把这个硕大的湖称为海 , 而且称为滇海 , 显示了他们希望控制整个滇海周边的决心 , 但昆人一直是这个愿望的最大障碍 , 如今 , 晋城将一如既往的组织对昆人的战争 。武士两百 , 意味着至少需要三倍的侍从 , 再带上一批驭使奴隶和牛马 , 将是上千人马的队伍 。瀓城内马上开始了出征准备 , 每个战士的武器和食物 , 都需要自己准备 , 早早备下的肉干 , 被细细切割为肉丝或肉条 , 一片片检查过了 , 再仔细地收入囊中 , 米面被炒熟 , 再磨细 , 也收入专门的干米囊中 。城东和城北面的铜匠作坊里 , 开始了连夜工作 , 铜矢必须越多越好 , 武士们盘算着 , 再花一些海贝 , 再多准备一把更硬的铜剑 , 砍杀昆人时 , 说不定能保住自己的性命;有的武士把头盔拿出来擦了又擦 , 寻思着需要在头盔的正面再加一些铜块 , 或者在长长的臂甲上再加固一块嵌铜 , 上次出征时 , 有个同伴就是因为臂甲薄了些 , 被昆人用铜斧把手砍断了 。 出征之前看看自己的装备 , 武士们总能发现还有没做完的事 , 之前一直没做 , 主要还是因为海贝不够用 , 就连源这样的富人也在想 , “打完战回来 , 等弥夏下一次再回家时 , 我要到弥夏常说的海边去 , 听说那里有捡不完的海贝 , 有了海贝 , 可以再做一套盔甲 。 ”源已经有了三套完整的盔甲 , 但在他的心目中 , 最好的一套还没有做好 。马儿正被悉心检查 。 长了秋膘的马匹 , 都在马厩里撒着欢 , 这些矫健的马匹 , 被人们牵出来 , 就在田野里驰骋 , 久经沙场的武士 , 指定一个小武士跟着 , 天天练习配合、协同 , 侍从们在马匹后面跟着跑 , 他们需要熟悉武士主人的意图和体力状况 , 如果由于侍从的疏忽而导致武士殒命 , 该死的侍从们会被其他武士割头的 。两百武士 , 六百侍从 , 这是瀓城最庞大的一次集合 。 战士们就在城外田野里野战合练 , 田野一览无遗 , 北山口开始向瀓湖方向刮起北风 , 冰冷的铜盔皮甲 , 硬邦邦地罩在身体上 , 把身体都磨出血道道来 。议人会议决定:每天杀五头牛 , 就在田野外烹熟 , 让战士们吃了再练 , 练了再吃 。 五天之后 , 人马就要出发了 , 这算是瀓城对子弟兵的款待 。议事堂的铜釜里 , 又开始烹煮着肉块和米饭 。 这次出征的费用怎么出 , 是这次议人会议的重点 , 其次 , 议人们要决定祭祀出征大事的人选和规模;征召这么多人马之后 , 瀓城的防卫事宜;再有一个话题 , 可以说得上是老生常谈――同昆人作战 , 这一次更显得迫不得已 , 从北面传来的众多消息称 , 北面那个巨大的地域 , 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征战 , 据说 , 北方的众多国家都能发起上万人规模的大征战 , 那边的人多得不得了 , 每一个人挥一把汗 , 地上就象下雨一样 , 等他们自己分出胜负来 , 他们迟早会从北边过来的 , 而昆人同滇人对抗多年了 , 昆人要是同北边来的人联合 , 滇人肯定要吃亏 。吃着肉 , 议人们先交流一下北边的情况 。 源的说法里充满着向往 , 这是弥夏从家乡 , 从旅途中 , 从昆人那 , 从出产盐巴的江边人那里听来的 , 再由源向大家娓娓道来:“那是一个有符号、有法度、人们不再袒露躯体的地方 , 更是一个血性的地方 , 那里的人会为一个承诺而放弃自己的亲身骨肉 , 会为一句话而肝胆涂地 , 也会为一些符号记录下来的、看不见的东西而到处游走 , 终其一生 。 ”佐亦喝着肉汤 , 若有所思:“我从以前就传过来的消息里知道 , 那里的人会为前辈说的话 , 甚至自己想出来的东西而整天争论不休 , 一天天不做事 , 就这样讨论来 , 讨论去 , 他们不大相信祭坛 , 更无法相信祭司的话 , 听说主张不打仗的人能同主张打仗的人和平相处 , 其他的人也能忍耐他们 , 这不是乱套了吗?”源只顾顺着自己的思路想:“说归说 , 但他们有更厉害的黑兵器 , 更奇特的作战阵势 。 我不知道什么是阵势 , 听弥夏说 , 他们的士兵都只做自己被命令做的事 , 弓箭兵就只射箭 , 长枪兵就只练习出枪 , 他们有战车 ,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战车……”艾平打断了源的话:“大战在即 , 我们谈谈这次怎样迎敌 。 这一次 , 晋城征召的数目特别多 , 我们将同昆人决战 , 从老祖祖开始 , 几辈辈人了 , 昆人消耗了我们大量的人力和财富 。 我们的疆域一直难以扩大 , 就是因为边界战事不断 。 有了昆地的牛马 , 再把昆人变成奴隶 , 我们把边界延伸到更远的北方 , 我们才能有力量对付北方人 。 ”佐亦嚷了起来:“上次晋城还没有把征召费用算过来 , 晋城没有办法 , 我们都知道 , 可这样一次次打仗 , 我们花费太多了 , 而从昆人那里无法得到我们需要的 , 无法补偿出战花费 。 这一次两百个武士出战 , 花费将是往年的三倍 , 往年打一次 , 基本是一年的积蓄了 , 这一次是三倍 , 彻底打败昆人也就无忧了 , 要是再无功而返 , 我们至少需要三年 , 才能恢复!”艾平拍案而起 , “什么话!我们滇人谁都不怕!别忘了 , 在祖辈的手上 , 每年上百的战俘抓来 , 不仅仅上百了 , 工地上总有上千人在劳作 , 天天有百多个武士看管着他们 , 不让他们干别的 , 就让他们年复一年修祭坛 , 修公坛 , 修城池 , 修码头 , 修山上的蓄水池 , 上百年了 , 战俘就干这个 , 谁说打仗没有好处?不打仗 , 我们不一定会修这些东西哪 。 我们的滇是一个大地方 , 向东走 , 我们要再走三天 , 才到我们控制的边缘 , 向南走 , 可以一直走到那条红色的大河 , 那是一个热得让人受不了的地方 , 距离我们钟爱的瀓湖和神山太远 。 我们祖先一路迁移而来的西北方、西南方 , 更是我们最可信赖的地方 。 除了昆人占据的北向 , 你说 , 我们还有那里到不了?我们只有打败昆人 , 才能同更北方的人决一雌雄!”源有些听不下去了 , “出征是肯定的了 , 冬天快要来临 , 我们不同昆人作战 , 昆人也肯定要来滇海坝子袭扰我们的晋城 , 袭扰我们在海边的城池 。 那座小城根本无法修高 , 昆人年年来 , 他们的马儿快 , 只要我们修城 , 他们就天天晚上来偷袭 , 有时大喊大叫来 , 有时偷偷摸摸来 , 每一次 , 都把小城的人惊醒一次 。 没有人受的了 , 守小城的人必须每三天就换一次 , 我们每次出击 , 其实很难找到昆人 , 他们是放牛放马的人 , 说走就走了 , 要同他们决战 , 不容易 , 否则 , 这么几辈辈祖先年年打 , 早打下来了 。 ”“屁!每次我们都能割头回来!虽然每年割的头越来越少 , 不过这也说明昆人越打越少了吗?我们这次举族出征 , 让周边的族群看看 , 滇人到底能不能决战!”“艾平!我不是不赞成决战 , 但昆人的实力远远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 , 弥夏的见闻还是要听听 , 他说 , 昆人实际上正同北边的人交易 , 购买一些昂贵的黑色武器 , 我担心他们会把北边人的方法也学会了 , 现在北边的人打仗 , 都是讲究阵势……”“阵势?!我就不信昆人同你摆阵势!这一次 , 我带一百武士 , 你带一百武士 , 看谁杀昆人多!”议事堂会议不欢而散 , 出征的费用怎么出 , 瀓城的防卫怎样安排 , 这些重要的议题根本无法讨论了 , 会议草草确定了出征祭祀的人选和规模 , 议人们各自回家 。天已经黑了 , 源搀扶着佐亦 , 一步步向她在城墙边的住所走去 , 出了议事堂 , 就不再谈论议事堂的事 , 这是议人的操守 。 源和佐亦沉闷地走 , 城中不时传来狗的嗥叫 , 同往日不同的是 , 狗们是在徒然地为自己壮胆 , 源熟悉这样的狂吠 , 心里一阵阵发紧 , 这种狂吠 , 是狗们在面对老虎 , 花豹 , 野猪等大型野兽时 , 才会发出的哀鸣 。 入夜后 , 北风更紧了 , 瀓城里有一种压抑的气氛 。佐亦停下脚步 , 示意源到此为止 , 三天后 , 将在天坛举行出征祭祀 , 从今天起 , 祭司们将斋戒三天 , 男子必须止步了 , 看到两个年轻的女祭司出现在住所门外 , 恭恭敬敬等待着佐亦 , 源告辞回家 。制作铜矢的作坊 , 几天来轮流工作 , 一直都没有休息 , 他们正在用耗资昂贵的失蜡法铸造铜矢 。 一只只腊做的箭矢模型整齐划一 , 正被工匠们逐一打磨修改 , 铜矢用失蜡法 , 能够保证箭矢没有范痕 , 个个一样精密 。 源小心抓起一只腊模 , 斜着眼睛看看 , 这样精良的铜矢 , 每一只都将夺取一个昆人的生命 。炉火正旺 , 源不愿早早回去 , 他守在火炉旁 , 为一只只腊模浇铸铜汁 , 工匠往坩锅里投入不同的锡块 , 铜条 , 慢慢熔为亮红 , 铜汁吐出一丝丝黑烟 , 翻出一点点黑斑 , 变得通透 , 变得高亮 , 源夹起坩锅 , 慢慢倾倒 。就在源的家中 , 已辛抵上窗户 , 再挂上一块块毛皮 , 火塘不时炸开 , 跳出一块块小小的火炭 , 在石板上闪动着 , 渐渐熄灭 , 已辛铺好厚厚的毛皮 , 再加上厚厚的垫子 , 侧耳听着屋外响动 , 许久 , 长长叹了一口气 , 钻进被筒里面 , 她的侧影放大到了墙壁上 , 微微摇曳颤动着 , 正对着无形的谁诉说什么 , 木块燃烧出好闻的气味 , 在紧闭的房间里慢慢扩散 。天坛顶 。 出征的武士们匍匐在地 , 天坛的平顶足够容纳两百人 。 他们都面对着坛顶的木厅 , 佐亦就端坐在木厅的高台中间 , 一把高几稳稳地托住了她 。木厅为两层 , 底层是平时祭祀所在 。 为了能够感应上天 , 木厅没有围墙 , 也没有隔断开来 , 甚至在二层高台上也没有栏杆 , 佐亦背对着凌厉的寒风 , 面向西南方向端坐 , 风吹拂着她的衣襟 , 长长的外罩披风在她身旁招展 , 使得她的身形骤然增大了几倍 。佐亦闻风而动 , 在朔风中缓缓站立 , 平举双手 , 衣襟翻飞乱舞 , 吓的前面的人颤抖起来 , 佐亦开始在高台上游走 , 毫无征兆的舞姿 , 怪异飘荡的形体 , 显示出一种对抗 , 一种针对无形物体的挣扎 , 高台周围的人们屏住呼吸 , 一动不动 , 等待着抗争的结果 。祭司在高台上快速游走 , 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个行动不便的老者 , 让源惊讶不已的是 , 佐亦这些年已经连肉都嚼不动了 , 走路都成了问题 , 今天在高台上如此疯狂 , 源时时担心她会瘫倒在朔风之中 , 定眼看过一阵 , 源放心了 , 佐亦在高台上的矫健身手 , 源暗叹不如 。台下的武士鼓噪起来 , 兴奋得大喊大叫 , 他们的祭司正在预示战争的结果 , 祭司越精神 , 就表明未来的战事将会十分顺利 , 祭司打击她那无形的对手 , 打击得越彻底 , 他们在战争中就越顺手 , 就能得到更多的战利品 。 年轻祭司们涌上台去 , 把佐亦抬了下来 , 佐亦就端坐在祭司们的肩头 , 神采奕奕 , 眼睛射出亢奋的光彩 。滇武士发一声喊 , 簇拥着佐亦冲下高台 , 如同冲下山峰的牛群 , 源跟在众人之后 , 感到一种惊天动地的气势 。 呐喊声丝毫不受西北风的影响 , 传递到瀓城的四面八方 , 城中各处 , 同样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咯咯”喊叫 。 更多的人向公坛奔来 , 滇人的传统 , 只有武士才能参加在天坛的出征祭祀 , 这个高台顶端 , 就是滇人最看重的圣地 , 从来不沾血的 , 滇人出征前的牺牲 , 将在公坛里的铜柱前宰杀 , 武士们的侍从和家人 , 正向公坛汇聚 , 大家将一起见证瀓城的征战奉献 。一头健壮的公牛 , 一个裸身的昆人 , 早已经分别捆绑在人柱、畜柱铜柱旁 , 不但裸身的人在瑟瑟发抖 , 就连那头高大无比的公牛 , 也流露出恐惧的目光 , 人越聚越多 , 在瀓城人的啸叫声中 , 昆人和公牛抖成一团 , 身下洌出一阵阵尿水 。佐亦高举双手 , 示意大家安静 , 悍走上前来 , 踩住昆人的长辫子 , 一圈圈绕在自己的手上 , 昆人的双手被另外两个武士按住 , 发出骇人的尖叫 , 绕好辫子的悍拖着昆人就走 , 一路走到人柱铜柱跟前 , 把辫子穿进铜柱的铜环之中 , 按住双手的两个武士把昆人的手扣到铜环里 , 用一段铜链固定好 , 再把他的眼睛蒙上眼罩 , 昆人就这样悬挂在那里 。年轻的祭司们围起铜柱 , 高举双手 , 口中念念有词 。 手掌也开始在空中颤抖起来 , 悍屏住呼吸 , 慢慢举起狼牙棒 , 听着祭司们的语速越来越快 , 声音越来越高 , 突然间 , 声音嘎然而止 , 悍挥下狼牙棒 , 只听“喀嚓”一响 , 昆人脑浆涂地 , 悬挂着的腿抽搐了几下 , 从鼻孔里长长出了一口气 , 身心彻底解脱 , 再也没有声息 。畜柱低矮、粗壮一些 , 牛的头颅 , 将放在畜柱上边 , 由铜锤锥毙 。 看到对面的昆人惨状 , 公牛的眼睛变得血红 , 这头牺牲不甘地昂着头 , 把鼻孔里的缰绳扯得笔直 , 鼻孔已经流出一股股鲜血 , 源看到这样的情况 , 有些担心了 , 他听说过这样的往事:莽撞的公牛撕开鼻绳 , 大肆践踏残害它的人 , 那种场景不常有 , 但据说确实发生过 。源走上前来 , 从侧后靠近公牛 , 把一条红布带罩到它的眼睛上 , 轻轻抚摸着它的额头 , 暴躁的公牛慢慢平静下来 , 源分明看到 , 红布带的下面 , 流出一道弯弯曲曲的眼泪 。源有些不忍 , 让大家把公牛拉出去 , 公牛的四条腿都袢上绳套 , 两个强悍的武士负责抽紧缰绳 , 在牛头上又加固了数道粗大的麻绳 , 把牛头牢牢压迫在畜柱上 , 而牛的四肢被分别扯开 , 前肢分别抱在畜柱两侧 , 而后肢几乎成了悬空腿 , 牛已经无法施展力量 , 被扼紧的牛颈发出低沉的吼叫 , 这是这头无助的牛最后的挣扎 。悍提着硕大的铜锤 , 走到畜柱前 , 他往手心啐了几口吐沫 , 再把铜锤小心扛起 , 眼睛望向佐亦 , 佐亦不露声色 , 轻轻点了下头 , 悍举起铜锤 , 在空中比划了一下 , 重重锥了下来 。牛、人的鲜血 , 把公坛整个染红 , 武士们逐个来到畜柱前 , 往自己的额头上抹一点牛血 , 再走到作为牺牲的昆人跟前 , 有的人粘一点人血 , 有的人粘一些脑浆 , 也有人什么也不沾 。牛肉开始分割 , 一块块肉被送到公房里面 , 火塘已经燃起 , 铜釜和烤架分别坐上火堆 , 芦笙、葫芦丝、铜鼓已经奏响 。 公房就在公坛旁 , 这里是瀓城未婚男女平时聚会的地方 , 今天 , 这里将是出征青年男子同情人告别的地方 。滇人有这样的规矩 , 青年男子第一次出战 , 如果他是未婚的 , 他都要把精血留在城中 , 留在公房之中 , 留在某一个姑娘的体内 , 不管他能不能让女子受孕 , 这样的交合都必须完成 。源端坐在公坛中段 , 看着场内的喧闹渐渐平淡 , 天色已晚 , 寒风刺骨 , 源不由得裹紧了衣服 。 公房是青年人的场所 , 他该回家了 。已辛早已经准备好了一切 , 她甚至为源准备了蜂 。 蜂是已辛从娘家带过来的女奴 , 严格来说她并不是奴隶 , 她的父亲在蜂五岁时 , 在一次对昆人的战斗中被俘 , 昆人对他施行了可怕的折磨 , 三天之后 , 蜂的父亲彻底崩溃了 , 昆人让他做什么 , 他都是言听计从 , 昆人专门用两个人架着他 , 让他带路夜行 , 悄悄地绕过滇海的那道石墙 , 从晋城的侧后围攻上来 , 那是一个漆黑寒冷的夜晚 , 昆人一直移动到晋城的城墙下 , 只要他们三人一组架成人梯 , 晋城的城墙将被他们踏到脚下 , 最凶悍的昆人先锋勇士将把宽大的铜剑刺入火堆旁的滇人胸膛 。城墙侧面的沼泽地里 , 冬迁而来的野鸭和大雁发现移动的影子 , 听到了细微的声响 , “嘎嘎”“呷呷”叫了起来 , 叫声此起彼伏 , 唤起了滇人武士中的猎手们 , 这些人知道 , 晚上出猎时 , 野禽只有在危险靠近时才这样惊惶失措 。滇人把火把扔下城墙 , 看到了正在墙角架人梯的昆人 , 他们只差那么一点就得手了 。 滇人看到的 , 还有在昆人中间被两个人抬着的 , 躲躲闪闪的蜂的父亲 。 城墙上的火堆被七手八脚扔下城墙 , 城上漆黑一片 , 而城下变得分外明亮 。 昆人的人梯马上散开 , 有人企图踩灭燃烧着的木材 , 立即被城上射下的铜矢戳穿 , 火把扔得不远 , 在墙角火把前出现的昆人距离太近 , 无法逃避飞矢 , 一瞬间 , 城下哭喊声乱作一团 。来袭的昆人把马匹留得远远的 , 他们不希望马蹄暴露他们的行踪 。 这是昆人在以往的盗窃袭击中经常用的方法 。 这一次 , 突袭的勇士们失算了 , 城中冲出一队举着火把 , 骑着骏马的滇武士 , 快速向发出马群嘶叫的地方奔去 , 昆人马群留守的地方 , 仅仅只有五个警戒人员 , 无法围拢慌张的马群 , 只好迎着滇人马队冲来 , 立即被杀死在旷野中 , 拼命奔向马群的昆人 , 绝望地止住了脚步 。 他们被出击的滇人扔出的火把困在旷野之中 , 想射杀出击的滇人 , 可根本找不到这些移动的目标 。 这时候 , 城中悄悄涌出一批滇人弓箭手 , 他们人数不多 , 但箭无虚发 , 只要看到有昆人接近火把 , 立即射杀 , 骑马出击的滇人不断往昆人周围投掷着火把 , 纵马追杀企图冲出火把圈的昆人 , 让昆人撕裂的惨叫遍布旷野 , 昆人最终彻底放弃了抵抗 , 等到天明时 , 饥寒交迫的昆人发现围住他们的滇人并不多 , 但滇人似乎正源源不断的赶过来 , 围上来的有执剑的女人 , 也有顶盔的老者 , 甚至有仅仅拉得动弓的少年 , 这些平时使用小弓小箭的少男少女 , 把他们的小箭对准了圈中的昆人 。这批昆人 , 被他们那惊惶失措的首领放弃了 , 石墙前的滇人守卫武士目视着大批准备攻击的昆人骑手纷纷后转――夜里突袭不成功的消息 , 被滇人举到石墙前的几颗昆人的头颅证实 , 并且被气势汹汹的滇人夸大了 , 不断有人头送到石墙前 , 排成整整齐齐的一排排 , 瞪着眼睛看面前的昆人 。 等太阳从滇人方向斜射过来的时候 , 昆人选择了撤退 , 对着初升的太阳发起进攻 , 他们将损失惨重 。被俘的昆人 , 以及蜂的父亲 , 都被送到瀓城加固公坛和祭坛去了 , 公坛和祭坛是滇人利用山型 , 在外层披上一层巨大的石块建成的 , 没有一个滇人说得清工程开始于哪一年 , 但大家都可以看到 , 这批被俘的昆人 , 将是最终完成这些工程的奴隶 。蜂的父亲成为奴隶 , 蜂和兄弟、妈妈也同时被贬为奴隶 , 家产充公 。 已辛的家人是蜂家的邻居 , 尤其是当时幼小的已辛 , 同情比她还幼小无助的蜂 , 就在这一年 , 从蜂五岁时起 , 她成为了已辛的贴身女仆 , 而就在这一年 , 从瀓城传来蜂的父亲死亡的消息 , 据说是被石块砸死的 , 一个奴隶的死亡 , 从来都是这样语焉不详 。所以 , 已辛一直想让蜂恢复她的自信和她的家族血统 , 在今晚这样的出征前夜 , 已辛安排让源收用蜂 , 并无不妥 , 蜂同样也是滇人 , 而且是同已辛没有区别的晋城人 , 十多年过去了 , 昆人造成的这场悲剧 , 不应该让蜂继续承担了 , 蜂要能光明正大地孕育一个滇人血肉 , 是最理想的解脱方式 。源的儿子洛卡 , 早就候在门后 , 一等源进屋 , 就象一只大号铜矢一样奔向源的胸腹 , 源被撞得退后几步 , 就势一屁股坐到木地板上 , 这个肉墩墩的小子身上 , 还带着一股乳香味 , 源把鼻子埋到儿子的肚皮里 , 深深呼吸着小家伙的味道 , 他的鼻子磨蹭着洛卡的痒痒 , 小家伙“咳咳”笑不停 。肉还在煮 , 烤鱼的架子刚刚抹上油的时机 , 已辛让源的侍从们把为他准备的装备搬出来 , 一件件展示给他看 , 有带毛的皮革膊披甲 , 长长厚厚的虫兽纹铜臂甲 , 源亲手打获的虎皮 , 在下摆装饰上了缀流苏 , 这是骑马时抵御寒风最有用的围腰 。 而束虎皮的腰带 , 装上了新的二虎噬牛扣饰 , 一对给源带来过好运的铜镯 , 是已辛在未结婚前送给源的 , 现在再次准备好 。 装饰用的金剑鞘、金钏、金项链、金扳指、玉耳环、玛瑙扣 , 让源挑选一些带上 , 源拜拜手 , 让他们把这些不实用的东西收起来“这一次 , 我估计是一场硬仗 , 这些不带 , 收好了 , 我回来要用的 。 ”新做的铜剑太长 , 源把铜剑系上腰带 , 佩带在身上比划 , 他发现 , 只有横背在身后 , 骑马才方便 , “这么长 , 可以击远了 , 只是不知道硬度怎样?”在源的印象中 , 太长的铜剑 , 在兵器对抗时 , 容易被短兵器折断 , 听说这柄铜剑使用了新的锡、铜比例 , 源拔剑在手 , 挥剑砍了木头 , 力道从小到大 , 剑的质心就在剑首 , 这样的剑 , 在击杀时将会十分舒服 , 源让侍从拔出铜剑 , 两人小心翼翼地对剑 , 逐步加大了力量 , 看样子 , 新剑比以往的硬度大 , 而且不容易折断 , 源十分满意 。源的新马具被呈上来 , 这是参照了弥夏一路骑过来的马匹马具 , 源专门让皮匠、铜匠制作的 。 皮具有项带、额带、鼻带、咽带、颊带等种类 , 而且在项带、额带、鼻带、咽带、颊带上面 , 由皮匠和铜匠合作 , 使用辔饰与铜泡、泡钉装饰 , 源翻过来细细看 , 在络头的各条革带上 , 都穿缀着辔饰 , 带与带之间交接处还使用节约相联 。 在马具的额头位置 , 用了一个通筒 , 这是可以装配羽翎的通筒 , 而在马具的颈胸前 , 辔饰和节约联缀成了新型的攀胸 , 马具颈下位置 , 悬挂了一个铜铃 。 这是一个鎏金圆形铜铃 。源的老母、家人一同看过他的新马具 , 让源稍稍担心的时 , 这一次 , 老母对他的新马具没有任何评说 , 十多年前 , 源的父亲战死后 , 母亲一直独自把孩子们带大 , 面对又一场大战 , 老人显得心事重重 。 父亲是在对昆人的战斗中损失了一只眼睛 , 铜矢伤及脑颅 , 在挣扎了三天后死去的 。 而就在源尚未成年时 , 源的大哥又在对昆人的战斗中阵亡 , 由于当时情况危急 , 尸体就埋葬在晋城附近 , 这是源一家人的遗憾 。 这一次战事绝对不会轻松 , 瀓城里的滇人都忧心忡忡 。看过源的马具 , 一家人可以开饭了 , 洛卡早已经跃跃欲试 , 被蜂悄悄地抱到另一边 , 往他的小嘴里塞满了肉 。 女儿利亚似乎懂得父亲就要出征的意义 , 忧郁的大眼睛一直跟着源转 , 看得源一阵心痛 。 他把利亚抱入怀中 , 再往她的小碗中夹入一点鹿肉 , 这是往日利亚最喜爱的食物 , 利亚用两个小手指小心地抓起肉片 , 非要爸爸吃不可 。 源就着她的小手无声地吃了几块 , 再也无法吃下去了 , 这是出征前家人团聚的一餐 , 但饭吃得很压抑 , 洛卡早被蜂塞饱吃好 , 只有他的心情丝毫不受影响 。 源让他爬到地上 , 双手抓住他的小脚 , 也俯身跟着爬 , 手就联上洛卡爬行的节奏 , 父子两人在地上步调一致地爬 , 学小老虎大老虎 , 这是滇人父亲最喜欢同儿子玩的游戏 , 大小老虎四处巡游 , 不时咧开大嘴吓唬人和家养动物 , 一家人终于有了笑声 。在摇曳的火光下 , 蜂面对着已辛坐着 , 源端坐在她们的侧面 , 静静地看着她们俩 。 屋门早已经关上 , 屋外的寒风只有在外面“呜呜”嚎叫的份 。 源感到自己的脊背在出汗 , 一股股往下淌 。 而蜂仿佛有些冷 , 慢慢裹紧了自己 。已辛笑了 , 她专注地看着蜂 , 慢慢伸出手 , 抚摸着她的面颊 , 对着她的耳朵说话 。 蜂低下头 , 似乎害羞地转过头 。 已辛站起来 , 把一壶水放到火塘上 , 屋内的光线顿时黯淡了很多 , 压迫源的那种燥热也一下消失 , 在影影绰绰的光影中 , 蜂慢慢对着他转过身来 , 褪去了自己的衣服 , 眼睛一直看着他 , 身子就侧倒下去 , 一直倒到被褥之中 , 圈着的双腿缓缓伸长出去 , 一个美好的躯体就这样坦荡无余地闪动着瓷光 , 火光为她的身体打上了柔媚的光晕 , 看得源一阵阵目眩 。已辛一动不动 , 就侧坐在蜂和源之间 , 靠近蜂脚部的位置 , 背部对着源 , 这个位置 , 还是多年以前 , 在源和已辛夫妻同床共枕时 , 已辛安排过蜂留驻的位置 , 这都是已辛刚刚结婚时候的事 , 那个胆小的女孩已辛 , 希望与自己一同长大的蜂能陪着自己渡过这种时候 , 但仅仅两次以后 , 已辛再没安排过这样的事 。源控制着自己的动作 , 慢慢站立起来 , 和衣钻到被褥之中 , 把被褥轻轻拉到两个人身上 , 面对着她躺下 , 蜂的眼神充满了期待 , 也充满了游动的灵光 , 源回应着这种灿烂的眼神 , 这是相互心悦之人才会燃烧出的激情 。 源就在被褥中除去自己的衣服 , 他默默念叨着努力让自己慢下来 , 但颤抖的双手还是抚摸到了蜂 , 同样火热的蜂往前移动了稍显瘦削的身体 , 立刻撞到已经极度膨胀的源身上 。已辛呆呆看着自己制造的这一幕 , 回想几年之前 , 同样瘦削的自己没有这样大胆的举动 , 但一瞬间之后的疯狂完全一样 。 触摸到源滚烫的身体之后 , 已辛和蜂的反应都是一样的 , 她们都用同样的火热打开了自己 。轻轻抱着蜂的源 , 还在控制着自己 , 他回馈着蜂的火热 , 让她同自己一起再迅速升温 , 火热燃烧着迷茫的蜂 , 烧得她叨出一声声不连贯的絮语 , 终于 , 一声有些突然的叫声从她颤抖的嘴唇发出 , 这种叫声似乎来自遥远的地方 , 仿佛不是蜂自己的声音 , 随即 , 蜂被一阵阵巨大的欢愉感冲开了天灵之窗 , 她飞起来了 。身着新铜甲、披挂着新马具、新铜剑的源 , 带着对新人的记忆 , 从北门出城 , 沿着昆滇交界的线路向晋城前进 , 左右簇拥着近千名瀓城战士 , 他们这一群人 , 组成了瀓城规模最大的出征队伍 , 人数太多了 , 他们将不再乘舟跨湖出征 。 看看前后左右簇拥着的伟岸甲士 , 听到身旁自己的装具制造出的砰砰声响 , 战士们摩拳擦掌 , 兴致勃勃 , 瀓城的大量牛群 , 由于大群战士外出作战 , 将被集中到距离城池较近的地方集中放牧 , 留守的女人和小童 , 以及年老体弱的人们 , 负担将更重了 。走出稻田耕作区 , 队伍进入了茂密的大森林 , 前队都是一些优秀的猎人 , 这些人鼻子比猎狗还灵敏 , 身手比老虎还矫健 。 这时候 , 他们就象兴奋的猎犬 , 在充满着兽味的森林中寻觅 , 令人稍稍遗憾的是 , 大队人马的喧嚣 , 早把野兽们吓跑了 , 开路先锋换上一批身高马大的壮士 , 他们手持开山大斧 , “咚咚咚”砍掉那些能挡住马的枝条 , 滇人穿越丛林的能力很强 , 这时候 , 大家纷纷下马 , 牵着马匹成单列在树林中慢慢前进 , 马蹄声“呱叽呱叽”淹没在丛林的稀泥里 。挥动着开山斧的大汉们接近黑色的森林 , 慢慢停下了斧头 , 这是平日单个猎人不敢轻易涉足的恐怖森林 , 是滇人传说中老虎经常聚集的虎山 , 老虎一般不聚集生活 , 但这座山的老虎 , 常常成群出现 , 这座山的树林高大挺拔 , 尤其在背阴面长得特别好 , 从瀓城看过来 , 这里的树仿佛就是黑黝黝的 , 有人把这里也叫做黑森林 。艾平扇动着鼻翼 , 仿佛在空气中闻到了什么 , 他被熟悉的人称为“黑森林之子” , 但这是一个会勾起痛苦回忆的称谓 , 每当听到、看到黑森林 , 艾平的心总是紧成一团 , 童年的惨烈回忆 , 总是伴随着艾平 , 一直到成为瀓城议人 , 成为瀓城最精锐的弓箭队队长 , 顺利娶妻生子 , 艾平还是被噩梦困扰着 , 阴郁的记忆中 , 从来都少不了黑森林 。源走到了整支队伍的最前面 , 面对着滇人的神山 , 他缓缓跪下 , 向神山祈祷 , 祈福虎山庇护 , 马到成功 , 旗开得胜 。之后 , 他镇静地上了马 , 径自骑行而上 , 身后的滇人中 , 大多不止一次穿行过这里 , 但这座黑幽幽的山永远不会给人安宁 。今天晚上 , 队伍就在虎山另外一侧山麓宿营 , 入夜 , 陆续有人返身步行到山顶的石崖边 , 向来路方向看 , 可以看到远处的瀓城 , 在宽阔的湖面上投下的点点火光 , 队伍中那些第一次出征的滇人武士们 , 无一例外 , 全部到了山巅 , 在黑夜的掩护下 , 他们可以把思念妈妈和恋人的泪水悄悄洒在脸颊边 。源就侧卧在火堆旁 , 冬季的山麓 , 处处透着一股阴森森的寒意 , 他漫不经心地往火里投着木材 , 有一句 , 没一句地搭着众人的话题 , 这时候 , 他才体会出昨晚已辛安排蜂的深意 , 蜂年轻玲珑的躯体留下的记忆 , 在这样温馨的氛围里 , 显得分外清晰 , 分外可贵 。艾平悄悄向黑暗深处走去 , 源打了个寒战 , 想起身跟着他去 , 艾平在森林边缘停住了 , 抬头看着高高的树影 , 树影如同一个深深的窟窿 , 一直坠向黑灰的天空 , 冬夜无星 , 天空涌动着不怀好意的黑色灰云 , 挑衅般在艾平头顶徘徊 。源听说过艾平的一些家事 , 那是源的母亲断断续续透露出来的 , 瀓城人对死亡熟视无睹 , 但对于发生在滇族福祉——黑森林的往事 , 始终顾忌重重 , 尤其是艾平家的事 , 他们说得很少 , 当事人大多是晋城武士 , 当年经历过变故的武士 , 如今大多已经故去 , 黑森林的往事 , 将永远成为秘密 。这个从小的玩伴和战时的生死朋友 , 一直是源最强的竞争伙伴 , 他们几乎一起学习斗剑 , 一起学习在众人面前辩论 , 一起在公坛聚会时勾引瀓城的年轻女子 , 艾平总是反驳源的主张 , 即使这是他们私底下已经反复讨论过的话题 , 但在艾平咄咄逼人的话锋中 , 源还是感到了艾平拼命掩饰的自卑 。 源总是在旁边默默留意着艾平 , 艾平似乎格外需要这种不经意的关注和保护 。一个年老的武士 , 不露声色地推推源的肩膀 , 顺着他们宿营的山麓往上看 , 在山巅左侧 , 出现了一个异样的闪光 , 之后 , 再连续闪了两次 , 看见闪光的滇人 , 只有源、年老武士 , 以及周围的三个将领 , 五个人心照不宣地相互注视着 , 默默地点点头 , 夜空再次变得漆黑一片 , 人声渐渐平息 , 只有马儿不时打着响鼻 , 山麓太冷 , 马儿很难入眠 。第二天 , 队伍都是行走在蜿蜒的山路上 , 晨雾一直笼罩着他们 , 直到他们走出很远 , 一直走到中午时分 , 周围还是雾气腾腾 , 源把宿营时盖在身上的虎皮架在身上 , 从后面看 , 就象一只老虎站在马背上耀武扬威地走 , 滇人们纷纷把皮毛挂在身上 , 有豹 , 有羊 , 也有狼、狗、熊、鹿 , 一只只动物在雾气中活灵活现 , 这是一支活过来的动物军队 。这天天黑之前 , 瀓城武士们到达了集合地点 , 开阔地带被划分成各城军队的宿营地 , 瀓城军队气势最盛 , 也是最早到达 , 大首领把他们移动到滇人阵列的最前面 , 提供给人马使用的水、草也最为丰美 。第三天 , 滇人队伍集合完毕 , 大队开始向昆地出发 , 这是一支接近四千人的队伍 , 堪称这块土地上最庞大的军队了 , 源默默走在队伍中间 , 在这样一支庞大的群体之中 , 他却不合时宜地觉得这样的出击毫无意义 。 昆人是一个放牛放马的种族 , 他们飘浮不定 , 诡计多端 , 只有在面对面对决时 , 尚武的滇人才能占到一些便宜 , 而这次出击的滇人人数众多 , 沿途的昆人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追击昆人 , 仿佛就是追击着太阳 , 源每天都跟着太阳起 , 追着太阳跑 , 他知道 , 太阳落山的地方 , 就是昆人逃离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