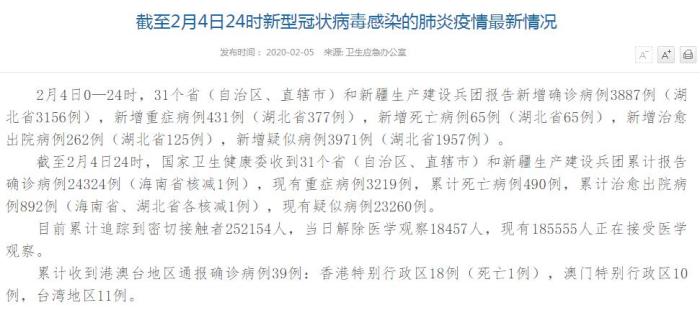偷东西是怎么样一种体验
我偷过七八样东西。价值大概在十元到五十元。每偷完一个东西都要忐忑好久,接下来几天都在想这件事,并且不敢把偷来的东西拿出来,只能放在家里,偷偷拿出来看几眼。我不知道别的偷东西的人是怎样的,但我一直为小时候偷东西的行为感到羞耻。
■网友的回复
嗯。。。好久以前的事了 几年前
朋友带着我在商场偷过东西
不知道是身边的攀比风太严重还是因为什么
她偷过化妆品,粉底液啊,遮瑕膏修容棒啊这种小贵的东西(她偷的东西都比较小 我俩逛街的时候她会偷偷藏在袖子里,)
一偷就是一小堆,价钱加一起总得有几百块了吧。。。。
她让我帮她守着,有店员去她身边我就会去支开
起初我是挺讨厌这种行为的
她跟我说有好处不会连累我,想想就答应了(现在想想真不应该)
再后来我们毕业了上的也不是同一个高中
再也不联系了
那段时间我的三观不稳定真的是随波逐流
她还和我说什么偷也算本事,自己偷来的
高考能作弊也是本事,毕竟自己有好处
现在我身边的朋友都不错
我也想弥补之前的过错
放假会回到以前中学旁边的那个商场
去那个店铺多买东西心里想着补偿补偿
会主动帮他们的店铺招揽顾客
那段时间真的是我一生里一个污点
最后奉劝大家
交友要谨慎 要交三观正的朋友
自己挣钱买的东西会有很大的自豪感
如果钱不够也不要攒生活费去买
更不要偷!!!!!!
【偷东西是怎么样一种体验】
■网友的回复
隔壁王二不曾偷,吴学俊。我曾在幼年时的一个夜被迭代的梦无限拉长的冬天,趁着做客小住之机,偷走了舅表哥家的一颗拳头大小的铁弹子,它大得让我只能想到有独门绝技的江湖侠客的武器,绝不会有哪种机械会用到镶嵌拳头的轴承——如果有的话,我一定要驾驶它,碾过曾经扭住我的胳膊的所有人的村庄,我要它的发动机发出雷声,像是空心糖的桐树干在黄金分割点被震断后舒缓地平移而失重,三千只麻雀从风中的竹林子弹一样慌张起飞,陪衬地掠过我自高自大的头顶,击碎那鹅黄了整整一个季度的矮天空。 但是当我跟它首次照面并动了偷窃的心机后,它不再是一个可供想象驱策的龙头虎身的机械,它仅仅是我必须顾及重量和形状的铁。我把玩了没有多久,突然领悟过来,不能让任何人在它失踪时想起我爱它。我视它如毒物,扔到了一间偏房的墙根,那个墙角的屋梁上悬挂着一具黑漆漆的棺材,它是为老而不死的人预先购置的——有完璧坚硬的棺材料理斑驳干脆的老身,他更能坦然地面对将死。我在几天后把它偷回来时,冒着很大的风险,那具棺材像一个死不瞑目的人一样盯着我,较大的一头又厚又肥,像是一颗为冤屈而浮肿的头颅,我越靠近墙角,山脉形的棺盖隆起越是高耸,我担心捡起弹子的一霎,棺盖会倒立,那已经被引狼入室寻替身的鬼魂会坐起来,大方得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他写过来的书信都是竖体的,而我必须拿生命当茶水和点心来侍奉他。我现在回忆过去,有如站在跟棺材平起平坐的角度观看偷窃。当时我就像一只准备受惊的老鼠拱着背走——停——停——走,目的十分直接,进程充满犹疑。我的眼珠子一动不动的,像是镶上的三色花瓣的陶瓷弹珠,在一切静止的危险面前跃跃欲试,但是任何一点运动都可能让我闻风丧胆,两股战战,几欲先走。 我把弹子偷到手带回家后就在堂屋里骄傲地弹来弹去,我喜欢听它在水泥地上轰隆隆的滚动声音。如果我把它带进学校,在课间的弹子比赛中,它会把一个小学的全部瓷质弹子打成三百朵莲花,所有人都会懊悔,对我出言不逊,最好是动手推搡,而我会爬到旗杆上装出纯洁的无辜,像一面国旗那样。可是就在上学的路上,隔壁的王二邀请我跟他弹子,王大和王三也入了伙。王三把我的弹子打飞了,王大一屁股坐到弹子跌落之处,王二跑到了王大屁股后面。然后王大站起来说,弹子丢了。王二说,我没有找到你的弹子。王三说,我们去上学吧。王大、王二和王三遂狼奔猪突而去。我和妹妹在王二母亲面前哭成泪人,她母亲左脸白、右脸红地说,他们不会拿你的;丢了就算了。 那时的冬天,我上身从内到外穿着四件衣服,衬衫、毛衣、棉袄和中山装。我把偷来的弹子藏在棉袄下摆处的内兜里。我一直脱臼了一样耷拉着两只胳膊,或者像个冻死鬼一样袖手抱臂放在小腹处。我不得不这么做,那个弹子放在衣服里就像是一个恶性脓包,随时可能爆出一腔白浆——如果我晚一点下手的话,也许我倒不用修正日常身势了,但母亲可能随时来接我,她一到来,我在这里的生活,就成了所有话题的引子与结语了,我的一举一动无不在前所未有的密切关注之中,直到我隆重地离去——还有一些惊心动魄的突发情况,为了应付它们,我的情感和理智一次又一次打破极限。一次洗澡时,我恶狠狠地打掉了表姐的手,坚持自己动手脱掉笨重的棉袄,在她的眼皮底下,从容地把藏有弹子的一角叠放到最下面,却不慎让弹子碰到搁衣服的椅板,发出叩击之声,我立即故意一脚捅到水盆里,溅起的水声,分散了表姐的注意力,只是我用尽了力气忍受了那滚烫。我的衣服在一天的晚餐上预言次日会被洗掉,于是在睡觉前我把弹子取出来藏到秋裤的后兜里,而在当晚,同睡的表哥爬到我的身上,用力地抱紧我,那弹子就一直咯着我,直到过了不久表哥觉得毫无意趣,翻身而下,我才得以稍挪弹子的位置。母亲在一个北风呼啸的下午姗姗来迟,我即将得救,表哥从后面捞着我的肩,表姐在前面扯着我的衣摆,虚情假意地挽留我,可是谁能阻挡一个罪犯逃离现场,我毫不留情地跟他们大打出手,当然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动真格的了!吴学俊。
推荐阅读
- 想象某些东西的时候会产生快感
- 接受去势手术是一种啥样的体验
- 怎样看待“人类只有一种疾病可治愈,即大叶性肺炎”的说法
- 在10天内被同一个东西上的病毒感染两次,可能吗
- 买东西的时候嫌它贵,是不礼貌的吗
- 一进知乎,看看评论,发现都是一些伪精英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
- 怎么样告诉父母我有男朋友
- 女生在空间留言说晚安,是啥意思
- 怎样在大学提升自信
- 年薪3万的你,过得是怎么样的生活